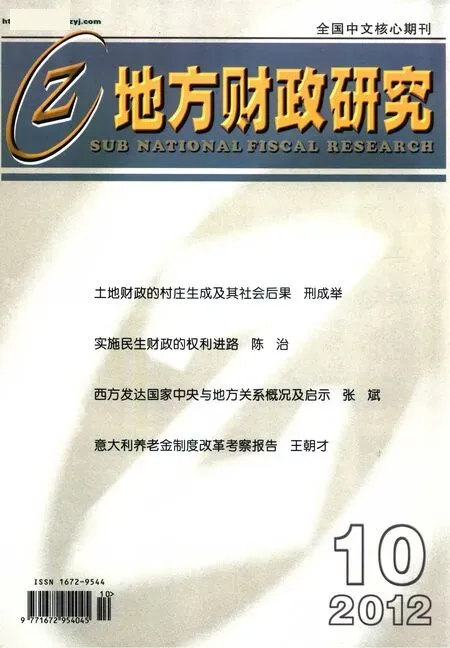“土地財政”路徑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及相關政策建議
于長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北京 100142)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增速保持在年初預期目標區間內,但國內外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世界經濟復蘇的曲折性、艱巨性進一步凸顯,國內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特別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面對新的經濟形勢,5月2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明確要求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宏觀政策預調微調力度,積極擴大需求,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梳理與“穩增長”相關的主要因素,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按照揚長避短的原則制定具體的政策措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其中,近年來為人們所熱議的“土地財政”自然應予以高度關注。本文從“土地財政”的產生入手,通過“土地財政”與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不可持續性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認真剖析“土地財政”與“穩增長”目標之間困局的形成機理,并結合當前的經濟形勢與目標任務提出具體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議。
一、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財政行動邏輯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與地方之間明確劃分了財政收支范圍,初步構建了分稅制基本框架,基本制度成果有目共睹,不容質疑。但由于省以下沒有真正實行分稅制,縣鄉財政困難便在“財權重心上移、事權重心下移”過程中凸顯出來,并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發了“土地財政”問題。
(一)“事權重心下移、財權重心上移”與縣鄉財政困難的凸顯
1994年分稅制改革初步劃分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但省以下未做統一要求。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省以下政府間財政收支的劃分頗具隨意性。另外,我國財政法制建設比較滯后,分稅制有關事宜主要源于行政法規,始終沒有通過立法程序,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在劃分過程中無法可依,在劃分之后的運行中更無法得到憲法與相關法律的保障,為高層級政府上提財權、下壓事權提供了空間,從而形成了政府間事權與財權的反向移動,直接導致了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嚴重錯位,最可悲的基層政府財力需求顯著大于財力供給,嚴重的入不敷出逐步使基層財政陷于“揭不開鍋”的困境之中。
2001年,全國拖欠工資的縣、鄉占全國縣、鄉總數的18.7%和27.1%,財政境況稍好的縣、鄉也僅僅限于“保工資、保運轉”,用于經濟建設的財力非常有限,各方面的支出欠賬越來越多,形成了巨額的隱性負債。
(二)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之下的自謀出路與“三亂”的泛濫
面對分稅制改革出現的“揭不開鍋”的窘境,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在無奈之下只能想方設法擴大稅源,以增加財政收入。但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地區的稅源是相對穩定的,地方政府通過增加稅收以盡快緩解財政收支矛盾的努力是不現實的。于是,預算外收支體系便成為地方政府財政解困的重要手段,地方預算外資金收入隨之迅速膨脹(如圖1所示)。

1995年-1996年,國家先后多次對預算外收支范圍予以調整,但地方政府卻不斷創新預算外收入名目,從而使地方預算外收入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1998年之后迅速上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預算外收支體系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且分散在各個主管部門,基本上游離于財政預算之外,不受財政預算約束,更不受中央的控制和監管,因此滋生出大量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三亂”行為,影響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嚴重干擾了財經秩序,損害了地區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
(三)“三亂”的治理與土地財政之路的開辟
“三亂”嚴重干擾市場經濟秩序,損害經濟效率,其危害顯而易見,國家隨之出重拳治理“三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三亂”的治理直接堵塞了地方政府的“財路”,財政重壓之下探索新的生財之道隨之展開,土地這一稀缺資源作為“救命稻草”和“搖錢樹”被牢牢抓住,地方政府迅速走上了土地財政之路。
所謂土地財政,是指政府通過土地的資本化來實現財政創收的過程。土地收入涉及面比較廣,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兩部分:一是土地稅收收入,其又可分為直接稅收入和間接稅收入。其中,直接稅收入包括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間接稅收入主要包括與土地財政休戚相關的房地產和建筑等行業的稅收收入。二是土地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地租性收入和相關收費等等。
如表1所示,2003年-2007年,全國土地財政凈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年均為38%,而土地財政總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年均則高達60%,2007年達到最高,分別為44%和70%。另據資料顯示,2007年-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和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比例從0.35∶1上升到0.75∶1,和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比例從0.18∶1上升到0.41∶1。這標志著對于地方政府而言,2007年-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未扣除成本)占到地方公共財政總收入的2/5左右,占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比例達3/4。

誠然,1994年分稅制改革因省以下沒有完全貫通,致使縣鄉財政困難在“事權下移、財權上移”過程中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土地財政”問題。但這只是一大誘因,事實上,土地暴力生財機制的形成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土地所有權制度、征收與流轉制度等,限于本文的篇幅和研究視角,此處不再一一贅述。
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之路與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縣鄉財政困難、地方政府官員GDP導向的晉升激勵,使土地財政的膨脹成為現實,并已成為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特點。近年來,該模式在拉動我國地方經濟增長方面雖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從長期來看,該模式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大大增加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一)“土地財政”在短期內是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國式財政分權改革始終伴隨著垂直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完全掌握著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與任免,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權。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撥亂反正,將工作重心徹底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經濟改革與發展開始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頭等大事,經濟績效也就成為干部晉升的主要指標。于是,中央便設立了以GDP為核心的考核機制,以激勵地方政府貫徹中央的政策意圖。在這種政治體制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而且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同樣,具有自利行為的政府官員自然也會把權重較高的指標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通過做大GDP和上繳更多的財政收入來顯示政績,并以此獲得晉升機會。
為加快GDP增長,擴大GDP和財政收入規模,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可以自主安排財政支出的權力,將更多的資源用于支持經濟建設,特別是那些能夠直接推動經濟增長并有助于吸引區外資本(如FDI)的基本建設項目,從而形成了資本推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當然,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公共財政收入是有限的,除必保的社會事業發展支出、“三農”支出、民生支出和公用經費等支出項目外,可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微乎其微。為了獲取用于拉動GDP增長的投資,地方政府便圍繞土地大做文章,充分利用“土地財政”拉動地方經濟增長。首先,土地作為稀缺資源,可為地方政府融通投資資金。政府作為土地交易一級市場的壟斷者,自然成為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唯一供給者。于是,地方政府經常以低價征用集體土地,然后通過招標、拍賣、掛牌等方式高價出讓土地,從中獲取以土地出讓金為主要形式的壟斷收入。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對土地出讓收入安排的自主權,將其重點用于為地方經濟建設融通資金,有力地促進了地方經濟增長。同時,土地有助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土地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特別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土地越來越因稀缺而彌顯珍貴。于是,地方政府經常通過提供一定數量的土地作誘餌招商引資,以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從現實情況來看,這一手段是極為有效的,對于近年來的地方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拉動作用。
(二)“土地財政”容易導致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
前已述及,近年來,“土地財政”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影響,其通過為地方政府融通投資資金和招商引資有力地拉動了地方經濟增長,對我國的“GDP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土地財政”也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使地方經濟增長患上了嚴重的土地依賴癥,進而使我國的經濟增長存在著嚴重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持續性風險。首先,眾所周知,土地是稀缺資源,房地產業是一次性稅源,隨著土地資源的日益減少,地方政府的這一重要“財源”將逐步萎縮,“土地財政”的危機自然將會對經濟增長形成制約。同時,“土地財政”直接受制于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一旦房地產市場和土地市場“降溫”,罹患土地財政依賴癥的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將驟然上升,甚至可能引發財政危機,進而影響地方經濟增長。去年以來,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的加大,許多高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的地方政府叫苦連天,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劇,大量依靠土地出讓收入融通資金的地方建設項目被迫停工或停產,直接降低了地方經濟增長速度。這也是近期我國經濟增速不斷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土地財政”直接威脅著“穩增長”目標的實現
眾所周知,“穩增長”不僅與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緊密相聯,而且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土地財政”雖然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其不僅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且會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對“穩增長”目標的實現構成巨大威脅。
一方面,“土地財政”的過度膨脹會直接導致耕地的大幅度減少,進而威脅我國的糧食安全。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出讓收入,地方政府經常以低價征用集體土地,然后以高價轉讓其使用權,以賺取巨額壟斷收益。同時,許多地方政府經常假借“公益”的名義征用非公共用地,致使耕地不斷減少。有關資料顯示,在某省11個縣(1996年)200個最大的用地項目中,屬于公共事業的僅有42項,占21%;屬于政府機關的10項,占5%;而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企業148項,占74%,其中房地產項目35項,占18%。隨著耕地的大量減少,我國的糧食安全受到的威脅日益加劇。據估計,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屆時人均占有耕地僅在1畝左右,已遠遠低于國際標準,以如此少的土地來養活龐大的人口數量,不僅會對國內的糧食供應安全形成極大的威脅,而且也會對國際市場構成挑戰與壓力。
另一方面,“土地財政”的過度膨脹會直接導致失地農民的增加,進而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政府土地征用權的濫用會造成“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數量的激增。據統計,現在每征用一畝地,就會有1.5個農民失地。由于失地農民大多沒有社會保障,加之他們在城市再就業能力的低下,龐大的失地農民群體必然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威脅著“穩增長”目標的實現。
三、以“穩增長”為契機徹底消除土地財政依賴癥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經濟增速雖然保持在年初預期目標區間內,但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各項指標顯著下行,令決策層改變了預期,宏觀政策重心有所調整,再度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對此,我們要予以正確認識。“穩增長”并不是“保增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于穩增長的方式,如果不注意,又會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回到依靠投資和拼出口的老路上去。如果如此操作,一時的經濟增長數據可能保住了,但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大事將再次被耽擱,未來再調整的成本會更大。
我國“十二五”時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7%,與此相比,今年一季度7.8%的增速并不低。《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下調至7.5%,是2005年以來首次低于8%。這種主動選擇回調,為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發展質量預留了一定空間,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即經濟增長應該向注重質量轉變,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到首要地位。因此,我們要以“穩增長”為契機,創新體制機制,破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癥,消除“土地財政”對經濟增長的不良影響,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一)進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解除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之憂
前已述及,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全國財政收入強勁增長、地方財政總收入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縣鄉財政困難卻在“事權重心下移、財權重心上移”過程之中凸顯出來,并引發了“土地財政”等問題,其根本癥結在于省以下一直沒有真正實行分稅制。根治方法必須從此入手,對癥下藥,通過深化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加以解決。
首先,要加快推進政府財政層級改革,減少財政層級。其核心措施之一便是推行“省直管縣”體制,省和縣兩級政府之間直接搭建財力分配框架,并適時輔之以“鄉財縣管”體制,逐步將政府財政層級從五級簡化為中央—省—市縣三級。這是深化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與財權的必然選擇,也是建立統一規范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之關鍵所在。
第二,按照受益范圍和法律規定,明確劃分中央、省、縣(市)三級支出責任,并逐步將其法制化。尤其要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要盡快明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一般來講,中央政府應主要負擔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地方政府主要負擔地方性公共產品。具體來說,中央政府應統一負責國防建設、社會保障、郵政、鐵路及其他跨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城市公用事業服務(公交、水電氣供應等)、市縣鎮際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由各級地方政府負責;水利、生態環境、公立性文體衛教事業以及其他介于前兩者之間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負責。
第三,在明確劃分事權的基礎上合理劃分政府間的財權,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呼應、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級財政體制。中央應賦予地方必要的相對獨立的財權,包括必要的稅種選擇權和一定的稅收政策制定權,乃至允許地方政府依照法定程序自主開辟地方稅種和稅源,籌集適量的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資金。當然,作為權力制約,中央應具有地方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審批權。另外,我國要借鑒國際經驗,進一步規范各級政府間的稅收收入劃分辦法,保證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基層政府)都擁有主體稅種,以確保中央有能力調控總體經濟形勢,地方有財力實現分級預算、自求平衡。
第四,努力構建規范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考慮到我國目前基層財政仍然比較困難的客觀情況,對現行政府間轉移支付應做如下調整: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比例。改進一般性轉移支付測算辦法,鼓勵和支持那些屬于禁止和限制開發的地區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完善資源枯竭型城市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該類城市的支持力度。增加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發展。規范現有專項轉移支付,嚴格控制設立新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區分不同情況取消、壓縮、整合現有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進一步完善“因素法”,規范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依據與方法。
(二)健全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從源頭上根除土地暴力生財機制
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國有土地分級管理體制,加快建立責任、權利與義務相匹配,預算約束與預算激勵相對等的土地資本預算管理體系,健全和完善國有土地監管方式,規范土地出讓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允許農民按照市場價格進行土地的有序流轉,加快建立健全與土地流轉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如登記備案制度、糾紛調處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等等,積極為農民土地流轉提供法制保障。
(三)合理控制土地資源利用節奏和資本化進程,建立健全可持續的土地生財機制
土地作為稀缺資源,其開發和利用一定要控制好節奏。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期,合理制定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中長期規劃,保持合理的供地節奏,相對均衡地獲取土地出讓收入。要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將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總量納入年度供地計劃,統籌安排集體和國有建設用地的配置比例,控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節奏,逐步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體系。要切實加強土地利用監管,強化土地規劃、利用計劃管理和用途管制,努力提高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為均衡調節土地財稅激勵,消除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不良沖動,可借鑒香港經驗,從土地出讓收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建立土地收益儲備基金,以便平衡年度預算。
(四)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建立健全科學的政府績效評價體系
盡快調整目前對官員晉升的考核機制,清理各類行政績效考核指標,凡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定位或有利于各級政府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虛作假的一律取消;逐步淡化GDP增長以及與之相關的指標在考核體系中的重要角色,將晉升地方政府官員的標準轉到轄區內的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等方面上來,并將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偏好納入對官員晉升的考核體系中。著手建立一套有利于政府職能轉變,保證政府公正高效履行職能的績效評價體系,更加關注民生和民意,更加貼近百姓的生活,并突出“綠色GDP”、“幸福指數”等考核指標,激勵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好的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關注經濟社會發展與增進社會福利之間的平衡。
〔1〕賈康,劉微.土地財政:分析及出路[J].財政研究,2012(1).
〔2〕于長革.中國式財政分權與公共服務供給的低效率[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8(11).
〔3〕辛波,于淑俐.對土地財政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分析[J].農村經濟,2010(3).
〔4〕唐在富.中國土地財政基本理論研究——土地財政的起源、本質、風險與未來[J].經濟經緯,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