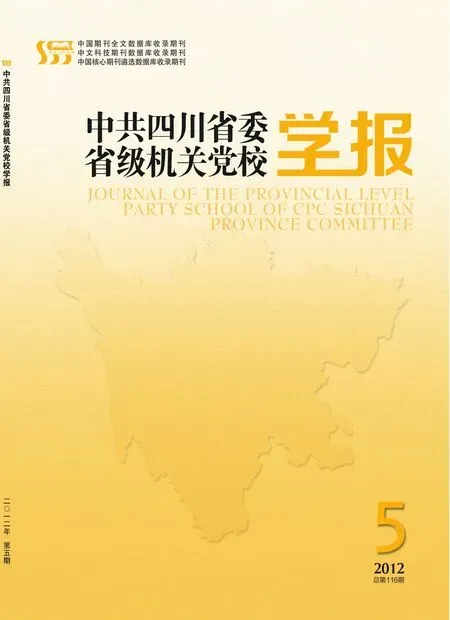組織中個體行動的一個分析框架
——對帕森斯“唯意志行動”模型的改進
劉曉峰 周 麗
組織中個體行動的一個分析框架
——對帕森斯“唯意志行動”模型的改進
劉曉峰 周 麗
人類關于自身行動的研究由來已久,并且一直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核心命題之一。在諸多理論中,帕森斯經典的“唯意志行動理論”影響深遠,有利于在分析層面上將具體行動抽象為科學理論,但其缺陷在于忽略了對組織中個體行動的分析。由于不同時代下組織類型有所不同,因而對組織中個體行動的分析只能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進行。在工業社會中,組織中的個體行動可以抽象為環境、行動者、手段和結果四個基本要素,行動者的能動性和行動的時序性使各要素能夠聯系在一起。
組織;個體行動;分析框架;帕森斯;行動理論;環境;行動者
有關人類行動的研究由來已久,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多數命題幾乎都與人類行為相關,有人甚至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學術責任就在于“觀察人行動的方方面面……并對人的行動做出觀察、探究、描述和說明。”〔1〕因此,可以說廣義上的行動理論并無嚴格意義上的學科歸屬,但是,若具體到研究問題的類型和認知視角,則不同學科中的行動理論就不同了,例如經濟學考慮的重點是人行動的成本和收益關系,政治學則更多地從權力、權威等概念出發探索政治資源的配置行為,社會學則“將人的行動視作更廣泛的一些型構 (figurations)的要素。〔2〕即將人的行動放在更大的社會網絡或系統中去觀察。本研究更多的是從社會學視角出發的,當然,我們并不因此認為各個學科在人類行動這個問題上是截然分開的。之所以做上述區分,一是為了避免因理論體系太過龐大而引起的理論評價上的困難,二是為了使視角更小一些以突出問題和便于展開分析。本文的目的是試圖在對帕森斯經典“唯意志行動”要素的批判性借鑒基礎上,提出一個在組織層面上個體行動的基本要素分析框架,以便在組織層面上更好地分析個體行動。
一、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動”模型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種哲學假設基礎上,認識論是這種假設的重要體現,也即研究者對客觀事物的哲學態度,不同認識論指導下的理論體系會有很大不同,因此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對不同的理論體系進行評價。帕森斯在建構其“唯意志行動理論”〔3〕過程中,便是從這個角度評價之前的理論的。他批判性地借鑒了唯心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哲學視角下的行動理論。他認為唯心主義的觀點錯在忽視人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外部約束的,但它用各種“理念”的概念去約束人們和社會的過程仍是有意義的,盡管有些‘理念’類型并不存在于常常被其要調節的、正在運行的社會生活中;而實證主義忽視人類思想復雜的符號功能和相對獨立的作用,過分強調可觀察的因果關系,很容易導致無休止的還原論;功利主義則把價值模式簡化為單純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它對行動者追求目標的敘述和對人們權衡利弊以及做出選擇能力的強調則值得借鑒。〔4〕
在此基礎上,帕森斯提出了“分析的實證主義”(或曰“分析的實在論”、“分析性現實主義”)(analytical realism),并將其作為該理論體系的認識論基礎,他認為“至少有某些一般科學概念不是虛構的,而是充分‘把握了’客觀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5〕這些“分析性概念”“并不對應具體的現象,而是對應從這些現象中可以分離出來和可以分析的要素。”〔6〕其研究目標就是用概念形成能理解社會重要特征的分析框架,而不被具體的經驗細節所掩蓋。因此,帕森斯和韋伯一樣,主張理論應當首先對社會現象進行細致的劃分,使其范疇化,并能夠反映社會現象的重要特征。
沿著這樣的認識論,帕森斯認為“有必要把歷史上關于基本社會過程的社會思想進行綜合,并將其分解為最基本的單元”,并指出“分析的第一任務就是把構成更為復雜過程和結構的最基本單位的系統特征從概念上分離出來。”〔7〕因此,帕森斯從傳統思想中挑選出來了一些概念并組合起來,作為其唯意志論行動理論的“終極單位”,也即“作為一個具體行動體系的組成部分的還能說得通的‘最小’單位。”〔8〕這樣的單位行動包括以下幾個要素: (1)行動者,即一個當事人;(2)目的,即“預期的未來事態與那在沒有行動者干預的情況下處境產生的未來事態之間的差別。”〔9〕; (3)處境,包括“條件”和“手段”,前者是行動者所不能控制的如外部的生態限制等,后者則是行動者可以改變的,如實現目標的方式方法; (4)行動者的“規范性取向”〔10〕,也即認為“行動者被各種價值觀、規范和其他理念所支配,這些價值觀、規范和理念影響著建立目標的和實現目標的手段。”〔11〕

圖1 唯意志論行動的單位〔12〕
帕森斯這種從復雜系統中抽離出基本概念的做法固然有利于在分析層面上將具體行動抽象為科學理論,但也存在弊端,一個顯著的弊端是不利于理解更復雜的具體行動體系,這是因為社會領域中的體系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機的,這些有機體系固然是由一些基本單位構成的,但是只有當這些基本單位的結合體復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些有機系統的某些伴生性的整體特征才能顯現出來。同樣的道理,如果將復雜行動體系抽象為所謂的“終極單位”,就像脫離了有機整體的部分一樣,“就不再是原來的自己了”〔13〕,就像亞里斯多德所言“離開人體的手就不能成其為人的手了”。顯然,帕森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試圖在《社會系統》一書中加以彌補,提出了“制度化”的概念,他認為單位行動中的行動者都有一定的價值和動機取向,這些決定了單位行動的基本方向,當這些單位行動相互影響互動時,就會產生某種較為穩定的互動模式,這種制度化的模式就是社會系統。〔14〕
這樣,在帕森斯那里行動理論的目標變成了理解社會系統是如何被價值觀、信仰、規范、動機等所制約的。這樣的目標轉換固然重要,但在行動單位和社會系統之間似乎缺少了一個中間層次,因為帕森斯所謂的社會系統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并沒有涉及一些次級行動系統,盡管對組織的研究最為常見的是從把個體作為觀察對象開始,但是,問題在于“這種分析必須從對個體層面的觀察轉移到利益沖突根本所在的系統層面”〔15〕。因此,我們主張在特定的組織層面上認識行動,嘗試建立一個次級行動系統視角下的個體行為分析框架。
二、組織中個體行動分析的一個新框架
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組織層面上如何更好地分析個體行動?我們的策略和帕森斯所提倡的“分析的實證主義”方法相似,也是主張從現實中抽象出概念來,并用這些概念形成能夠理解社會現象特征的分析框架,而不被具體的經驗細節所掩蓋。我們從組織的個體行動抽象出以下幾個基本分析要素:
(一)環境
這里的環境不同于帕森斯的“處境”,在帕森斯那里,行動的“處境”被粗略地分解為行動的“條件”和“手段”,前者是行動者所不能控制的,后者是行動者所能控制的。〔16〕盡管帕森斯聲稱反對還原論,批判那種“將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歸結到某種生物選擇理論”的做法,〔17〕并明確指出就行動理論的目的來說,沒必要或不值得在物理的、化學的或生物學的層面上對人類行動進行分析,〔18〕但事實上帕森斯“處境”概念的外延仍然過于微觀,他更強調行動者面臨的各種環境條件 (如行動者的生理構成、遺傳特征和外部的生態限制)對行動者目標和手段選擇的影響。〔19〕盡管我們不否認這種影響的存在,但在組織層面上,過多地考慮行動者個體的先天性條件對行動的影響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在一個特定組織中,個體無法改變的先天性條件相對于個體所置身的外部環境而言對行為的制約能力并不明顯,即便是對行動有重要影響的行動者價值觀等因素,也往往被視為是行動者將外部環境內在化的結果。
我們在這里將組織中個體行動的環境進一步分為以下兩個層面:社會層次 (組織外環境)和組織層次 (組織內環境)。
組織外環境是指組織外部大的社會系統,主要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三個方面。組織外環境與組織行為的關系問題是組織理論中的經典論題之一,但在最初的組織理論中,組織外環境因素卻是被忽視的。理性系統模式中的主要理論著作以及自然系統模式中早期的一些著作基本上沒有關注到外部環境與組織的關系問題,只是到了自然系統模式后期如賽爾茲尼克的制度學派、帕森斯的AGIL模型才開始重視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到了開放系統模式提出控制論、系統設計、組織權變等理論之后,環境才真正成為組織研究的核心對象之一。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組織環境是如何影響組織行為的呢?筆者認為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途徑:一是社會化,即個體在進入組織之前以及進入組織之后,都無時無刻不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個體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不斷被社會化的過程,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最基本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并最終影響了個體行為的基本取向。拉爾夫·林頓研究了社會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角色,并指出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人格標準。林頓進一步分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存在一些共同的人格因素,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個緊密結合的綜合結構,即稱為這個社會的“基本人格型” (Basis personality Type)。這個綜合結構的存在,提供給社會成員共同的理解方式和價值觀,并且使社會成員對相關的價值環境做出一致情感反映成為可能。〔20〕二是合法化。合法化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組織層面的合法化,即環境中的組織通過不斷調整自身的規則、行為方式、組織目標等方式不斷適應組織外環境以取得組織合法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組織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結構、目標、組織規則、組織文化等。第二個階段是組織中個體的合法化過程,也即組織的結構、目標、規則、文化等又進一步形塑個體行為的過程。個體要想在組織中生存下去,必須接受這些因素的制約,這也可以被認為是組織中的個體取得“組織合法性”的過程,這個時候個體從一個社會人轉化為社會人和組織人的結合體。
不難看出,我們上面所說的合法化途徑,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我們即將要討論的組織“內環境”的問題,也即那些存在于組織內部的,個體行動者之外的諸多因素(如組織結構、組織目標、組織規則、組織文化等)是如何影響個體行動的問題。在這些要素中,我們主要強調組織規則對個體行動的影響作用,這是因為我們認為組織規則是其他諸環境要素特征的外在體現,另外組織規則對個體行為也具有更為直接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解釋組織規則是如何影響個體行為的,我們進一步將組織規則分解為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這是一種流行的劃分方式,韋伯在論述人類社會的規范時便承認“在一個群體中被一致認為有效的規范,絕非全部是‘法律規范’”〔21〕,盡管韋伯是正式規則的積極倡導者,但他也承認即便是在官僚制的組織中,影響成員行為的除了正式規則外,還有許多非正式或曰潛規則,有些學者甚至“把正式系統看作是對于這類非正式實踐的一種回應,看作是對這類實踐所引發的諸種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22〕在此我們無意對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加以界定,我們只是希望在這里提出一個分析思路,以便于用更具體的經驗性材料觀察具體的組織現象。
(二)行動者
在組織研究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種思維邏輯。一種邏輯過分信任組織的理性能力,強調優秀組織所帶來的效率優勢,而對此不加懷疑,這本質上是一種簡單決定論,這一思維邏輯源于早期的“泰勒主義”;第二種邏輯可以被視為是對上一種邏輯的矯枉過正,它過分夸大了組織的“機械性”危害,強調組織可能產生的對人類所構成的壓迫性威脅。這兩種思維邏輯的錯誤根源在于,他們都忽視了組織是由“行動者 (即能動的人)”構成的這一事實,當“行動者”這一“螺母”被安裝在組織這部機器上的時候,便注定了它要比世界上任何一種常規機器要復雜得多。因此作為行為的建構者和實施者,行動者這一要素是不容忽視的。
上述的復雜性源于組織行動者對行為選擇的多樣性,就已有的相關理論來看,我們認為有兩種簡單化的理論模式值得警惕。
第一種簡單化的理論模式受組織心理學的影響較大,特別是馬斯洛的動機理論〔23〕提出以后,很多組織研究者試圖從個體的需要,特別是從心理需要以及這些需要產生和進化的規律出發,解釋行動者與組織之間的關系。這一簡單化模式把組織視為一種完全抽象的實體,并且認為行動者與組織是相互對立和分離的,另外,一個意料之中的后果是導致了個體諸種心理需要的物化傾向,這并不能更好的解釋人類行為的復雜性。第二種簡單化的理論模型則從類似于市場經濟的模式出發來研究個體與組織間的互動行為,即假設個體是經濟人,個體始終試圖得到至少等價于他有效付出的回報。〔24〕對行動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帶來了行為分析的復雜性。行動者在行動之前,已經建立了一個理性的行為選擇評價標準,這個標準既來自于他的自然歸屬群體 (客觀決定要素),也來自于他自身 (主觀決定因素)。
盡管看上去第二種簡化模式要比第一種模式復雜,似乎也更為全面,但和第一種模式一樣,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先驗性模式,存在與實踐相脫離的問題。
筆者對特定組織所進行的一段時間的田野觀察發現①筆者于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在山東省某鄉鎮政府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田野調研。,組織中的行動者及其行為的選擇更接近于法國組織學派的觀點,即認為組織中的行動者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行動者的計劃和目標是多重的,有時甚至是含混的、矛盾的。行動者很少有明確的目標,而嚴密的計劃則更少;2.簡單的用理性行為或者非理性行為已經不能很完整地解釋復雜的個體行為現象了,策略性行為似乎有更大的解釋作用,策略概念的實用價值在于,它既適用于看上去最為理性的行為,也同樣適用于看似完全無規律的行為;〔25〕3.行動并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為的綜合,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行為流,行動也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單個分離的意圖、理由或動機組成的,而是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4.行動是行動者能動性的體現。行動者具有運用資源的能力,或多或少總會掌握一定資源,能夠介入或者干預這個世界,并且影響事件的特定過程或事態,因此由不斷發生的事件所構成的世界并未具有一個確定的未來;5.行動具有建構性。組織規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行動的結構性后果,因為作為能知和能動的行動者在各種實踐活動中能夠不斷地利用各種規則和資源,并且在各種實踐活動中再生產出規則,因而結構既不斷融入實踐活動中,成為行動的組成部分,同時又在實踐活動之中再生產出來,成為行動的結果。
(三)手段
組織中的個體互動行為必然要通過某種手段或方式表現出來,個體行動的手段有兩種:權力運作和社會交換。
權力運作是組織中最基本的個體行為方式,它是以組織所賦予的正式權力為資源的行為方式。眾所周知,權力來源于拉丁文“Potere”,原意為“能夠”,或具有做某事的能力。在不同的組織中,權力的來源或基礎是不同的。按照韋伯的觀點,權力部分地依賴于權威,而權威又可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26〕
這里所說的“權力運作”中的“權力”是以法理型權威為依賴的,是受組織中正式規則制約的個體行動方式。在權力運作行為中的個體是一種“組織身份個體”,其行為要符合某種特定組織身份要求,當個體被組織正式規則安置于某一組織職位上的時候,便具有了某種特定的組織身份,組織中的個體對“組織身份個體”的行為具有較強的預期。因此,有不少“權力運作”看上去都是在“按部就班”地進行,是可預期的。組織中個體行動的另一種手段是社會交換,在霍曼斯那里,社會交換的內涵較為寬泛,幾乎把一切社會活動都看成是交換行為,而布勞則把交換行為理解為特定的交往,他將社會交換定義為:“人們被期望從別人那里得到的并且一般來說確實也從別人那里得到了的回報所激勵的自愿行為。”〔27〕在他看來,社會交換具有如下特征:(1)參與交往各方都期待他們回報,一旦他人停止了所期待的回報,這一交往關系便會停止;(2)相互信任是社會交換的基礎,同時社會交換必須是雙方的自愿性行為〔28〕。
筆者所指的社會交換要比布勞的社會交換的范圍要寬泛一些,但卻又比霍曼斯社會交換的范圍要小,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組織中的社會交換加以限定:一是發生在組織中行動者個體之間的自愿行為,因此同布勞一樣,我們將那些采用類似“肉體強迫”手段獲得的交往行為排除在外;二是建立在信任或社會心理承諾基礎上的交往行為,因此我們把政治性契約和經濟性契約之下的行為排除在外;三是動力來源于習慣、社會文化規范的壓力或者對他人回報意愿的期望,這就不同于布勞將“沒有目標取向”和“遵從內在化規范的行為”排除在外的觀點〔29〕;四是該行為面臨先賦組織環境的影響,因此行動者個體有別于一般社會中的原子化個體,在進行社會交換的過程中他們會考慮到其它交換形式 (如政治性交換)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不能僅從行為主義心理學角度做出解釋,這有別于霍曼斯的行為交換理論。
(四)結果
組織中個體行動的“結果”是一個不易界定的概念,它類似于個體行動的影響,但結果和影響又有不同,筆者認為影響的外延更大,由個體行動引起的變化都可以被認為是影響,但我們認為只有那些由個體行動所引起的具有一定穩定性,呈現出某種特點和規律的客觀變化才能稱之為結果。也可以說,這里的“結果”是比個體行動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宏觀的一種結構性表現,如組織規則的變革或組織整體性行為等。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討論社會學領域有關微觀和宏觀研究思路的分野問題。
在社會學領域有關個體行為的討論往往是在“微觀-宏觀”二分框架下展開的。在人們眼里,微觀研究視角主要關注的是“行動者”的各種活動,這些問題應該交給符合互動論或常人方法學這樣的理論立場來處理;而另一方面,人們認定,宏觀社會學的領域就是分析對自由活動施加限制的那些結構性制約因素〔30〕。這種觀念暗含了研究者在認識論上的某種對立,他們將“微觀”與“宏觀”視為敵對的兩種認識論取向,認為研究者似乎只能在二者之中做非此即彼的選擇,例如,戈夫曼就有意拒絕關注涉及到更大范圍的社會組織和歷史問題,在其背后隱藏的認識論是,人們只需要通過微觀社會學的這種研究,就完全可以發現社會生活的基本現實〔31〕。與此相對,宏觀社會學的倡導者們則認為,對微觀個體行為的研究是瑣碎無聊的,而那些涉及范圍較大的問題才具有意義。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上述微觀和宏觀研究思路的分野并沒有消退,特別是當功能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者是二者之間的某種結合支配社會理論的時候,這種分野反而日益突出。與此同時,另有一部分社會學家開始試圖填補所謂微觀和宏觀之間的鴻溝,例如柯林斯就認為,“要想邁向更為成功的社會學科學,至關重要的一步是努力以更為連貫一致的方式重新構想宏觀社會學,把它奠基在徹底經驗性的微觀基礎之上。”〔32〕換句話說,他主張通過對“結構現象”進行“微觀轉譯” (microtranslation)才能推動社會學的發展,這種轉譯產生的理論會比現有的各種宏觀社會學理論具有更強有力的經驗性基礎。
然而遺憾的是,柯林斯簡單的將宏觀社會現實理解為微觀經驗的簡單累積,他曾明確指出“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如果不涉及數量、時間和空間的話,就只是微觀環境中的行為的‘結果’。”〔33〕
筆者贊同柯林斯在更宏觀層面上探尋微觀個體行為結果的做法,認為組織中個體行為的結果主要表現在組織規則和以組織為單位的整體行為上,當然,在更宏觀的層面上,例如對組織外在環境的影響盡管也存在,但并不是本次的研究重點。另外,我們認為組織內的個體行動塑造結果的過程要比柯林斯所謂的“微觀聚合”要復雜的多,作為結果的組織規則和組織整體性行為并不能通過微觀面對面的個體互動行為就能一探究竟,而是微觀個體行為在長期互動中逐步塑造而成并仍在持續變化的社會現象,這一過程甚至復雜到難以準確全面的對其加以描述,因此我們只能以某個時間點中靜態的“結果”來反映結果,并且這個靜態的“結果”也并非個體行為的所有結果,僅是我們認為的若干值得關注的結果的外在體現而已。
三、結束語
本文將組織中的個體行動抽象為環境、行動者、手段和結果四個分析要素,但接下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些基本分析要素在實際行動過程中是如何被聯系在一起的呢?筆者認為,以下兩個條件為上述聯系提供了可能:一是行動者的能動性。在若干行動鏈條中,作為行動唯一載體的行動者看上去更像是一個轉換器,他們將各種環境因素進行分析和利用,并通過合適的手段轉化為外在行動。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始終是積極能動的;二是行動具有時序性。所謂時序性是指行動的一些特征是在時間-過程向度上呈現出來的,我們可以通過觀察不同時序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和行動各要素在時序上的總體態勢來分析組織中的個體行動。
本文有關組織中個體行動的研究僅僅是在理論層面上的討論,實際組織生活中的個體行動要比這復雜得多。因為在實際的組織行動中,一方面某個行動往往是多個個體互動的結果,另一方面,組織中的行動也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多個行動相互交織在一起。因此本文僅僅為組織中的個體行動提出一個分析框架,目的是為宏觀組織理論提供微觀基礎,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帕森斯“唯意志行動理論”在分析次級行動體系中的不足。另外,筆者希望在后續研究中利用上述框架通過進一步的經驗性研究,來探索特定組織中個體行動的邏輯。
〔1〕〔2〕齊格蒙特·鮑曼,蒂姆·梅.社會學之思〔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4,5.
〔3〕〔5〕〔6〕〔8〕〔9〕〔10〕〔13〕〔16〕〔18〕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M〕.New York:Free Press,1968.P.730,P.730,P.731,P.49,P.44,P.32,P.44,P.45,P.47.
〔4〕貝爾特.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48.
〔7〕〔11〕〔12〕〔14〕〔19〕喬納森·H.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 (第七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37,37,38,39,37.
〔15〕Huber,J,1990.Macro-micro links in gender stratific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5:PP.1-10.
〔17〕烏塔·格哈特.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7.
〔20〕拉爾夫·林頓.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會與個體關系之研究〔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01.
〔21〕閆洪芹.公共組織理論:結構、規則與行為〔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9.111.
〔22〕〔24〕克羅齊耶.行動者與系統:集體行動的政治學〔M〕.上海:上海人們出版社,2007.30,32.
〔23〕A.H.Maslow,Ma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New York,Harper,1954.
〔25〕Berger&T.H.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Doubleday,1966.
〔26〕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rans.A..M,Henderson and Talctt Pars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333.
〔27〕〔29〕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46,38.
〔28〕謝立中.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290.
〔30〕〔33〕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M〕.北京:三聯書店,1998.233,235.
〔31〕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M〕.黃愛華,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2〕Randall Collins,Micro-translation as a theory-building strategy,K.Knorr-Cetina and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London:Routledge,1981),P.82.
【責任編輯:陳學明】
D630.1
A
1008-9187-(2012)05-0091-05
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鄉土社會資本與鄉鎮干部行為研究”(SK2012B196)
劉曉峰,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講師,博士,安徽 合肥 241003;周麗,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江蘇 南京 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