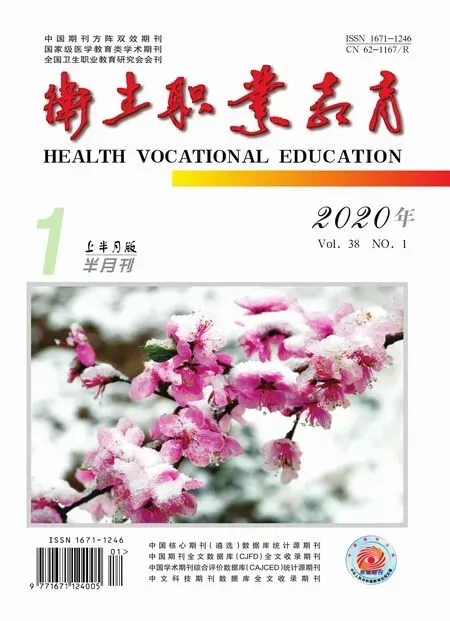OSCE教學模式在醫院臨床實習教學中應用效果的Meta分析
彭雅琴,高國貞
(1.廣州醫科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2.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廣東 廣州 510000)
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也稱多站式臨床考試,由英國Dundee大學的Hadren[1]于1975年提出,針對需考查的能力,創建一系列模擬臨床情景的考試站點,受試者按規定依次接受各考站考核,以最終成績作為結果評定學生綜合素質[2]。OSCE被廣泛應用于國內外醫學教育領域,并被認為是評估醫學生臨床能力的“金標準”[3]。1984年,麥克馬斯特大學Hamilton教授首次將OSCE引入北美護理領域[4]。OSCE在我國護理領域開展較晚,仍處于探索階段[5]。雖有為數不少的護理教育者對OSCE進行了探討,但研究結果卻不甚一致,各類結局指標從單個到數十個不等,不一而論,差異較大,在其教學效果上存在較大爭議。相關Meta分析也多局限于學院教學,在臨床實習教學中未見相關分析。因此,OSCE對護理臨床實習教學的影響尚需進一步分析。本文將OSCE教學模式應用于護理臨床實習教學,并就其影響進行Meta分析,為今后的臨床實習教學改革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檢索策略
本研究納入國內外主要中外文數據庫,檢索時限為建庫至2018年11月。檢索數據庫包括PubMed、Medline、Cochrane Library、Embase、EBSCOhost、Science Direct、CNKI、VIP 和萬方。文獻檢索以主題詞+自由詞互為補充。中文檢索詞為“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護理或護生”“護理教學”“專科或本科或研究生”。外文檢索詞為“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nurs*education or teaching”“nurs*students”。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1)研究類型:隨機對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2)研究對象:護理專業臨床實習生,包括本科生和專科生。(3)干預措施:對照組采用傳統教學模式,即教師根據教學大綱集中進行理論講解和操作示范,之后輔導學生進行自主練習;觀察組采用OSCE教學模式,即教師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設置一系列模仿臨床真實情景的考站和標準化病人,對護生臨床能力進行反復訓練和評價。(4)結局指標為可進行量化的特異性效應指標,如考試成績、滿意度、評判性思維能力等。
1.2.2 排除標準(1)研究過程包含其他干預方法,無法判斷OSCE教學模式對教學效果的影響的研究;(2)非醫院臨床實習教學研究;(3)研究對象除研究生、本科及專科護生外,還包括其他類別人員;(4)研究設計不嚴謹,重要資料無法獲得的研究;(5)無法獲得全文和重復發表的文獻。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筆者獨立進行文獻檢索,兩名研究者分別通過瀏覽標題和摘要進行初步篩選,對于初步納入的文獻進行全文閱讀,對存在爭議的文獻進行討論,必要時請第三人協同判斷是否需要納入。采用Excel制作表格并進行資料提取處理,需提取的內容:(1)文獻的基本資料:作者、發表年份、基線資料等;(2)研究的干預方法和結果指標;(3)文獻質量評價。
1.4 文獻質量評價
文獻質量評價由兩名研究者共同完成,依據《Cochrane指南》(5.1.0版本,2011年3月更新)中描述的7種一般偏倚來源(隨機分組的產生、分配隱藏、對研究者和受試者施盲、研究結局盲法評價、結局數據的完整性、選擇性報告研究偏倚和其他偏倚),分別評定為3個等級:低度偏倚風險(Low Risk)、不清楚(Unclear)和高度偏倚風險(High Risk)。若是全部滿足“低度偏倚風險”標準,表明納入文獻偏倚風險較小,評定為A級;部分滿足“低度偏倚風險”標準,表明納入文獻存在一定偏倚,評定為B級;完全不滿足上述“低度偏倚風險”標準,表明納入文獻存在偏倚的可能性較大,則評定為C級。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evMan 5.3軟件進行異質性檢驗和Meta分析。本研究提取的結局指標中,連續型變量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td Mean Difference,SMD)作為研究效應指標,以消除各研究因測量單位和方法差異帶來的影響;二分類變量則采用OR值(Odds Ratio)作為效應指標。各效應量均計算95%置信區間(95%CI),P<0.05表示存在顯著性差異。首先對納入研究進行異質性檢驗,異質性以Q統計量檢驗和I2檢驗來判斷,當Q統計量檢驗中P<0.01或I2檢驗中I2>50%,表示存在異質性[6-7]。I2為研究異質性引起的變異百分比,常用于Meta分析中異質性的判斷。I2<50%表示異質性可接受,I2為50%~75%表示存在中度異質性,I2>75%表示存在高度異質性[8]。對于存在中度或高度異質性的進行敏感性分析或亞組分析,以明確異質性來源,并盡量消除或降低異質性,進而提高Meta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對于效應模式選擇,當結果不存在異質性或異質性較低時(I2<50%),采用固定效應模式,反之(I2≥50%)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式。最后利用漏斗圖判斷納入文獻是否存在發表偏倚。
2 分析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步檢索到相關文獻968篇,其中中文文獻478篇,外文文獻490篇。利用EndNote軟件排除重復文獻160篇,經兩名研究者獨立閱讀標題及摘要,排除不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的文獻774篇后,初步納入文獻34篇。按照本研究設置的納入標準與排除標準對初納文獻進行全文閱讀,并對所引參考文獻進行追查,參考文獻中未發現符合文獻。文獻篩查結束時,本研究最終納入文獻12篇[9-20],共包含16項相關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如圖1所示,納入文獻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資料
2.2 Meta分析結果
本次Meta分析納入的16項研究共包含結局指標20個,但由于部分結局指標涉及的文獻過少或僅一篇,難以進行綜合評價,故本次Meta分析選擇了涉及研究數量較多的7個結局指標作為效應指標進行系統評價。
2.2.1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理論成績比較 來自 6 篇文獻[9,11,14,17,19-20]的 9 項研究將理論成績作為結局指標,共納入實習護生892名,比較OSCE教學模式與傳統教學模式對實習護生理論成績的影響。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7%),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Meta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傳統教學組,OSCE教學組實習護生理論成績提高顯著(P<0.01,見圖 2)。

圖2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理論成績分析的森林圖
2.2.2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操作技能比較 3項研究[13,14,16]比較了兩組實習護生操作技能,共納入232名護生。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7%),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傳統教學組,OSCE教學組實習護生操作技能提高顯著(P<0.05,見圖3)。

圖3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操作技能分析的森林圖
2.2.3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評判性思維能力比較 兩項研究[19-20]比較了兩組實習護生評判性思維能力,共納入372名護生。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8%),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Meta分析結果顯示,OSCE教學組實習護生評判性思維能力提升情況明顯優于傳統教學組(P<0.01,見圖4)。

圖4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評判性思維能力分析的森林圖
2.2.4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溝通能力比較 3項研究[9-10,20]就兩組護生溝通能力進行了比較,共納入護生342名。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8%),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Meta分析結果顯示,OSCE教學組實習護生溝通能力提升情況明顯優于傳統教學組(P<0.01,見圖5)。
2.2.5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健康教育能力比較3項研究[13,15,20]比較了兩組實習護生健康教育能力,共納入護生279名。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8%),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OSCE教學組實習護生健康教育能力提升情況優于傳統教學組(P<0.05,見圖6)。
2.2.6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突發事件應對能力比較 兩項研究[13,20]就護生突發事件應對能力進行比較,共納入護生151名。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9%),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突發事件應對能力提升情況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圖7)。

圖5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溝通能力分析的森林圖

圖6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健康教育能力分析的森林圖

圖7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突發事件應對能力分析的森林圖
2.2.7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實習護生對教學模式的滿意度比較 3項研究[12-13,18]比較了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對教學模式的滿意度,共納入護生551名。各研究間存在異質性(P<0.01,I2=94%),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式。Meta分析結果顯示,OSCE教學組護生對教學模式的滿意度高于傳統教學組,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圖 8)。

圖8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教學模式滿意度分析的森林圖
2.3 漏斗圖分析
以實習護生理論成績作為效應指標,對納入的6篇文獻[9,11,14,17,19-20]的 9 項研究進行漏斗圖分析,如圖 9 所示,大部分研究落于圖形上部,表示樣本量充足,標準誤小,分析結果準確性較高;圖形不完全對稱,因而不能排除發表偏倚存在的可能,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文化特性,陽性結果的研究較陰性結果的研究更易發表。其余各項結局指標因納入研究過少,故而無法繪制漏斗圖進行分析。
2.4 敏感性分析
森林圖和漏斗圖生成后,針對各項結局指標,分別去除樣本量最大或最小的研究后,在提高護生理論成績、評判性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方面,SMD值和95%CI值無本質變化,結果穩定;部分結果發生變化:OSCE教學模式在提高護生滿意度、操作技能、健康教育能力3個結局指標方面的優勢與傳統教學模式相比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而在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方面的優勢則明顯大于傳統教學模式,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針對此結果,本研究以受試者學歷(本科/專科)、OSCE考站數和標準化病人類別(非醫學專業人員/護士/不詳)分別進行亞組分析,發現OSCE考站數和標準化病人類別為影響結果穩定性的主要因素,為主要異質性來源;去除此二重因素影響后,Meta分析結果穩定性好,異質性出現不同程度降低。

圖9 OSCE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護生理論成績分析的漏斗圖
3 討論
3.1 納入文獻的方法學質量
采用《Cochrane指南》(5.1.0版本)中描述的7種一般偏倚分別對文獻進行評價。通過分析全文,從研究分組、實施、結局指標測量、報告等方面對納入文獻進行綜合質量分析,發現納入的12篇文獻[9-20]均為B級,文獻質量一般。納入的12篇文獻中,在對研究者和受試者施盲、研究結局盲法評價和其他方面可能存在較大偏倚風險:所有文獻均未報告對研究者施盲,除1篇文獻[11]描述了盲法測量結局外,其余文獻[9-10,12-20]均未報告盲法,可能會導致主觀因素雜糅;多篇文獻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偏倚[9,11,12-18]。除此之外,其余4種一般偏倚風險較小。在研究對象基本信息方面,所有文獻均報告了學歷,9篇文獻報告了平均年齡,8篇文獻報告了性別比,所有文獻均報告觀察組和對照組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顯著性,具有可比性。
3.2 OSCE教學模式對護理臨床實習教學的影響效果有待進一步研究
近年來,隨著護理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開展,OSCE作為一種新的考核形式受到護理教育者關注。本研究納入的12篇文獻,涉及的結局指標多達20項,除納入Meta分析的7項指標外,還有臨床處置能力、臨床管理能力、職業價值觀、整體護理能力等13項結局指標,因涉及研究太少,無法綜合評價其可靠性。
3.2.1 OSCE教學模式有助于提高護生理論成績、評判性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 納入Meta分析的7項指標中,結果證實OSCE教學模式能有效提高實習護生理論成績、評判性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這與王虹等[21-22]的Meta分析結果一致。OSCE教學模式下,教師通過應用標準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SP),并借助相關環境和物品,模擬臨床真實情景,針對待考核的不同能力設置不同考站,護生想要通過考站,便要對考站中SP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獨立判斷并結合所學知識進行相關處理,而不是簡單記憶。在此過程中,護生的理論知識得以鞏固,并鍛煉了評判性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改變了死記硬背的學習模式。
3.2.2 OSCE教學模式在提高護生臨床能力和滿意度方面效果尚需進一步驗證 在操作技能、健康教育能力、護生滿意度和突發事件應對能力方面,敏感性分析結果提示Meta分析結果穩定性差,雖進行了亞組分析,對相關干擾因素予以控制,但由于分組后涉及研究較少,難以進行綜合判斷,尚需分析更多設計更為嚴謹的研究結果方可判定。這與黃培雯等[22]關于健康教育能力的研究結果一致。除此之外,OSCE教學模式對護生滿意度和突發事件應對能力的影響在王虹等[21]和黃培雯等[22]的Meta分析結果中均未提及。這可能是由于OSCE在我國護理教育領域尚未有明確規范的實施方案和標準,各教學醫院教學條件和人員差異較大,且其臨床工作繁忙,因而OSCE具體實施情況各異所致。OSCE教學模式對護理臨床實習教學的具體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
3.3 OSCE考站數和標準化病人來源為影響OSCE教學效果的關鍵性因素
由于OSCE教學模式在我國護理教育領域的應用尚不成熟,缺乏客觀標準,不同研究者在實施過程中主觀性較強,這也是造成本次Meta分析各研究間異質性較強(I2>75%)的主要原因。考站是OSCE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其實施的基礎和載體,而結局指標則是考站建立的目的與指引,這兩者對于OSCE的開展至關重要。從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納入的12篇文獻考站數和結局指標各不相同,除兩篇文獻[11,13]考站數不詳外,其余文獻報告了考站數為3~10站,所測量的結局指標為1~8個,且在考站與結局指標的設置上未見具體方法學報告。標準化病人(SP)是OSCE教學順利開展的另一個關鍵,然而,其培訓及應用情況同樣缺乏規范和標準。在納入的文獻中,除3篇國外文獻[9-11]是面向社會招募非醫學專業人員作為專業SP外,國內文獻中 3 篇文獻[12,15,19]采用臨床帶教護士作為 SP,1 篇文獻[18]采用普通臨床護士作為SP,1篇文獻[14]采用電子模擬人和真實病人作為 SP,另有 4 篇文獻[13,16-17,20]未報告 SP 應用情況。在國內的研究中,SP的招募和培訓同樣缺乏具體方法學報告。這些是我們在以后的研究中應積極探索解決的問題。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1)納入文獻質量不高,偏倚風險評級均為B級;(2)由于語言限制,文獻檢索范圍僅限于中文和英文,且由于國內外文化差異大,符合標準的國外文獻較少,可能會對研究結論的得出和推廣造成影響;(3)由于客觀情況,部分結局指標的分析納入研究較少,不能排除單篇文獻對研究結果造成較大偏倚的可能;(4)納入的各研究間研究異質性較高,這可能是由于OSCE教學模式在我國的發展不成熟,實施情況差異較大所致,因而采用的隨機效應模式可能導致檢驗效能降低。
4 結論
OSCE教學模式下,教師通過設置考站,應用標準化病人,模擬臨床真實情景,針對護生綜合素質進行考核,彌補傳統教學模式以理論成績和操作技能判斷學生能力的不足。本研究顯示,OSCE教學模式在提高實習護生理論成績、評判性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方面明顯優于傳統教學模式;影響OSCE教學效果的關鍵性因素為OSCE考站數和標準化病人來源,在未來的研究設計中應著重注意。雖然當前OSCE教學模式在我國護理教育教學中的應用還不成熟,卻能為護理教學模式改革提供新的方法與思路,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