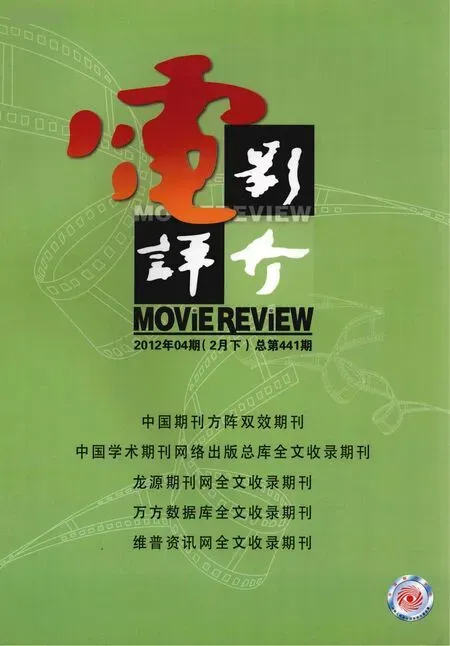電影《金陵十三釵》人物身份芻議
作為電影文本的《金陵十三釵》與原著文學文本有著直系血緣關系,但其效果呈現卻有很大區別,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將電影《金陵十三釵》視為獨立文本存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影視改編過程中人物身份設置的創造性變遷。電影中出現的人物身份可分為:以玉墨等為代表的秦淮妓女、以李教官為代表的中國軍人、以書娟為代表的教會學生以及洋人入殮師約翰。
《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原型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并且在多部文學及影視作品中以多種形式反復出現,因此這些作品從題材上皆被視為有關大屠殺的“南京”敘事。在“南京”敘事中始終未曾脫離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主流意識框架,作為救贖模式的經典故事,創作者要追求普泛化的情感表達并創造個性化的審美旨趣,其中人物身份背后的內涵延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電影《金陵十三釵》中每個表層身份背后都熔鑄了對于身份類型的深層內涵,對這方面的深入探討更是解讀這部電影的重要途徑。
一、妓女與俠女
以玉墨為代表的秦淮河畔妓女是故事的核心角色,妓女形象自古有之,也是藝術作品中千姿百態紛繁復雜的表現對象,但在電影《金陵十三釵》中這些女子的身份背后首先隱藏的是俠女身份。她們是救贖主題的具體實踐者和殉道者,并在此過程中一步步將自己的妓女身份淡化直至徹底置換,最后以俠女的精神本質走向傳奇書寫,從而在身份定位上造成巨大的審美落差,實現戲劇突轉,完成英雄敘事。其實她們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具有連續性的身份結構,與尸骸遍野的悲涼景象和殘暴駭人的殺戮氛圍形成鮮明對比的熱出場——扭捏妖嬈的身姿、紛繁魅惑的衣著、煙花教坊式的怨憐喧嘩,但其中主要視角又落在對玉墨內斂、含蓄、貴氣、神秘等精神氣質的呈現,儼然是對于傳統“俠風”的摹寫,這些都表明了她們身份的特殊性,也注定了她們奪目的主體表達,很大程度上消減了傳統書寫中常規的負面表達,也標志著對其身份的獨特審視與肯定。十四個秦淮妓女華貴風情地大步走向教堂的鏡語表達更是帶著濃重的俠士情懷,與大氣灑脫放蕩不羈的青樓風范相結合,協調統一的情感契合把這些女子通過性和肉體去交換物質生存的現實尷尬遮蔽不見,同時隱去了對其社會身份和性別價值的公眾認證,只剩下單純美好的樣貌與矛盾又神秘的欲望。
這種對于女性主體張揚的審美再現,絕不是片面的以隱去負面效應來突出正面效應。這些妓女也并非屬于“惡之花”式放棄靈魂、歡縱肉欲、沉淪墮落的底層妓女,而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反而更帶有“同是天涯淪落人”般強烈情懷標識的人物群像,但又區別于經典文本《桃花扇》中李香君式“抨擊奸佞熱愛國家的妓女形象”[1],而是將有情有義置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宏大主題之下,她們關心的核心問題與教堂里的教會學生一樣。對于這些妓女的俠義書寫姿態也是她們身份轉變的開始,從妓女身份變為俠女身份的過程在經歷了她們與教會學生的沖突之后隨著日本軍隊的介入也變得清晰起來。教會學生在日軍進入的剎那放棄鉆入地窖而掩護她們的行為,讓敘事關注從妓女們的外在樣貌和身份轉入其內心層面的深層探尋,她們被學生的義舉所感染,也喚醒了外在社會身份掩蓋之下的“情義”,雖然是被動改變,但無疑這種敘事邏輯是完全合理的。妓女身份也隨之合理地走出傳統的邊緣定位,融入到主流的社會價值中,進入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直到最后選擇代替女學生去赴一場生死未卜的災難,舍身而取義。這種救贖模式,是典型報恩式的俠義表達模式。
一直被排擠在社會倫理之外的妓女形象,道德和政治責任是不必負的,她們的正常存在恰是威脅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因素,身份的重新編碼是對地位和價值的置換。邊緣化的有情有義的妓女本質上已經不再是妓女,她們的身上帶有了很強的奇觀性,地位和價值的提升使之一躍從被救者變為拯救者,她們身上被付諸了無限的希望。在教會學生面前,她們褪去青樓妓女的外在身份后,消解了顯性與隱性的雙層對立和障礙,成為年長的依賴對象,被動強硬地承擔起拯救的重任,扶危濟困落在一群妓女身上也具有了必然性,也成了“敘事奇觀”硬性的審美需要。但這僅僅是妓女“情義”建構的第一步,成為教會學生的保護者和拯救者的“俠肝義膽”側重表現性情中的“義”,要真正呈現其真實立體“重情重義”的真性情,對于“情”的建構則更為重要。作為女性身份下的最為本真的情感欲望的表達,固然離不開與男性的依戀和糾葛,如影片中豆蔻對小傷兵王浦生既憐又愛的復雜情感表現,她為了給臨終的王浦生彈奏一曲琵琶,而舍生忘死地奔回妓院尋找琴弦,卻不幸遭遇日軍殘暴奸殺,成了典型的殉情者;美花臨赴宴的前夜拿出一副玉鐲,交給女學生,流著淚后悔當年因為沒信送玉鐲的男人、沒跟他一起走,這個并未出場的男人卻一直藏在她的內心,這份含蓄的愛也不言而喻;玉墨的情感相比較更加清晰,無論是她對于軍人身份的李教官的因為崇拜而衍伸出的情感依賴還是對于神父替代身份出現的洋人約翰濃烈直白的愛戀,都是鋪墊起她赴難豪情的情感基礎。因此,邊緣化的社會身份注定的“婊子無情”式薄情觀念得以糾正,也為后面十三位女子慷慨赴義提供了堅實保證,她們最終徹底化身為俠女形象。
妓女形象作為影片敘事書寫的核心角色,內在的身份轉變決定著角色塑造的成功與否。這種轉變需要形象塑造的前期身份定位必須是多層次的,俠女的內在身份才是真正表現的敘事重心,救贖的主題內涵附著于她們身上才符合邏輯。
二、軍人與儒士
《論語?衛靈公》曾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愛作為儒家道德的最高標準,為了維護正義事業而舍棄自己的生命也成了歷代儒士遵從的價值信仰。
影片一開篇就是中國士兵與日本兵的慘烈對抗,中國士兵已經死傷眾多,就在此時一群女學生逃了過來,為了讓女學生順利逃走,這群本可以突圍出城的中國士兵選擇了留下保護學生,導致眾戰士陣亡,只剩下李教官和年輕的重傷兵浦生僥幸存活。這種價值選擇固然帶有鮮明的儒家色彩,然而對實現自我價值的壯烈要求極端化——毀滅自我,成就他人,絲毫不帶有自我生存的欲求和對毀滅的恐懼感,反倒更為彰顯拯救過程中的成就感,這是對儒家社會倫理秩序的充分肯定。中國軍人身份的理想與抱負不像西方社會價值模式下的個人主義表達,而更集中表現其內在意識下的集體價值建構,使得故事要求對世俗目標的微觀刻畫變為對英雄信仰贊美的宏觀追求。
軍人形象的刻畫在儒家社會倫理秩序的大背景下展開,逐漸呈現出以尊倫理懂道義為特色的儒士身份,因此在這些軍人形象背后隱藏的“二律背反”也凸現出來:第一,這些軍人身份的英雄形象非常勇猛,可以殺出重圍出城求生,但同時卻也并不能足夠勇猛殺出重圍,在保護學生的過程中絕非日軍對手;第二,他們本應嚴守部隊紀律保存戰斗實力不被學生所打擾,但同時軍隊保家衛民的使命危急之下又使得部隊紀律必須舍棄。這樣的矛盾悖論,也決定了這樣身份的英雄群像必然走向悲劇結局。儒士身份下的末路英雄李教官,既理性又充滿智慧,他料定了結局卻并不沖動行事,而是暫時丟下軍人的尊嚴忍受妓女們對他的誤會將生命危在旦夕的王浦生送到了教堂的地窖,王浦生作為一個被卷入戰爭的無辜者,不僅是年少的弱者,在身份定位上更不算是軍人。除暴安良、抑強扶弱,作為中國古典英雄豪杰最突出的精神特質,無疑在這里也成為英雄塑造的主要情感基調。但更重要的是,在儒家觀念仁愛的影響下,其人性溫情細膩的一面頓時顯露出來,令我們看到一位有血有肉、舉智慧重情義的英雄義士。李教官安頓好王浦生之后,又來到教會學生房間的門外,默默掏出女孩子跑掉的一只鞋放在門口又悄然離去,這些細節刻畫對于英雄塑造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也不乏刻意之嫌。溫情的表達在英雄主義呈現中屬于張揚的氛圍營造,而儒士身份的要求必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強調情感的節制和謹慎,[2]當李教官遇到被他英雄氣質所吸引并產生依賴的妓女玉墨時,他們彼此的情感卻顯得十分隱忍含蓄,勇氣和毅力俱佳的英雄面對女性魅惑,克己禁欲的傳統倫理規范成了他們之間情感表達的無形障礙。
儒士身份超乎常情的極端英雄主義表達,是儒家英雄共同的歸宿。李教官最后在教堂對面紙店對大規模日軍的伏擊,帶有典型的英雄傳奇色彩,是個人英雄主義最極致的呈現。神勇的武藝展示、深謀的戰術安排、慘烈的戰爭場面,都為李教官轟轟烈烈的結局選擇做足了鋪墊,將帶有史詩風格的英雄豪氣渲染到頂峰,完成了軍人形象背后儒士身份“殺身成仁”的救贖使命。但遺憾的是,軍人角色救贖使命的完結并不是整體敘事救贖主題的實現,身份價值在整體敘事架構中得不到具有推動力的實質性延伸,導致軍人群像的塑造在極端個人英雄主義呈現中顯得更加單薄。
三、入殮師與上帝
洋人約翰是一名美國入殮師,更準確地說他是一個貪利縱欲的底層混混。他作為一個局外人,因為企圖得到英格曼神父的喪葬費用,來到教堂卻發現并不能得到想要的利益,但仍然執拗地陷入這場災難,卻又繼而完成自我內心救贖和對他人的救贖。可見,底層入殮師這樣的身份動機設定是存在悖論的,冒著槍林彈雨的威脅和無情的殺戮,一個底層小人物出現在災難現場,沒有足夠的誘惑動力驅使且在發現并無所獲之后依然不曾離開,直到等待質變來臨,這本身就是一種英雄書寫中“欲揚先抑”的敘事手段。同時,底層混混貪婪世故的外表卻依然掩飾不住約翰入殮師職業的特殊性,從事與生死相關的神圣性職業身份的隱喻暗示了他絕不是一位平凡英雄,但對于“上帝”式的英雄的塑造卻是從底層小人物到平凡英雄再到上帝身份的轉化開始,在約翰的雙重救贖中完成的。
影片中約翰以先入為主的入殮師身份出場,卻由于英格曼神父在轟炸中已經被炸飛無須入殮的黑色幽默導致這個顯性的職業身份完全失效,這層預設的職業外衣一旦褪去,使得約翰形象塑造少了束縛變得自由起來,然而同時也造成了人物行動理由缺乏說服力的缺憾。底層小人物被動卷入災難的敘事模式與陳凱歌的《趙氏孤兒》同車同轍,但對于約翰入殮師身份的暫時徹底割裂卻導致人物形象也出現前后落差,因此在約翰開始自我內心救贖的時候僅僅依靠他穿上了英格曼神父的彌撒服就得以實現也顯得非常生硬。約翰與玉墨的簡單調情,很顯然約翰出于肉體欲望的發泄遠不及玉墨想利用洋人來求得活命更為合理充分,反倒不如著重塑造約翰對玉墨內心深處生出的一種著迷,如此設置或許可以解決前面約翰形象留下來的敘事不足。并且在中國軍人李教官這個堅毅勇敢的儒式英雄面前,完全褪去職業身份的酒色約翰更加被動地被推到神圣的對立面,也使他實現“上帝”身份轉換的上升空間達到最大化。約翰自我內心救贖的歷程,實際上便是“上帝”身份的建構過程,他目睹了豆蔻和香蘭被日軍殘殺后的慘狀,并放棄了唯一可以逃離抽身的機會。李教官的犧牲和后路的斷絕雙重動力為約翰非一般救贖身份最終確立提供了充分的主客觀條件,他終于扛起對他人救贖的旗幟,成為尊嚴和正義的最終庇護者。約翰“上帝”身份的確立對核心敘事即如何實現妓女主動替學生去赴宴提供了保障:他擁有了強有力的話語權,一躍成為所有人的精神向導,并同時入殮師職業身份的回歸為其提供了重新塑造人外形與靈魂的萬能本領,一切救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玉墨與約翰的情感轉變以及在充滿隱喻意味的交合儀式,同樣也是印證“上帝”的存在和對其神圣的救贖洗禮。最后的一場戲中約翰親手將金陵十三釵送上赴死的卡車,再開動卡車救出了困在南京城的學生,這種絕妙的靈魂置換,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
另外,影片中的喬治是一個積極向上的角色,自始至終沒有退縮。他的存在對于約翰身份的成功設定起著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小喬治其實是真正的神父,他繼承了英格曼神父的衣缽,是典型的布道者,并成為“上帝”約翰的助手和信徒,最終殉道完成自我救贖和整體救贖。
注釋
[1]劉道生:《古代文學作品妓女形象淺析》,《欽州學院學報》,2010年4月。
[2]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28-31頁,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