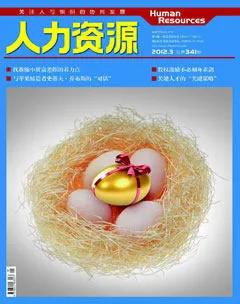民企成長勿“錯位”
雖然大部分企業家屬于社會精英階層,但單憑企業家的一己之力并不能保證企業的基業長青。用組織決策代替英雄決策,用制度化管理代替人情化管理才是規范企業管理的必由之路。
伴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成長起來的本土民營企業,在經歷了原始積累的陣痛后,正處于戰略轉型的重要階段:一方面,企業需要由粗放的生產經營向戰略導向、系統化運營轉型;另一方面,內部管理也急需由傳統的“人治”向規范化的“法治”轉型。
此時的民營企業,不僅需要制度的保駕護航,更需要以組織為中心,開展一系列的變革。這些工作必須是以包括企業家在內的高管團隊逐步職業化為基石,而恰恰在職業化進程中,高管團隊有時會迷失自己,容易犯下一連串小錯誤,進而使企業的前途命運出現了“錯位”。
錯將企業當兒子
“含辛茹苦”通常形容父母養育子女,而民營企業家經營企業,同樣可以用“含辛茹苦”來形容。白手起家的過程中,企業家本人以及家人對這份事業傾注了太多的感情,他們對企業的呵護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甚至押上了身家性命。
史玉柱總結巨人時代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自己經營巨人就像撫育孩子,總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顧孩子,不信任也不采納公司其他管理人員的意見與建議,形成了乾坤獨斷的局面。久而久之,重金聘請來的職業經理人淪為配角,成了普通的執行者。巨人大廈建設過程中,史玉柱得不到公司管理團隊的提醒與支持,或者說這些提醒與支持被他習慣性地忽略了,最后只好慘淡收場。
若將企業視為自己的孩子,必然造成企業“社會化”不足的缺陷,使其難以接受外界信息,不能及時進行調整或變革i同時,企業高管不得不扮演成“保姆”的角色,在企業家這個“父母”角色的陰影下只能默默成為企業管理的執行者,不能真正發揮職業經理人的作用,嚴重的還可能乘“父母”監管不力時虐待“孩子”。
篤信江湖義氣
我國不少民營企業家都是“草莽”出身,江湖義氣曾經幫助他們獲得過一些機會與資源,江湖義氣在創業初期或許能感召和凝聚住一批合作伙伴,但是當企業步入正軌后如果仍然保持江湖做派,必將給企業的規范管理造成巨大的傷害。
國內很多民營企業老板在用人過程中往往是人情、感情為先導。當跟隨老板多年的老哥們跟不上企業發展步伐而成為企業的拖累時,老板又不忍心拋棄他們,只能“創造”新崗位安置他們。后備人才得不到培養,公司總體管理效率日漸低下,長此以往企業正常的經營管理就難以為繼了。
國美的“陳黃之爭”在一定意義上也源自黃光裕的江湖義氣。在感情上黃待陳不是親兄弟勝似親兄弟,辦公室、配車都按自己的標準給陳配置。正因為視陳為自己人,黃把董事會交給陳時,并沒有考慮去調整這一決策機構的權限,同時也反映出他的江湖義氣使得他對董事會其他成員忠誠度的估計過于樂觀。最后黃家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付出的代價何其大也,黃陳二人之間的“兄弟感情”也蕩然無存。
這些都充分說明,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處處講人情,必然破壞規則;處處講義氣,必然破壞以業績為導向的績效管理;以忠奸辨別人才,勢必破壞人才引進與開發機制,最終給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帶來沉重的打擊。
錯將企業當試驗田
本土民營企業家大都好學、肯學,適逢過去幾年培訓業蓬勃發展,各種各樣的培訓課程讓企業家們眼花繚亂。一些企業家經過幾輪學習自認為掌握了管理的真諦,就開始“學以致用”,用剛從書本上學到的理念與工具操練自己的企業。管理試錯、應用新的理念本身并沒有錯,錯在不加辨別地借鑒和使用。
曾經鼎鼎大名的哈慈集團在交接班過程中,郭立文與趙力父子就有意無意地把企業當成了他們家族傳承的試驗田。由于年齡關系,創始人郭立文需要將企業傳承給選定的兒子趙力,但在接班過程中并沒有按企業交接班的規律設計一套相對系統的交接方案與流程,而是不斷地試錯:將管理權限下放給兒子一段時間,只要短期業績不如意,或者管理思路與自己相差較大就把管理權收回一段時間,過上一陣覺得自己把兒子調教好了,再把管理權限下放。如此反復,反映在企業管理方面就是組織、流程與人員的劇烈調整。在哈慈最為鼎盛的1999年與2000年兩年間,集團組織架構進行了至少四次大的變更,事業部制、產品線制、直線職能制、營銷獨立制等組織模式不一而足,作為一家擁有數十家分子公司、全國遍布28家營銷機構的集團企業,如此劇烈的調整,對于企業經營與管理的傷害可想而知,最終的結局就是哈慈業績大幅下滑,此后再無回天之力。哈慈的失敗雖然也有營銷政策、盲目多元化等其他誘因,但兩位老板將企業作為試驗田的管理行為不能不說是哈慈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996年就上市的標桿民營企業落得如此結局,怎能不讓人扼腕嘆息。
山東的一家企業,老板在短時間內引入了諸如現場5S、目標績效管理、執行力體系、決策管理、例會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工具與方法,幾乎涵蓋了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但是,員工對企業的認同度卻始終不高,很多管理人員先后離職。后來才知道,這位老板每次學習回來都要求按自己新學到的思路,作出某些方面的調整與改革,剛開始時下屬們還都很配合,但每年都要“折騰”好幾次著實讓人吃不消,最后只剩下董事長一個人的激情了。
錯將經驗當真理
還有一部分民營企業家在取得階段性成功以后,固步自封,認為一切外來的理念都不及他的經驗。這種企業家的口頭禪是“這種事經歷多了,一定會……”,或者“這樣做一定沒問題,當初已經嘗試過了”,云云。
曾經輝煌一時的秦池與太子奶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兩家都是通過做標王迅速崛起、將營銷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的企業。但他們在取得了階段性成功后,沒有系統梳理自己的戰略與內部經營管理體系,只是不斷地去復制過往的營銷模式。殊不知,在市場大環境、企業所處階段都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把過往經驗當成企業經營管理的真理,必然造成截然相反的經營結果,這兩家企業的結局,就是最好的注解。
在企業的經營實踐中,思維慣性與變革帶來的陣痛往往使很多企業無意識地犯下這樣的錯位。況且在市場機會導向的大環境下,也會縱容把經驗當成真理的錯位思維。一旦遭遇市場與人才的瓶頸,這樣的企業就難以適應了。
錯將自己當神人
企業家的成長環境與中國傳統的君臣文化,容易使企業家周圍充滿贊揚與羨慕,同時,企業家手中掌握著巨額財富的分配權,對于企業內部員工以及企業外部服務商而言,那就是生殺大權,這也加重了部分企業家擁有“上帝之手”的意識。
北京有一家民營企業,老板經過十年創業帶領企業成為了行業排名第一的公司,營業額逐年增長,很多業務開始主動上門。業內知名度的提升,使老板也變得不再愿意直接出面洽談業務,加之民營企業專權獨斷的通病,這位老板開始聽不進下屬的任何建議。后來,由于一次重大的經營決策失誤使公司大傷元氣,大部分員工另覓出路,公司也在行業中沉寂了下來。
當個人的地位發生重大變化,而又掌握了決定別人職業前途的所謂生殺大權時,部分企業家就開始自覺高高在上,聽不得逆耳之言,久而久之,下屬們也就只圖索取,而不再合作了。
錨將自己當“超人”
習慣一手掌控企業的企業家,自認為掌握了研發、技術、生產、市場、財務、人力資源等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要素,就能顯示出高人一籌的能力,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是決策權帶來的敬畏還是專業度帶來的點撥,部分企業家往往不能自知,反正自己比其他管理人員的認識都透徹,不僅為他人的無能而嘆息,更為自己的“超能”而驕傲。
巨人時代的史玉柱也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從開始的電腦技術研發,到后來的房產建設,全憑一己之力,似乎他無所不能。由于產權與中國傳統的強權文化,大部分民營企業家都曾經或者正在演繹著這樣的“神話故事”,只是程度上有一定的差異,比較嚴重的企業必然造成下屬事事請示,沒有指令不敢干活,最終企業家忙得像陀螺,而管理人員始終得不到培養。
錯將資產當家產
部分企業家及家人從一開始就把企業、家庭一體化,當企業需要進行資本運作與高管股權激勵時,企業家往往很難理解合伙人或高管的質疑,甚至開始懷疑股權激勵措施的科學性和高管們的職業品性。試想,如果企業家將企業的資金當成家產隨意支配,高管們又如何敢把自己的未來寄托在企業身上?
成都的一家企業,管理層里面既有家族成員又有職業經理人。老板發現,盡管每年都給管理人員加薪,這兩年還在籌備采用期權進行長期激勵,但高管們的工作狀態似乎沒有任何改善,后來得知,原來是在激勵政策上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家族成員的態度是,反正公司都是我們家的,怎么發只是形式問題,我們有需要只要打個招呼,就能從公司提錢:職業經理人的態度是,都是干同樣的活,甚至干更多的活,跟家族成員相比卻總是相差一大截,期權問題就更值得考慮了。
這就是企業家將資金當成家產的后果之一,幾年的激勵措施不僅沒有發揮任何積極的效果,反而引發管理人員更大的不滿。
錯將人才當“寵物”
企業規模做大了,老板們深感自己或原有管理團隊的不足,部分企業開始大量引進人才。博士、海歸、有外資企業經驗者都成為了企業家的座上賓,尤其是那些草莽出身的企業家,對這樣的人才更是格外禮遇。
很多企業家(甚至是很多地方政府)都認為,引進了高端人才,企業(或當地)的管理水平必然會發生質的提升,但殘酷的現實往往給了他們相反的答案。于是這部分企業家出現兩個分化,一部分開始認為人才不行,雙方分手;另一部分人繼續將人才供養起來,以作為自己企業提升的標志。
面對一系列民營企業失敗的案例,社會上也在深刻反思著我國民營企業家的角色。出現以上“錯位”的現象與行為,大都是企業家因個人能力局限所帶來的成長困惑。民營企業家需要從投機式地經營企業,成長為用戰略性思維引導企業。適當跳出企業的局限,用行業的視角、甚至更宏觀的視角思考企業的問題,或許就會找到更好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