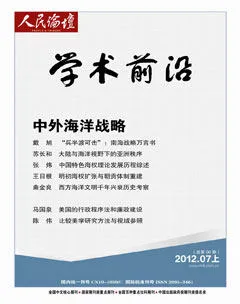美國的行政程序法和廉政建設(shè)
摘要 美國國會于1946年通過的行政程序法,目的在于防止美國行政系統(tǒng)一支獨大,演變成脫離三權(quán)分立為基本構(gòu)架的政治體系,成為不受美國憲法制約的第四權(quán)力部門。其強調(diào)的政府運作透明、公眾參與以及司法復(fù)審,在相當(dāng)程度上保障了美國百姓的基本權(quán)利,推動了美國廉政建設(shè)的步伐。然而,權(quán)力的腐蝕,對利益的追逐,驅(qū)使政府官僚利用該法的某些條文,千方百計藏匿情資。實踐證明,落實廉政建設(shè),要有行政程序法,更要有信息自由和陽光政治。
關(guān)鍵詞 行政程序法 政府運作透明 公眾參與 司法復(fù)審 廉政建設(shè)
行政程序法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內(nèi)容
自1933年起,作為新政立法計劃的一部分,美國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民主黨占多數(shù)的美國國會聯(lián)手,在聯(lián)邦政府中設(shè)立了一系列新的機構(gòu)。到了30年代后期,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的問責(zé)性開始日漸為人們所關(guān)注。具體表現(xiàn)為:1937年,布朗洛委員會提出了官僚程序需要改革的建議;全美律師協(xié)會有關(guān)行政法的報告;1941年,聯(lián)邦政府司法部長的行政程序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二戰(zhàn)”結(jié)束不久,國會對聯(lián)邦政府行政部門日益擴張的權(quán)力開始感到憂心忡忡。以規(guī)范聯(lián)邦政府行政程序為主旨的行政程序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46年6月問世的。
行政程序法要求:所有政府部門①都必須將其部門的運作公諸于世;必須就建議的規(guī)章提前發(fā)出通知;必須允許有關(guān)人員由律師陪同進行作證,并盤問對方證人;同一官員不得身兼兩職:既當(dāng)公訴人又作裁判官;有關(guān)人員可以在法庭就政府部門的決定提出上訴;法庭有權(quán)撤銷政府部門任何主觀隨意的或者沒有實質(zhì)性證據(jù)支持的規(guī)定。②
由于行政程序法的約束,政府部門不能未經(jīng)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就聘用或者解雇員工,投入基建項目,或者出售物品、服務(wù)等等。不但政府部門的目的,就連這個部門的運作程序也往往要由美國國會事先制定。例如,按照美國法律,美國國務(wù)院未經(jīng)許可不得隨意關(guān)閉屬下的任何駐外機構(gòu);又如,由美國國會授權(quán),主管援外項目的國際開發(fā)署(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必須致力實現(xiàn)33個目標(biāo)和75項優(yōu)先項目,每年還必須向國會呈交288份報告。③
正是由于行政程序法的要求,政府部門提議的規(guī)章必須刊載于每周五天每天出版的《聯(lián)邦紀事》(Federal Register)上。這個制定規(guī)章的程序被稱為“通告和評論規(guī)章制定程序”(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整個程序包括三個階段,即頒發(fā)提議的規(guī)章、公眾評議,以及最終審定規(guī)章,并將之再在《聯(lián)邦紀事》上刊出,以公諸于眾。④行政程序法大大地約束和限制了政府官僚的行政裁量權(quán)。首先,各部門管轄范圍內(nèi)的大小事務(wù),必須要管。其次,一定要在聽證前事先公告,并允許有關(guān)各方出席聽證。再者,經(jīng)辦官員必須客觀公正,要做的決定不涉及任何個人利益。此外,所作的決定要以實質(zhì)的證據(jù)為基礎(chǔ)。最后,受決定影響的有關(guān)方必須給予咨詢和上訴的機會。這就是在程序意義上的法定程序(due process)。⑤
也正是由于行政程序法的規(guī)定,美國的法庭有權(quán)審閱行政部門的所作所為,以決定這些政府作為是否專斷不公、反復(fù)無常、有濫用行政裁量權(quán)(abuse of discretion)之嫌,或者與法律分道揚鑣。美國的行政程序法還授權(quán)法庭,強制政府部門就其非法擱置,或無故推遲的決定采取行動。正是這種司法自由度(judicial latitude)使消費者、環(huán)境保護群體,以及強調(diào)安全第一的公民等能夠通過法庭對拖延推托、遲疑不決的政府部門施加壓力,逼迫它們盡責(zé)盡力。⑥
顯而易見,行政程序法的目的在于防止美國行政系統(tǒng)一支獨大,大權(quán)獨攬,甚至演變成脫離了三權(quán)分立為基本構(gòu)架的政治體系,不受美國憲法制約的第四權(quán)力部門。行政程序法強調(diào)的幾個方面,即政府運作透明、公眾參與,以及司法復(fù)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美國百姓的基本權(quán)利,推動了美國廉政建設(shè)的步伐。正因為如此,美國參議員麥卡蘭(Pat McCarran)將該法譽為“其個人事務(wù)被聯(lián)邦政府部門通過這樣那樣的途徑控管的千百萬美國百姓的人權(quán)法案”。 ("a bill of rights for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whose affairs are controlled or regul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by agen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行政程序法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然而,古往今來,政府官員濫用權(quán)力、假公濟私的不軌行為始終屢見不鮮,層出不窮。1788年,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 )就曾說過:“如果由天使來治理凡人的話,政府就無需受內(nèi)在的或者外界的制約。在規(guī)劃一個由凡人來管理凡人的政府時,老大難的問題在于:你必須首先設(shè)法讓政府能夠控制被統(tǒng)治者,然后又強制政府去控制它自己。”⑦ 1887年,英國貴族艾克頓(Lord Acton)也曾寫道:“權(quán)力導(dǎo)致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導(dǎo)致絕對的腐敗。”這些名言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沒有過時。自己約束自己難,有權(quán)有勢時,自己約束自己更難。怎樣才能迫使大權(quán)在握的政府官僚不無視民意,專橫武斷,剛愎用事?如何才能設(shè)法駕馭住儼然以政府的第四權(quán)力部門自居的官僚機構(gòu)?正如美國學(xué)者肯尼迪(Sheila Kennedy)和舒爾茲(David Shultz)所指出的,行政程序法只是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初始努力而已。⑧
的確,盡管行政程序法已經(jīng)問世,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和大大小小的官僚機構(gòu)依然故我,互相勾結(jié),繼續(xù)左右政府政策的實施和落實。美國朝野上下對此的憂慮有增無減。⑨本來,行政程序法是因應(yīng)羅斯福總統(tǒng)的新政和“二戰(zhàn)”的發(fā)展而問世的。大量政府部門成立,要頒布一系列的規(guī)章制度。為了使這個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gòu)系統(tǒng)化,行政程序法為行政作為制定了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其目的有二:一是有助于公眾參與規(guī)章制度的制定過程;二是要求政府各部門向公眾通報有關(guān)這些部門的組織、程序、制定出的規(guī)章制度的最新動態(tài)。然而,隨著冷戰(zhàn)的硝煙再起,政府官僚趁機在文字上大動手腳,千方百計藏匿情資,把黎民百姓蒙在鼓里。結(jié)果是,原本對政府部門必須將其組織、程序和規(guī)章及時通報公眾的要求,卻讓政府官僚借各種借口和例外,堂而皇之地變成了將政府信息秘而不宣,隱而不告的權(quán)威令箭。⑩
按照程序辦事,并不等于廉政建設(shè)就可以水到渠成。按程序辦,到了官僚的手里,也可能成為他們有機可乘,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按理說,遵循應(yīng)有的行政程序,保證行政公平合理,是有助于廉政建設(shè)的一個重要方面。美國的著名學(xué)者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曾經(jīng)說過,要嚴格落實法定程序(due process)和公平合理的原則,為的是給政府行為對象一個公平的機會,使其可以將對官方?jīng)Q定的看法記錄在案,使其自身的利益不至被無端忽視,甚至為當(dāng)權(quán)者任意蹂躪。然而,按照法定程序辦事往往耗時費日,涉及許多官僚作風(fēng)的繁文縟節(jié)。這個過程不但浪費公共資源,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官僚大權(quán)在手,完全可以或呼風(fēng)喚雨,施加影響,或小試牛刀,動動手腳,以致結(jié)果也就不一定公平合理。正因為如此,考夫曼直截了當(dāng)?shù)刂赋觯叭绻麤]有行政程序法的話,政府部門也許就不會任意踐踏百姓的權(quán)利。官僚部門既定的章程,司法的先例,政治的壓力,以及公認的公正原則本可以讓政府官僚有所約束。然而行政程序法卻毫無疑問地使那些官僚們有機可乘,大大地把官僚程序形式化,復(fù)雜化了。”
由此可見,保障公眾對行政程序的知情權(quán)并不容易,是廉政建設(shè)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盡管行政程序法明文要求,各政府部門在施政的過程中要注意聽取公民的建議,在施政的每一個階段都規(guī)劃出一定的時間,以讓社會對政府的措施做出回應(yīng), 然而,要具體落實,真正達到行政廉潔的目的,一個更為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加大行政透明的力度。正如美國學(xué)者萊特(Paul C. Light)所講,美國國會和總統(tǒng)為了使政府作業(yè)更加透明,憑借的是三大法寶,即行政程序法、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及陽光政府法(the 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與政治詞典在“行政程序法”項下特意注明:“對行政程序法的主要修正包括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74年的隱私法,以及1976年的陽光法。”
信息自由法和陽光政府法
如果說行政程序法是從國家機器內(nèi)部對政府官員進行制約的話,那么信息自由法和陽光政府法就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于從國家機器之外對政府官員實施監(jiān)督的大環(huán)境,使新聞界及非營利組織等美國社會的一些群體可以監(jiān)視、督促政府官員自己管好自己。美國新聞界的影響力之所以如此之大,首先應(yīng)當(dāng)歸功于對民意的尊重。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第三任總統(tǒng)托馬斯·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說過:“民意是政府的基石,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首要目標(biāo)。”這種對民意的尊重,對新聞界的支持并不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而是通過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裁決予以落實,從而成為新聞界監(jiān)督政府的堅強后盾。1964年,最高法院裁決:只有在一篇關(guān)于政府官員的報道是不真實的并出自“實際上的惡意”或“不顧一切的無視真相”時才可以被認為是誹謗。這意味著:要證明一份報刊故意登載了虛假的損害性的消息是幾乎不可能的;即XJLIZKSQt7uRPcPGZ8h3eyLyrCmhbiB5H2UB2CscNIs=使是那些長袖善舞的政客們,要想打贏針對他們的所謂誹謗官司,也是難乎其難。
美國社會之所以能夠在官僚體制外對政府官員進行監(jiān)督,關(guān)鍵在于他們手中握有信息自由法和陽光政府法兩大利器。美國的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于1966年由林頓·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tǒng)簽字生效。在簽字儀式上,他講了下面一段話:“我一直相信,信息自由是如此的至關(guān)重要,所以唯有國家的安全,而不是政府官員或者民間公民的愿望,才可以決定什么時候信息應(yīng)該受到限制。”根據(jù)該法,任何人,包括美國公民、外國人、各種組織、協(xié)會和大學(xué)都可以提出信息自由法申請。聯(lián)邦政府行政系統(tǒng)各部門擁有的記錄都可以供公眾閱覽。在該法生效之前,老百姓想要查閱政府的記錄,就必須要設(shè)法證明自己享有這樣的權(quán)利。該法生效以后,政府不能要求想要獲取信息的個人或團體去說明為什么需要這樣做。“知的需要”已經(jīng)被“知的權(quán)利”所取代。現(xiàn)在要做解釋的不再是百姓,而是政府,政府必須解釋為什么有保密的需要。
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信息自由法的修正案,加入了不少新的內(nèi)容。例如,對政府部門的決定進行司法評審;收縮某些豁免的范圍;禁止政府部門超額收費;政府部門必須于十天內(nèi)對提出信息自由法的申請做出答復(fù),于二十天內(nèi)對行政上訴作出答復(fù),特殊情況下可以寬限十天;政府部門如果在信息自由法爭辯中敗訴則必須負擔(dān)法庭和律師費用;允許法庭指令美國聯(lián)邦公務(wù)員委員會對任何故意扣押應(yīng)予公開的信息的行政官實施紀律處分,等等。1974年的信息自由法修正案進一步強制政府部門要落實信息自由法的各項規(guī)定。此后,公眾運用信息自由法提出獲取信息的申請急劇上升。
1986年的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條款。非商業(yè)機構(gòu)、教育系統(tǒng)和新聞界的申請人可以免交律師費(如果要打官司的話)和申請費。國會認為,這些并非從事商業(yè)活動的申請人,如記者、學(xué)者、公共利益集團等,大都經(jīng)濟并不寬裕,他們通過信息自由法尋求公開某些信息,多半是為了推動公共利益,其志可嘉,其行可賞。
1996年,電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經(jīng)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tǒng)簽字,正式生效。新的修正案要求聯(lián)邦政府各部門均需設(shè)立對公眾開放的、具有電子搜索和索引功能的電子閱覽室,為公眾根據(jù)信息自由法申請閱覽政府記錄提供更多便利。顯而易見,信息自由是公眾監(jiān)督政府,防腐倡廉的一大利器。正如美國的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說,“一個信息不普及的,或者無法去普及信息的,所謂的人民的政府,只能是一個鬧劇的開場或者是一出悲劇的序幕,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一個國家的人民要想成為自己的主人,就必須用知識賦予他們的力量來武裝自己。”
必須指出的是,普及信息的道路并不是一條平坦的康莊大道。用知識所賦予的力量來武裝自己,監(jiān)督政府,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時有反復(fù)的過程。正如2004年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委員會少數(shù)成員報告(a 2004 minority staff report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所指出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上臺以后,信息自由法的落實范圍變窄了,政府部門或借口程序所需,或施以拖延戰(zhàn)術(shù),將公眾依據(jù)該法提出的公開信息的要求拒之門外。
公眾監(jiān)督政府、防腐倡廉的另一利器就是陽光政府法(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美國國會于1976年通過該法,要求會議對公眾開放,也就是說,除非有某些特定的事務(wù),如軍事秘密、貿(mào)易秘密,以及私人的人事記錄等需要討論,除了十項豁免外,政府部門的每次會議的每個部分都必須開放,讓公眾出席旁聽。為此,政府部門召開會議之前必須先發(fā)出通知。其次,政府部門必須要遵守該法制定的一系列程序上的要求,再決定會議能不能符合十項豁免中任一項的條件。
然而,往往法律條文是一回事,官僚落實又是另一回事。2001年1月,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George W. Bush)簽發(fā)總統(tǒng)備忘錄,成立國家能源政策開發(fā)小組,由副總統(tǒng)錢尼(Dick Cheney)牽頭出任組長。小組成員包括聯(lián)邦政府的財政部長、內(nèi)務(wù)部長、商務(wù)部長等。外界傳言,一些能源和石油大公司的高層主管也躋身其內(nèi),大有官商勾結(jié)、利益輸送之嫌。于是,應(yīng)國會議員要求,總會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為美國國會服務(wù)的、獨立的、非黨派的審計機構(gòu),一再要求錢尼提交出席該小組會議的人員名單及其職務(wù)。錢尼辦公室卻以各種托詞對此置之不理。這場官司時斷時續(xù)地打了好幾年,結(jié)果要求會議信息公開的嘗試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證明,美國在落實信息自由法和陽光政府法的過程中不斷地遇到新的挑戰(zhàn)。面對政府官僚的抗拒,唯有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最終實現(xiàn)監(jiān)督政府、遏制腐敗的目的。當(dāng)然,這種努力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正如美國學(xué)者佩恩特(Richard W. Painter)在探索美國行政道德改革的途徑時所說,“選民不會從政府那里得到他們要求的每一件東西,但是,他們通常會得到他們最經(jīng)常,最堅決要求的東西。”
廉政建設(shè)對行政程序的挑戰(zhàn)
從1946年行政程序法問世到1964年通過國會的信息自由法,這段路走了18年。又過了12年之后,國會才通過了陽光政府法。即便已經(jīng)立法,也還面臨著如何與時俱進的挑戰(zhàn)。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從最初版本的信息自由法,經(jīng)過歷年的一再修正,直到1996年電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經(jīng)總統(tǒng)簽字生效,前后更費時長達32年。正是由于對行政透明的強調(diào),歷經(jīng)數(shù)十年的實踐,以及法律條文上的不斷完善,“經(jīng)自由信息法和陽光政府法修正的行政程序法”已經(jīng)成了對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行政程序法的完整的、正式的稱呼。
柯特爾教授(Donald F. Kettl)長期研究美國政府,曾經(jīng)在常青藤名校賓州大學(xué)擔(dān)任羅伯特福克斯領(lǐng)導(dǎo)學(xué)教授(Robert A. Fox Leadership Professor),現(xiàn)為馬里蘭州大學(xué)公共政策學(xué)院院長,并兼任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 2008年,柯特爾教授被美國政治學(xué)學(xué)會授予學(xué)會的約翰高斯獎(the John Gaus Award),以褒獎其對政治學(xué)和公共行政學(xué)所作的畢生貢獻。在回顧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所推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時,他認為,奧巴馬行政當(dāng)局所采取的是“以透明作業(yè)為基礎(chǔ)的策略”(a strategy based on transparent performance),是試圖“通過透明來重新界定問責(zé)”(redefine accountability through transparency)。在他看來,“奧巴馬政府相信,注重官員業(yè)績,通過行政透明落實官員的問責(zé),將會使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行政管理面貌一新。”奧巴馬政府能否如愿以償,人們正拭目以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行政透明,是廉政建設(shè)的不二法門。
注釋
根據(jù)行政程序法5 U.S.C. 551(1),美國國會、聯(lián)邦法庭、美國屬地政府均屬例外。此外,按照1992年法院的一項裁決,美國總統(tǒng)也不受行政程序法的約束。見Franklin v.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