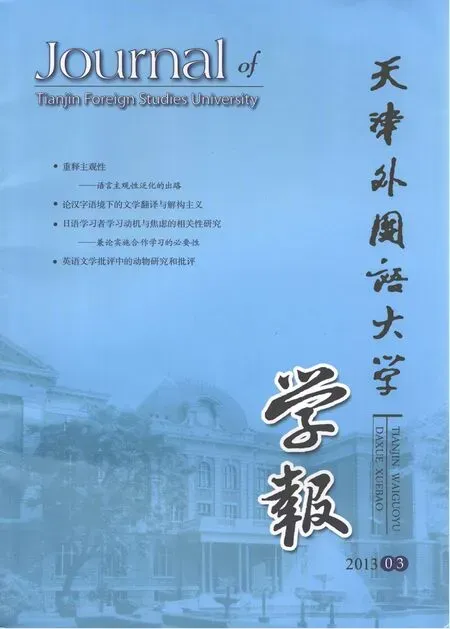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戴乃迭譯介活動研究——對20世紀8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的譯介
王惠萍
(上海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34)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創作的繁榮期,其中由從文革中成熟起來的一批新時期女性作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尤為引人注目。作為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的專家和主要翻譯人員,戴乃迭對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大量譯介打開了一扇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而她的雙重文化身份和女性主義思想使其譯介活動呈現出獨特的風格。本文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對戴乃迭的譯介活動展開研究,以期揭示她為提升女性地位,使中國女性的聲音被世界所聽見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二、女性主義與翻譯
1990年,巴斯內特與勒菲弗爾(Bassnett&Lefevere,1990:4)明確提出了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問題,指出翻譯的基本單位需要擴展到以文化為單位,因為任何文字、文本的產生與傳播都深深根植于文化語境之中。翻譯研究從以文本為中心轉變為對社會、歷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強調。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便已悄然發展起來。在文化學派形形色色的分支中,最具特色的可以說是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主義翻譯學派。
20世紀70 至80年代,女性主義發展經歷了第三次浪潮。西方女性主義者對語言中大量存在的、或隱或顯的歧視女性的成分予以了嚴厲的抨擊。加拿大女性主義學者西蒙(Simon,1996:8)曾說:“20世紀70年 代,一個耳熟能詳的呼聲是:女性必須獲得語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須先從語言著手。”與此同時,大量西方現代理論,如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學等的成熟使女性主義者得以用一種嶄新的視角去看待翻譯,從而形成了以為女性服務為宗旨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女性主義翻譯觀認為,翻譯首先是一種政治活動。后現代哲學家福柯的權力話語學說為女性主義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福柯拒絕一個先驗的、固定不變的主體,代之以一個建構的、話語構成的主體。這樣女性能夠通過適應和改造話語來達到建構主體的目的(黃華,2005:18)。女性主義者們意識到女性之所以淪為第二性,是因為女性沒能掌握話語權。現行的主流話語是男性的話語,要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根本在于要建立一套屬于女性并為女性言說的話語,重新界定兩性的地位。加拿大女性主義學者羅特賓尼爾–哈伍德(S.de Lotbinière-Harwood)宣稱:“我認為翻譯是一種政治活動。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通過在語言方面的工作,我把我的政治觀點經由翻譯而投入實踐。”(劉亞儒,2005:12)
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另一核心理念是將翻譯視為一種改寫。西蒙在《翻譯中的性別:文化特征和轉換的政治性》中提出,翻譯不是簡單的轉換,而是各種文本和社會性論文構成的臨時性網絡中意義創造和傳播過程的延續。這種觀點源自解構主義學派代表德里達的延異理論。德里達指出:“所指概念永遠不是自為的存在,每一個概念都是序列或系統中的一環,還指向其他概念,這通過系統的相互區別來實現。”(Davis,2004:13)只有能夠相互區別,語言才有意義。這種區別有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符號不能直接指向某種存在。因此,翻譯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體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條件下的一種改寫,原作者/譯者、原作/譯作二元對立的邏各斯主義被摒棄了,翻譯和其他形式的寫作一樣都是“意義的流動創造”。翻譯成了女性主義作者和譯者共同參與的女性主義寫作項目(Simon,1996:1-2)。
費拉德總結了女性主義翻譯實踐中的三種最主要的翻譯策略:增補(supplementing)、添加前言和腳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及劫 持(hijacking)(von Flotow,1991:69-70)。增補是指補償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不同之處,特別是補償原文在表述性別意義上的方式。通過添加前言和腳注向讀者表明自己的個人背景、政治議程和翻譯策略等。如羅特賓尼爾–哈伍德在譯者前言中坦陳:“我的翻譯是意圖使語言為女性說話的政治活動。我對于翻譯的屬名意味著:這個翻譯作品已經使用了所有可能的女性主義策略,以使女性在語言中顯形。”(費拉德,2007:29)劫持則是指女性主義譯者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圖對原文中不符合女權主義觀點的部分進行操縱,使其帶有女權主義傾向。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于中國翻譯研究的影響相對較晚,直到2002年我國才出現與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相關的論文。“由于國情不同、語言形態不同、宗教因素不同等原因,我國迄今尚沒有真正的女性主義譯者”,“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女性主義對我國譯者沒有影響”(蔣驍華,2004:14)。例如,朱虹坦言她的翻譯選材標準一是作者是女性,二是作品寫女性(穆雷,2003:41-44)。女性主義思想對于我國的翻譯實踐已經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三、戴乃迭的雙重文化身份
戴乃迭(Gladys Yang)是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的妻子。她1919年生于北京,其父為英國來華傳教士,1926年隨母親返回英國。1937年,戴乃迭入牛津大學學習,結識了楊憲益,兩人相愛并終結連理。1940年,戴乃迭隨丈夫回到中國,直至1999年病逝,在中國整整生活了60年,期間很少返回英國。戴乃迭與丈夫共同經歷了中國社會的沉浮變遷。作為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部的專家及英文版《中國文學》的主要翻譯人員,戴乃迭與丈夫合作翻譯了大量中國古典及現代經典文學作品。她還獨立譯介了許多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尤其對于20世紀80年代女性文學的譯介,打開了一扇讓西方了解中國的窗口。
張裕禾和錢林森(2002:72)將文化身份定義為一個個人、一個集體、一個民族在與他人、他群體、他民族比較之下所認識到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的核心是價值觀念或價值體系。哈馬斯(Hamers,1989:11)則認為,復雜文化結構整合進入個體人格并與之相結合就構成個體的文化身份。戴乃迭始終保留著英國國籍,在一次采訪中她談道:“我是英國人,也許有些中國人覺得我沒有放棄我的英國國籍是不夠愛中國,我不那么想……我愛中國,不是說我不愛英國。”(楊憲益、文明國,2010:25-26)戴乃迭并未簡單地將自己定位于某一種文化,她曾說:“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楊憲益,2003:2),在她的身上凝聚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論家巴巴(Bhabha,1997:30-31)指出,今日文化的定位來自不同文明接觸的邊緣處和疆界處,“最真的眼睛現在也許屬于移民的雙重視界”。我國學界從西方理論中引入流散(diaspora)這一概念,以描述游離于宗主國和居住國之間的生存狀態及其文化心理。目前多數學者關注的是由第三世界國家流動和移居至第一世界國家的流散者,戴乃迭則屬于相反的狀況。這種反方向的流散者往往是出于對居住國文化的熱愛而更積極地利用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去促進兩種不同文化的溝通和融合。在中國多年的生活及與源語文化的疏離使戴乃迭的譯介活動實際上更多地受到居住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得以立足于中國,向西方推介中國的文學和文化。
四、女性主義與戴乃迭的譯介活動
20世紀50 至7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經歷了一個絕對政治的時代,以主流意識形態為綱的無性化文學和宏大的國家主題成為統治性敘事話語。表面上中國婦女解放的程度比其他國家更好,女性歡喜地接受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等觀點。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男性中心’文化因此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會環境中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在家庭生活中、在男女關系中、在我們心中依舊根深蒂固”(李小江,1999:205)。
雖然五四時期女權主義思想曾傳入我國,但其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社會政治領域,并未波及文學和文化的深度。于東曄(2006:28)指出,女性主義真正走入中國是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進行,男女實質上的不平等開始顯露出來,讓女性從男女都一樣的迷霧中清醒過來。張潔(1983:123)在小說《方舟》中發出了女性的吶喊:“婦女解放不僅僅意味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解放,還應該包括婦女本人以及社會對她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正確認識。”而20世紀80年代初的女性作家更多的是憑借女性經驗觸及女性主義問題,對女性主義仍然是懵懂無知的。她們特別關注女性的精神渴求,側重反映女性的生活,希望引起社會、時代的關注和男性的理解與同情。此時的女作家們還習慣于將女性個人的悲劇隸屬于社會政治的悲劇,而沒有更深入地探討女性處境的深層原因(于東曄,2003:53)。
一些后殖民女性主義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婦女與第三世界婦女在各自經歷、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單靠以社會性別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不觸及更深層的因素,是無法描述第三世界婦女所受的壓迫的。中國女性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女性自身的主體意識長期遭受壓抑,“漫長的男權文化已經使女性的‘出嫁意識’,即歸屬意識,內化為女性的一種無意識”(同上:50)。戴乃迭在中國長期的生活和坎坷的經歷令她能深切地了解中國女性的現實狀況和問題,從而通過一種本土化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向海外昭示了被西方權力話語所隱蔽的中國文化的真實面貌。
1 翻譯的選材
20世紀80年代之前,戴乃迭的譯介活動受到居住國文化范式的影響,并未呈現出對于女性作家和主題的偏重。獲益于20世紀80年代起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活躍,且由于楊憲益開始主持《中國文學》的編務工作,使戴乃迭能夠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作為一名女性譯者,戴乃迭首先將目光投向了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在翻譯的選材上偏重于新時期女性作家創作的且體現了一定女性主體意識的作品。戴乃迭的好友、女性主義學者達文曾提及:“80年代,她(戴乃迭)對婦女運動產生了興趣,大量翻譯了從文革中成熟起來的一批中國當代女作家的作品”(楊憲益,2003:152),如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中短篇小說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新鳳霞的自傳《新鳳霞回憶錄》、諶容的《減去十歲》等中短篇小說,與他人合譯的王安憶的小說集《流逝》以及張辛欣與桑曄合著的報告文學《北京人》等。除親自參與翻譯外,戴乃迭的另一重要貢獻是通過在《中國文學》上撰寫介紹性文章,參與編輯“熊貓叢書”的女作家作品集并親自為之作序,有時甚至動用個人的海外渠道來推介作品等,積極地向海外介紹戴厚英、張抗抗、宗璞、黃宗英、遇羅錦等眾多女作家。通過對這些女性作者的譯介,戴乃迭及時使西方了解到中國當代女性的生存狀態。
2 翻譯的目的
戴乃迭對于作品的譯介往往伴隨著譯作中詳實的譯者序,或是散見于《中國文學》各期對于相關作家和作品的介紹性文章,全方位地介紹了作家和作品的時代歷史背景,向西方描繪了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戴乃迭尤其希望世界能關注和理解中國女性的處境和問題,如在《當代女作家七人集》(Seven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的序言中說道:“根據憲法規定,在中國男女權利平等,但在實際生活中這并未完全實現,雖然目前女性地位已大幅提高了。……許多女性試圖在提高專業技能的同時當好賢妻良母,結果過早衰老。張潔曾不止一次對我說:‘當女人不容易!’但是在中國沒有女性解放運動,一方面是因為女性地位比起過去改善了許多,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們是從社會的大環境去看待問題的:為實現現代化而工作,以減輕自己的負擔。這就是為什么在大多數作品中,她們的困難被邊緣化了,而不是作為中心的主題。”(Yang,1982:6-7)從序言中不難發現戴乃迭本人鮮明的女性主義思想以及對于提高中國女性地位的企盼。但她并未將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強加給復雜的中國社會,而是對于中國女性的現實狀況給予了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并試圖通過自己的譯介活動努力喚醒中國女性沉睡的主體意識。
3 翻譯的策略
于東曄(2003:50)認為,張潔等女性作家的創作屬于女性主義文學的少女時期,作品中呈現的女性主體意識尚朦朧。以張潔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沉重的翅膀》為例,原作是圍繞改革開放中工業體制改革引發的種種問題展開的,人物的情感描寫被掩藏在這個大主題下。戴乃迭通過自己獨特的翻譯處理,使譯文突出了人物的情感脈絡,強化了女性主義色彩,從而呈現出與原作不同的風貌。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義譯者,戴乃迭避免采用激進的翻譯策略。她通過撰寫譯者序,使讀者將注意力轉向作品所反映的婚姻制度不合理的問題上:“作品強調了——這次主要從男性角度——當前婚姻體制的不足。在所描述的六對已婚夫婦中,只有一對是幸福的。在中國男性掌握權力,是道德觀的制定者。但在愛情方面,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也成了自己所創造或容忍的倫理觀的受害者。”(Zhang,1987:x-xi)她還邀請了達文為其英譯本作跋,對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作了詳細的介紹,引發讀者對中國女性問題的思考:“在《沉重的翅膀》中,女性人物給人的震動和失望多于鼓舞,其原因值得我們思索。”(ibid.:175)
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戴乃迭運用了相對溫和卻不失靈活的處理方式。她凸顯了女性人物角色,對主要女性人物的名字進行意譯,而其他人物的名字則采用音譯,如將“葉知秋”譯為Autumn,“夏竹筠”譯為Bamboo,“劉玉英”譯為Jade 等。這些英語詞匯和人物的性格有一定的聯系,從而更生動地塑造了女性人物的形象。但對于“萬群”的翻譯,戴乃迭卻選用了與中文含義無關的詞Joy。萬群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年輕守寡,愛上有婦之夫,最終不幸死于車禍。joy 這個詞與人物的悲劇命運形成了強烈反差,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戴乃迭的譯文刻畫了女性細膩的情感特征,凸顯了女性的地位。下面試舉例比較戴乃迭與另一位男性譯者、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的譯文。
(1)在比她似乎還老于世故、不易動情的莫征的面前,她覺得自己有時候像個幼稚的、容易感情沖動的小女孩。(張潔,1981:7)
戴譯:The worldly-wise,phlegmatic Mo Zheng made her feel like an ingenuous little girl,too easily upset.(Zhang,1987:4)
葛譯:She feels like a high-strung child whenever she’s around him;he’s so much more worldly than she,and less easily moved.(Zhang,1989:8)
上句是對女記者葉知秋的性格描寫,她是一個外表剛強冷漠,內心卻柔弱敏感的女人。ingenuous(真誠的)較high-strung(容易生氣的)更好地體現了人物感情的真摯。而little girl 較中性的child 更凸顯了葉知秋的女性身份,從而細致入微地傳遞了女性人物內心深處的溫柔情感。
(2)“……婦女解放還應該靠自己的自強。而不是靠——”他停下來,看著夏竹筠的頭發、服飾。“她應該不斷進取,讓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業心。而不是把她當作一朵花來觀賞……”(張潔,1981:260)
戴譯:“...Women have got to emancipate themselves.”He stopped,eyeing her hair and clothes.“You should get ahead,win your husband’s respect.Not just doll yourselves up...”(Zhang,1987:111-112)
葛譯:“...It means relying on your own strength,not on...”He pauses and looks at Xia Zhuyun’s hairdo and her attire.“A woman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herself so her husband will respect her character,her spirit,her dedication,and not treat her like some lovely flower...”(Zhang,1989:191-192)
兩位譯者的敘述角度有差別,戴乃迭使用了第二人稱,而葛浩文用了第三人稱。戴乃迭站在女性的立場上,通過使用doll up(打扮得花枝招展)這一形象的動詞詞組,呼吁廣大女性如果要得到男性的尊重,就不能只注重自己的外表。葛浩文的譯文則基本依照原文進行了直譯。
更重要的是,在文本的全局處理上,戴乃迭刪除了原作中過多有關政治和經濟的言論。在譯者序中戴乃迭說道:“有些地方關于政治和經濟政策的討論過于冗長……因此我經過作者同意刪除了這些內容。”(Zhang,1987:xii)正是因為經過這樣的處理,原作隱含的女性主題得到了彰顯,文本的女性主義色彩明顯增強。
戴乃迭所譯介的多部女性文學作品在海外發行后,“在歐美引起極大的反響,刊物(《中國文學》)的貿易發行量顯著增長,文革中丟失的教授、學者和白領讀者又重新回來了”(趙學齡,1999:505-506)。戴乃迭的譯介活動揭開了中國神秘的面紗,使西方讀者對于當代中國女性的狀況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促進了中西方的溝通和了解。
四、結語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創作的繁榮期,而此時西方女性主義思想也進入了中國。戴乃迭敏銳地捕捉到了女性主義對于中國女性文學的影響,并積極地將新時期的女性作家作品推介到海外。但她并未將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強加給復雜的中國社會,而是對中國女性問題給予了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她運用本土化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在選材上偏重體現女性主體意識的新時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并且在譯文的序跋和介紹性文章中詳細闡釋了中國女性的現實狀況,以提高中國女性文學作品的海外接受度。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戴乃迭運用相對溫和而不失靈活的翻譯方法,提升了譯文中的女性主體意識,強化了作品的女性主義色彩,從而使女性在語言中顯形,而這“意味著讓女性在現實世界中被看見和被聽見”(費拉德,2007:29)。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關注男性和女性的權力關系,屬于翻譯研究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女性主義翻譯研究未來的發展必將更為廣闊,蔣驍華(2004:15)指出:“女性主義將會進一步影響我國的翻譯研究和實踐。”
[1]Bassnett,S.&A.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and Culture[C].New York:Pinter,1990.
[2]Bhabha,H.Life at the Border:Hybrid Identities of the Present[J].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1997,(l):30-31.
[3]Davis,K.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Hamers,J.&M.Blanc.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5]Simon,S.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6]von Flotow,L.Feminist Translation[J].TTR:Traduction,Terminologie,Redaction,1991,(2).
[7]Yang,Gladys.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C].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1982.5-16.
[8]Zhang Jie &Gladys Yang.Leaden Wings[M].London:Virago Press,1987.
[9]Zhang Jie &H.Goldblatt.Heavy Wings[M].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
[10]費拉德.翻譯與性別:女性主義時代的翻譯[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11]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2]蔣驍華.女性主義對翻譯理論的影響[J].中國翻譯,2004,(4):10-15.
[13]李小江.解讀女人[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14]李銀河.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精選[C].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7.
[15]劉亞儒.加拿大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起源、發展和現狀[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2):11-16.
[16]穆雷.翻譯與女性文學——朱虹教授訪談錄[J].外國語言文學,2003,(1):41-44.
[17]吳文安.后殖民翻譯研究——翻譯和權力關系[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18]楊憲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19]楊憲益,文明國.楊憲益對話集: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C].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
[20]于東曄.女性視域——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女性話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1]于東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D].蘇州大學,2003.
[22]張潔.沉重的翅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3]張潔.方舟[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4]張裕禾,錢林森.關于文化身份的對話[A].樂黛云.跨文化對話[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25]趙學齡.翻譯界盡人皆知的一對夫婦——記楊憲益、戴乃迭[A].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C].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5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