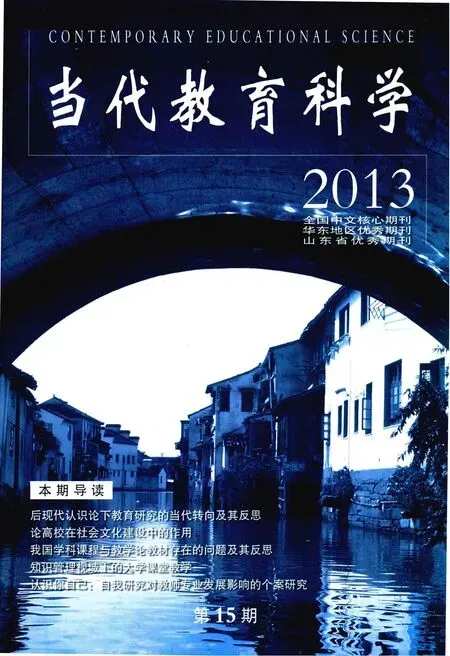認識你自己:自我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影響的個案研究*
●吳穎芳
在教育革新的國內外背景下,教師發展的研究轉向促使人們達成共識,即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教學是否有效、學生學習是否成功的攸關要素。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要“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要“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師德水平和業務能力,增強教師教書育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也就是說,專業知能及情意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精髓,是使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感到滿意的必備要素。因此,如何實現專業發展以適應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求是每一位高校教師必須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
對于(英語)教師發展主題,國內外學術界對教師的職前培訓和職后發展都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1][2]。自我研究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西方教師教育者為了改變傳統說教式的教師教育方式轉而研究自身的教學實踐運動,并逐漸流行為教師研究的新取向[3]。敘事研究是教師發展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4]。敘事研究認為,個體在敘述人生故事與回憶自傳體記憶的過程中建構與發展自我[5],即教師敘事要理解和探究個體所經歷的具體教育體驗,目的要認識、建構和發展專業自我,凸顯了科學量化方法在研究自我和同一性方面的不足,盡管教育實證分析具有非常可靠的預見性,但教師的教育生活卻日益變得枯燥、規則化[6]。敘事研究則可以自下而上地呈現教師自我專業發展過程所具有的獨特性、情境性、自主能動性、豐富性和長期性等特點,使人們由關注教師的外在行為轉而深入思考行為背后的思想原因。
作為一名對教師發展有困惑亦有理想的教師研究者,我具有7年(2006-今)在地方高校執教公共英語的經歷,這7年是我的專業自我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所以這一階段是“自我研究”的寶貴資源。在本文中,我將走回自己的教師生活世界,圍繞“教師為何要進行專業發展”、“教師如何認識專業自我”的主線講述“教師如何學會教學”的故事,對教師專業發展歷程進行個人化詮釋。
一、“我”為何要進行專業發展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教師職業規范的經典詮釋,其實,今天的教師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同時,自己卻面臨著不解之惑。十八大報告告訴我們:教育、就業已與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并列,昔日象牙塔的“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式消費”,高等教育的價值和質量備受社會詬病;大部分高校公共英語課程的定位與目標簡化為“四六級”,在課堂上,我每天都能夠感受到學生來自的挑戰和壓力,思考著“我為何而在”的價值;同時還要擔負大學教師“不出版就死亡”的生存格局。這種困境使我產生了發展的困惑,困惑于社會發展速度之快、發展中與他人的差距之大以及自我未來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直接帶來的是人生挫敗感和專業發展走向的不確定感:走出教學,作為教師的我將不復存在;走進教學,便產生無力感。這種發展困惑產生了幸福困惑,幸福困惑進而帶來了人生意義困惑——學而為師,我的存在價值在哪里? 我的職業幸福感在哪里?
對困惑追根溯源,除了主觀努力不夠,我找了兩條客觀原因:首先,職前專業成長營養不良。2006年9月,我正式走上大學講臺,標志著我告別學生身份,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在品嘗了“長大后我就成了你”的那份最初的欣喜與驕傲后,卻再難感受到身為教師的神氣與自信,面對學生,只有忐忑,不知道怎么給學生上課。本科階段,必修學習課程除專業課程(英語)和教育課程(教育學、心理學)外,其他課程與非師范專業學生相同,沒有教學實習;研究生階段,必修學習課程除專業課程(英語)和教育課程(英語教學論、第二語言習得概論)外,其他課程與非師范專業研究生相同,沒有教學實習;這兩個階段的共同點是:教學實習缺席。由于缺乏實踐,教育學、心理學、英語教學論、第二語言習得概論的學習效果與坐在教室學游泳、拿著教材學駕駛無異,誠如克蘭迪寧講述的故事所言:“作為一名學生,每當我們上教師教育課的時候,就是在這里等待被灌輸理論,似乎以后我們就能把這些理論應用到實踐中。我感到莫名的困擾,但是我知道這些大學教授將要對我們的學習進行考評,雖然我還沒有真正弄懂這些神圣的理論,但是我需要向我的大學教師顯示我已經懂了,而且能夠把它們運用到實踐中,這些神圣的理論讓我感覺不滿意和不確定……”。Richards 也在自己的研究中表示:曾接受這種職前教師知識基礎培訓的畢業生,幾乎沒有人宣稱自己的教學與先前的這種準教師培訓有任何直接關系[7]。其次,職后專業培訓食而不化。在入職三、四年后,我意識到教學舉步維艱,主動參與專業培訓,內容從如何上好一門專業課(精讀課、寫作課、口語課)到有效課堂等,這些題目很吸引人,培訓者介紹的教學理論、教育理念和教學過程也很令人激動,但理論只是在理論上可行,理念只是在理念上先進,過程只是在培訓者的課堂上激動,自己卻很難將培訓者傳授的精髓移植到自己的課堂。這有個人對課程駕馭能力差異的原因,這種差距是教學經驗、教育智慧、學術背景的凝練,短時間內幾乎無法跨越;也有所處教學環境不同的因素,培訓者大多來自國內外語院校或重點大學甚至國外高校,自己所處的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二者在學術環境、學生質量、學習資源等方面大相徑庭,由此所影響的教師發展意識與程度也千差萬別。所以職后專業培訓離自己的現實很遠,只可遠觀。
二、“我”如何學會教學
盡管教師發展會受到不利客觀因素的影響,而我認為主觀因素仍然是影響個體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外因只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本。可以說,在教師發展歷程中,教師的專業自我意識,即“意識到作為教師的自我”是教師發展的前提,自我意識的強烈程度決定著自身專業發展的進程。約瑟德早在1955年就專門系統地研究了“教師自我”對其日常教育行為的支配性作用[8],展示了教師自我意識對教師專業實踐獨一無二的價值。自我研究又起始于教師對自己日常教學的觀察和反思,不同階段的自我意識和形象則構成了“教師如何學會教學”這一連續的畫面。以下我把自己的發展歷程按照專業自我的發展狀態分成三個階段,在敘述中探究“專業自我”在教師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專業自我原始期
2006年,我艱苦學成得以棲身教職,王國維總結人生之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對我心情的寫照。初為人師,我對教學躊躇滿志,一開始就告誡自己“教學要用心、盡力、做好、盡職”,思考“如何面對臺下的莘莘學子? 如何明確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夢想“成長為一個教書育人的教師典范”。這夢想在我的想象中展開:教學再容易不過,我的老師以前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學生。所以,我的教學風景中山水分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美國學者Lortie 曾提出“學徒觀察”(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9],這一概念是說新入職教師往往模仿上學時老師的樣子施教。我搜羅盡可能多的背景材料,期望給學生一堂百科全書式的英語課,包括文化背景、段落大意、詞匯句型等,我唯恐漏掉知識點,盡力做到面面俱到。盡管我也信奉“在課堂上要特別注意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加強師生交流,充分體現學生自主體作用,讓學生學得容易,學得輕松,學得愉快”這樣的教學理念,自己的行為卻與這一理念背道而馳,因為課堂的目標就是講完所有準備內容,講不完就會引發極大的焦慮,這樣的壓力迫使我沒有時間去關心學生需求和學習效果,總以“反正自己盡力了”來安慰自己,在這樣的自我陶醉中我度過了教師生涯的第1、2年。
作為一名教師,我是誰?我存在的價值是什么?這一階段的教學行為表明:拿著課本對學生宣講百科知識的那個人,就是作為教師的我,我對學生知識灌輸的多少是我專業知能的唯一體現;“大學生學習主要靠自學”的觀點讓我覺得大學教師的作用并不像中小學教師那樣重要,至于我的“教”是不是引發學生的“學”、他們學得如何,跟我關系不大,這些所思所行體現了我的專業情意。可以說,這一階段的專業自我只是自然存在著,教師是我的職業符號,內心深處并未領悟到專業自我的存在,而專業自我存在和領悟到專業自我存在完全不同,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說真正的實在是存在,真正的存在唯有通過思維才能把握[10]。這一階段我對“我是誰”、“我存在的意義”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教師與教學的形式層面,并滿足于此,因此也就不具有反思意識和發展意識。因此,我把這稱之為專業自我自然存在期。
(二)專業自我萌發期
潛伏在專業自我自然存在期的危機在第3年的第一次“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s)”中爆發。“關鍵事件”是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刺激性因素,指“個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教師要圍繞該事件做出關鍵性決策,它促使教師選擇特定的專業行為,并通過自我澄清的過程對自己的專業進行解構和重構”[11]。那次趕去上課,一上講臺就發現一張紙條:我們不喜歡您的課。我幾近眩暈,內心沉到谷底,我意識到自己的教學失敗無效、亟需改進。此時的教學風景中山水已看不分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舊的自我已被否定,新的自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作為教師的自我。失去自我是為了找到自我、發展自我。王國維總結人生之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可以寫照這一階段的經歷。
1.“我”意識到專業自我的存在
紙條事件之后,我問自己:什么是教師的責任?我的答案是:在教學過程中主動地去了解學生的所想、所惑、所得、所感,整理科學的教學理念,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教案,實施卓有成效的教學方法,創造感染學生積極學習、攝取知識的氛圍,并以教師的人格魅力贏得學生的敬愛,激勵他們為理想、為目標做堅持不懈的努力,從而獲得良好的個人發展。責任感的確立,讓我下定決心“增強上課技能,提高教學質量”,為此,我經常問自己“這堂課上的成功嗎? 學生滿意嗎”? 并閱讀了一些教學專著,比如《非常教師——優質教學的精髓》、《教學方法手冊》、《課堂提問的藝術——發展教師的有效提問技能》、《多元智能教學》、《名師營造課堂氛圍的經典細節》等,我寄希望于閱讀中獲得成功教學的法則。還在學生當中開展問卷訪談,了解學生對課堂的看法。然后我做了教學調整,比如減少單詞的講解,增加實用句型的練習,擴大廣泛閱讀的力度,改進課堂時間的分配。教師生涯第4年學生評教結果是“課程進行得很順利”。這說明我的專業知能剛好滿足學生的要求,專業情意也在為增進專業知能的努力中萌芽,這二者的發展都與內心深處已領悟到的專業自我存在有關——作為教師,我的教學必須滿足學生要求,否則,就被學生否定、也不被自己接納,我就失去了專業自我。即使如此,這時期的專業自我仍然沒有徹底脫離自然存在期的自我意識和形象,因為我的實際教學行為與自己的“責任書”仍然無法契合,我不清楚學生想讓我教什么,也不知道教學目標、難點重點為何物,也沒有創造感染學生的課堂氛圍。教學帶來的“無奈與疲憊”使我像盲人摸象一樣總是不確定教學的真相、自我的走向,教學生活給我一種不安全感。
2.“我”改變專業自我的存在
領悟到專業自我存在并不能給我帶來安全感和正義感,因為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會教學,也說不出自身教學存在的問題,我在同一教學模式中輪回,這樣的輪回在第5年的第二次關鍵事件中被打破:面對一團沉默的學生,本著完成教學任務的宗旨,我硬著頭皮按照自己的預設完成“我的任務”,學生的學習效果當然不在計劃之內。結束任務,我匆匆逃離現場,走在路上,我內心沉重、迷茫:完成任務很簡單,可這對無辜的學生有價值嗎? 而我又何苦為這承擔一切? 可是我是教師,教學是我的生活,這生活如果給我帶來的是重復的煩惱、孤寂的獨白,還有繼續的必要嗎?我要改變自己、改變課堂!為了拒絕重復一樣的課堂,每次課我都會涉及不同的內容,即使內容一樣,呈現的方式和時間段也會不同。我還比較哪種呈現方式、哪個時間流程的效果較好。這一年學生一致認為我“認真、負責、耐心”,這是改變專業自我的存在所帶來的結果。這一階段,我對教學負有使命感,對學生懷有責任感,對自我抱有認同感,我的專業情意已逐步養成,而專業知能仍然處于徘徊期,在于我仍然沒有克服自身的缺陷,我性格隨和但偏執、做事認真但不靈活,所以在教學中,我只堅持我認可的價值觀,鼓勵學生腳踏實地獲得知識、反對他們急功近利只想考試,因此懸置學生的考試需求,教學內容遠離學生的需求,教學還是以自己為中心。
(三)專業自我意識發展期
關鍵事件、自我反思是促使我發現、領悟、改變專業自我存在狀態的關鍵因素,它們督促我不斷懷疑自我、否定自我又建構自我,而研究自我的意識與行動則是專業自我發展的飛躍。教師生涯的第6年,我使用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來研究自己的課堂、課堂中的自己,自我監控指“教師以文字、音頻、視頻記錄自己的課,將所獲得信息作為自我教學的反饋資源”[12]。課前,我在監控本上記錄自己的教學設計,保證課堂的流暢性;課中,我隨時隨地記錄我的教學節奏、時間分配、教學設想、突發事件等;課后,我則比較預設課和生成課的效果、檢查節奏是否緊湊、時間是否得當,“自我監控能幫助教師縮小想象教學和現實教學的巨大差距”[13],自我監控幫助我發現了自己的教學缺陷:內容多、信息量大;重點不突出;時間使用不當;灌輸說教方式居多。這些教學缺陷在過去的公開課中都被“重要他人”糾正過,為何自己今天才確認呢? 這是因為自己早已習慣于這種教學模式,陷于自己習慣的行為中,便很難質疑自己的行為,認清自身存在的缺陷,懷特海德把這種現象稱為“活的矛盾”,指“個體自身存在的矛盾,在某種情況下,這種矛盾可以穩定的共存,因為個體已經習慣適應于原有的經驗模式,很難以獨立于自身經驗之外的角度檢驗出這種矛盾”[14]。這些“活的矛盾”之所以難以被我鏟除,是因為其根深蒂固性,教學內容、重點、時間的缺陷跟我的學習方式有關,學生時代的我好讀書不求甚解,導致我的教學也帶有不分重點、不管多少、不顧時間的痕跡;教學方式跟我的家庭環境有關,我父母教育子女以言傳說教為主,導致我也不自覺地向學生灌輸很多,而學生對此并不樂于吸納多少。
在我教學生涯第6年結束第7年開始之際,我終于對自己的教學缺陷茅塞頓開,不僅確認了缺陷的內容,還知道了缺陷的淵源,自我研究解決了我在多年實踐中遭遇的困惑、緊張、焦慮和矛盾,同時也詮釋了教師專業自我的發現與建構的實踐性本質。Feiman指出:“學習教學應該被視為一個延續教師整個職業生涯的連續過程”[15],所以故事到這里并未結束,王國維人生境界之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告訴我教師進入教學自由王國的光仍然不是十分分明,教學風景中的山水仍然需要用研究的眼光、發展的意識才能領略到其風采。
三、“我”如何認識專業自我
我通過敘述教學經歷來促進自我專業反思、了解專業自我以改變未來的教學行為、提高教學質量、獲得教師專業發展,在這個敘述與回憶中,我更好地理解了專業自我的發展原因,認識了作為教師的我對自身身份的悅納過程。
第1、2年是我棲身于教師的階段,專業自我處于自然存在期,由于自己本身的學習風格和性格特性,也沒有經歷教師專業的實戰期,專業自我意識微弱,導致專業知能和專業情意發展趨于不發展狀態;第3、4年是我容身于教師的階段,由于專業自我意識的缺乏,導致我的行為出現嚴重缺陷,我失去了專業自我,我用各種方法彌補缺陷試圖找到它,專業自我意識的覺醒與領悟讓我暫時站穩腳跟,專業知能和專業情意發展趨于初步發展狀態;第5、6年是我安身于教師的階段,專業自我意識的改變和自我研究的行為使我逐漸立足,專業知能和專業情意發展趨于穩定發展狀態。第7年是我立命于教師的階段,專業自我的特征在自我研究的放大鏡下逐漸清晰,批判與發展專業自我是自我研究的結果和目標,專業知能和專業情意發展趨于持續發展狀態。維特根斯坦說“只有生活在自己的趣味中,才會有身心的安妥和應對環境的從容”,這時的我已建立自我的身份和志趣、確認自身的缺陷和特征,所以了解自我、認識自我是擺脫盲目與焦慮的途徑,自我研究是我專業發展的點睛之筆。
通過敘述和回憶我的教學經歷,我發現作為教師的我,不斷從對專業自我無知無覺的狀態發展到清醒認知的階段,自我意識的強烈程度又決定了研究教學、提高質量的進度和程度,專業知能的積淀分布在這一過程的各個階段,專業情意的養成體現于這一過程的始終,這也是自我專業發展的歷程,因為教師發展是指其智慧、經驗、態度繼續成長的過程[16]。Pennington 認為“只有當教學建立在兩種知識基礎上:了解學生和認識自我,它才最有效”[17],Combs 也說:“一個好教師……是一個知道運用‘自我’作為有效工具進行教學的人”[18]。兩人的觀點不謀而合,研究自我是進行有效教學的關鍵因素,因此教師自我研究最終回歸于那個古老的命題:認識你自己,這也是教師發展的起點和終點。
[1]Richards,Jack C.& Nunan,David(eds.),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吳一安等(編著).中國高校英語教師教育與發展研究[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3]呂立杰,劉靜炎.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教與學——西方國家教師教育者“自我研究”運動述評[J].全球教育展望,2010,(5):42-46.
[4]Clandinin,D.J.&Connelly,F.M.Narrative Inquiry:Experience ancl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San Francis(c):Josse Bass Publishers,2000.
[5]汪新建,朱艷麗.敘述方式、自我視角與自我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0,(12):1858-1863.
[6]吳宗杰.外語教師發展的研究范式[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08,(3):55-60.
[7]Richards.Jack C.The dilemma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In Jack.C.Richards & David Nunan(eds.),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3.
[8]胡福貞,唐日新,胡銀泉.美國教師自我研究的評析[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5):33-38.
[9]Lortie,Dan C.School Teacher:A Sociological Stud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62.
[10]朱輝榮.論自我存在、規定與結構[J].社會科學家,2012,(8):17-20.
[11]Sikes,P.Teacher Careers:Crisis and Contiuities[M].UK:Falmer Press,1985:57.
[12][13]Richards,Jack C.The language teaching matrix[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18-119.
[14]Whitehead,J.The growih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Creating your own living educational theories [M].Bournemouth Hyde Paolications,1993.
[15]Feiman-Nemser,S.From Preparation to Practice:Designing a Continuum to Strengthen and Sustain Teaching [J].Teachers college Record,2001,103:1013-105.
[16]Lange,Dale E.A blueprint for teachers development [A].In Jack.C.Richards &Davicl Nunan(eds.),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45.
[17]Pennington,Martha C.A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cus for th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A].In Jack.C.Richards &Tavid Nunan(eds.),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35.
[18]Combs,A.W.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Teachers[M].Allyn &Bacon,Inc.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