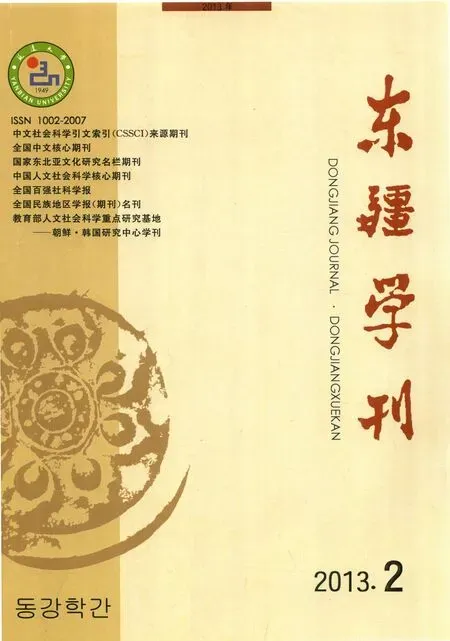論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
付 健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利益主體的數量激增并逐漸分化,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也不斷增強。而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中涉及多方利益主體的矛盾和沖突也越來越頻繁、突出,這集中表現在城市化進程中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例如,2007年的廈門 PX項目事件,2008年的甘肅隴南拆遷事件,2011年的廣東烏坎事件等等。這些社會矛盾的解決必須改變過去由政府單一主導城市規劃建設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應保證相關利益主體參與到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中。因而,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問題越來越成為城市治理、城市化發展的重點。
二、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
正如有學者指出:“沒有一個政治概念像‘公眾參與’那樣在近幾年的中國政治話語和學術中流行,而使用又是那樣模糊混亂。”[1](1)筆者認為,公眾參與是 20世紀 60年代民權運動發展以來出現的特定社會現象,“公眾參與”這一概念只有在參與民主的理論框架中才能得到恰當理解和有效界定,“公眾參與”只有在區別于代議制民主所包含的政治選舉以及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等街頭抗議活動時,才有其自身獨特的所指,因而,本文主要在以下意義上使用“公眾參與”的概念:“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公眾參與民主制度,應當是指公共權力在進行立法、制定公共政策、決定公共事務或進行公共治理時,由公共權力機構通過開放的途徑從公眾和利害相關的個人或組織獲取信息、聽取意見,并通過反饋互動對公共決策和治理行為產生影響的各種行為。它是公眾通過直接與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互動的方式決定公共事務和參與公共治理的過程,它不包括選舉,也不包括街頭行動和個人、組織的維權行動,”[1](5~7)它更強調公眾在與政府和平、理性溝通、對話、協商的基礎上參與公共事務和公共治理的行為與過程。
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是公眾參與在城市規劃領域的重要實踐,同時,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也推動了公眾參與的進一步發展。
作為現代意義的城市規劃發源地的美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對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進行了制度上的規定。[2](30~40)英國在 1947年頒布實施的《城鄉規劃法》中,就已經允許社會公眾就城市規劃發表意見,并且可以針對不滿意的規劃提起訴訟。到了20世紀60年代,基于對此前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模式的不滿,公眾開始更加主動直接參與到這種規劃中來,“公眾參與規劃”的意識得以真正誕生。1962年,保羅·達維多夫與托馬斯·瑞納發表了著名的《規劃選擇理論》,該文奠定了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的理論基礎。[3](103~115)1969年,由斯凱夫頓任主席的由英國負責規劃事務、由政府部長組建的特別小組提交了著名的“斯凱夫頓報告”,這被認為是英國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發展的里程碑。同年,雪莉· 阿恩斯坦發表了《公民參與的階梯》,[4](216~224)這篇文章“對公眾參與的方法和技術產生了巨大影響,至今仍廣為世界各地的公眾參與研究者和實踐者所采用”。[5](13)
我國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1980年制定的《城市規劃編制審批暫行辦法》使得公眾參與規劃的精神初步顯現;1991年,為了配合1990年的《城市規劃法》的施行而頒布實施《城市規劃編制辦法》,規定了規劃過程中展開公眾參與的原則性要求;[2](40~51)2008年施行的《城鄉規劃法》規定了諸多有關公眾參與的法律規范,從而使公眾參與在城市規劃領域取得了重大發展。與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的實踐同步,包括城市規劃理論研究者、政治學界、法學界等多領域的學者對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問題進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細致的研究。但是,“我國有關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自 20世紀 8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所討論,但至今只是在局部范圍內、在特定層次上得到一些嘗試,但在制度和實踐的整體上尚未全面推行”。[6](1)因而,如何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化、拓展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問題研究,進而對我國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的社會實踐發揮指導作用,就成為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問題研究的當務之急。筆者在此試圖以權利本位范式為視角,提出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概念,并對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權的存在基礎予以探討。
三、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
現有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研究雖然對公眾參與興起的歷史背景、理論基礎、內在內容以及實現機制、實踐發展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將公眾參與作為法律權利來予以探討的研究并不多見。雪莉· 阿恩斯坦在其《公民參與的階梯》一文中,提出了公民參與是公民權利的概念。1981年,國際建筑師聯合會第十四屆世界會議通過了《華沙宣言》,該宣言提出了“市民參與城市發展過程,應當認作是一項基本權利”的主張。[7](43)但是這些論述缺乏對公眾參與權系統、詳細的闡釋,而僅限于倡導式的主張,所以本文將對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的存在基礎予以進一步的闡釋。
當代中國法哲學的研究范式經歷了從階級斗爭范式到權利本位范式的轉換。權利本位范式表征為確立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學基本范疇的地位,并在此基礎上確立權利作為法學基石范疇(權利為本位)。權利本位范式將我們所處的時代概括為“權利時代”,并對權利時代的理論景象作了這樣的描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邁向權利的時代,是一個權利備受關注和尊重的時代,是一個權利話語越來越彰顯和張揚的時代。我們越來越習慣于從權利的角度來理解法律問題,來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8](3)權利本位范式的提出,“使得我們擁有了全景式的法哲學視窗,看到權利構成現代社會法律實踐的實質和鮮明特征:人們,無論是個體,還是利益集團,關于法律的要求和主張,一般首先是以權利主張的方式提出”。[9](81~82)以權利本位范式來透視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問題,就漸顯了由公眾參與演變而來的公眾參與權概念。筆者認為,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的存在基礎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歸結
“從長遠來看,社會和經濟現代化導致參與擴大。”[10](1)經濟發展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根本原因,而市場經濟則是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根本動力。[11](168~17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瓦解了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使得在國家之外、市場之中發展出具有自身合法主體地位的利益主體,改變了過去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利益格局。市場經濟的發展放開了對利益主體的過度束縛,促進了利益主體在平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這些不同利益群體和社會成員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將自己的意志反映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因此公眾參與就成為必然。”[12](2)利益的多元格局使得利益主體必須有其利益的表達渠道,“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公民的財富和利益日益增加,獨立、多元的經濟主體日益成長和壯大,獨立、多元化的利益產生獨立和多元的權利訴求”,這成為公眾參與興起的根本動因。[1](10)
城市規劃過程中同樣涉及到多元利益主體,這包括城市人民政府與城市規劃主管部門、城市開發商以及其他私益主體、社會公眾等等。[13](203~208)“城市規劃實質上是城市空間利益的分配,存在各種巨大的利益。由于沒有公眾參與,就由少數領導和專家在由他們的意志決定著影響公眾巨大利益的分配。”[5](2)因而,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問題,實際上就是城市規劃中的多元利益主體表達各自合法利益訴求的法律權利問題。利益主體合法的利益訴求是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的本質所在,也是其必然要求。
法律制度通過承認某些利益,按照各種法令通過司法、行政過程來確定承認與實現那些利益的限度以及努力保障在確定限度內被承認的利益而達到法律秩序的目的。[14](39)法律通過權利與義務的設定以及法律責任的追究來實現對利益的承認和保障,“權利、義務是法律的價值得以實現的方式,正是通過權利和義務的宣告與落實,國家把特定階級或人民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變為國家和法律的價值取向和選擇,并借助于國家權威和法律程序加以實現”。[9](43)法律權利與利益有著密切的關聯,“著重從權利的法律功能和社會價值的角度分析,可以把權利解釋為規定或隱含在官僚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9](266~272)
因而,從本質上看,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是對城市規劃過程中對各利益主體合法利益訴求的承認,進而通過法律上的權利設置和法律渠道加以表達,實現其各自的合法利益訴求。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各自獨立、合法的利益是公眾參與權存在的邏輯前提,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則是城市規劃過程中各利益主體表達各自利益訴求的必然要求。
(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
雖然20世紀60年代作為公眾參與理論支撐的參與民主理論才開始逐漸興起,但是盧梭早已對參與民主有過重要論述,“在參與民主理論家中,盧梭或許可以被認為是最為卓越的代表”。[15](22)盧梭諷刺“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16](121)卡羅爾·佩特曼則提出了系統完整的參與民主理論,認為“在參與理論中,政治不僅限制于通常所指的全國性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參與理論中,‘參與’又一次指在決策過程中的(平等 )參加,‘政治平等’指在決策結果方面的權力平等”,參與模式意味著最大程度的輸入亦即參與,而輸出的不僅包括政策(決定),還包括個人的社會能力和政治能力的發展。[15](39~40)美國學者科恩在其民主定義中將參與作為關鍵性概念,并且認為“對參與的分析可以進一步闡明民主,弄清參與的具體內容就可以對任何實際社會所實現的民主程度作出理性的估價”。[17](10~11)作為參與民主理論在 20世紀后期發展的協商民主理論則主張,公民參與而反對精英主義的憲政解釋,這同樣肯定了公眾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作為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新近發展,它更為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西方參與民主理論的興起為我國公眾參與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而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也內在地要求公眾參與。憲法從根本上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人民當家作主成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內涵和內在要求。
2000年 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引導人民群眾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2003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工作,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實行公示、聽證等制度。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就明確提出了公眾參與權的概念。
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是公眾參與權的重要實踐場域,是公眾參與權在城市規劃領域的具體落實和實踐發展,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所蘊含的人民當家作主,從本質上決定了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內容。西方近代以來的代議制民主在 20世紀 60年代遭遇到了危機,因而參與民主理論興起、參與民主理論并不是代議制民主的替代,而是其必要的補充。我國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從根本上決定了公眾參與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被認為是與自由權、平等權、社會權一樣的人權的基本組成部分”。[18]因而,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不僅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同樣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三)風險社會科學決策的必然選擇
德國著名學者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了“風險社會”的理論。“由于現代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顯現的時間滯后性、發作的突發性和超常規性”,[19](99)就使得“在事關全人類生死存亡的巨大風險和災難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專家”,[20](90)科學不再僅僅只是被當作一種處理問題的源泉,而且也被視為一種形成風險、造成問題的原因,“一種科學的解釋神秘化過程開始了”,科學知識的非壟斷化出現了,科學對真理的控制越來越不夠有力,科學也成為反思和懷疑的對象。在這種科學、技術、專家失去對知識、真理的壟斷地位,而風險又源于人的決策的風險社會中,決策的作出“總是存在各種現代性主體和受影響群體的競爭和沖突的要求、利益和觀點,它們共同被推動,以原因和結果、策動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風險”。[21](28)“在對風險的關注中,自然科學家不知不覺地以某種方式使自己失去了權力,將自己推向了民主化。”[21](68)“風險整體轉型的主要影響是產生了新的合法性危機:貫穿發展過程當中的民意、認識論基礎上的科學權威、社會制度體現與維護的權威都不斷地受到削弱。”[22]在風險社會里,傳統的資產階級工業社會在政治體系中決策權威集中化的設計和想法已經行不通,試圖一方面執行公民的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在影響政治決策的時候保留等級權威乃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僅僅想把民主制的規則限定在政治代表的選擇上已經不可行。政治的決策過程再也不能僅僅被理解為幾個精英或領導預先決定的某種模式的單純強制或簡單執行。[21](235~236)危機的出路在于走向增強民主風險管理的道路。“為了克服這些普遍存在的風險,民主社會不得不保持某些基本的價值觀,如公民了解和參與決策過程的權利。”[23](257)
在風險社會下,現代城市規劃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就顯得至關重要。有學者將西方的城市規劃理論分為四個時期,認為其中 20世紀 60年代開始的第二代理論為現代規劃理論修正時期。這一代城市規劃理論的特點就在于對第一代的現代規劃理論時期基于工具理性單純強調規劃工作的科學性予以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理論。勒·庫布西耶的學說最能反映60年代之前的這種規劃思想,而在其影響下產生的《雅典憲章》也最能體現這種規劃思想。“勒·庫布西耶是大型的、機器時代、垂直等級和集權城市的極端表現。”其城市秩序是解析的純粹形式和無可替代的機械要求的浪漫結合。勒·庫布西耶關于城市主義原理的格言是“規劃:獨裁者”,強調城市的單一理性規劃,認為普遍的科學真理具有無可替代的權威,規劃本身的才智可以掃除一切障礙。勒·庫布西耶堅信城市是機械時代意識的理性表達,根本不承認居民在城市規劃設計方面有什么發言權。[24](129~148)《雅典憲章》認為機械時代無計劃、無秩序的發展導致了現代城市的混亂,強調現代市鎮計劃和建筑技術在改造城市工作上的應用。[31]
與之相反,簡·雅各布斯則認為:“所有城市規劃的藝術和科學都無助于阻擋大片城市地區的衰敗——以及在這種衰敗之前毫無生氣的狀態”,“城市有著遠比車輛交通要錯綜復雜得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26](3~5)簡·雅各布斯對以勒·庫布西耶為代表的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規劃進行了批判,而 1977年制定的《馬丘比丘憲章》則可以視為是對《雅典憲章》的修正。簡·雅各布斯批判了城市改造和規劃中的偽科學,認為城市里的市民最為熟悉城市,認為“在城市生活、職責和擔憂方面,城市里的人最有發言權”,認為任何規劃方面的專業知識都不可以取代市民對具體地方的了解,主張城市規劃應該考慮城市市民的需要和意見以及自治權利。《馬丘比丘憲章》主張科學技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正確運用,認為“雅典代表的是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學說中的理性主義,而馬丘比丘代表的卻都是理性派所沒有包括的單憑邏輯不能分類的種種一切”,因此,“城市規劃必須建立在各專業設計人、城市居民以及公眾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系統的不斷的互相協作配合的基礎上”。[27](2)
因此可以說,簡·雅各布斯對勒·庫布西耶的批判以及《馬丘比丘憲章》對《雅典憲章》的修正可以視為對城市規劃中單純重視規劃者和專家的權威、科學技術的作用的反思和批判,進而對城市規劃中公眾的需要和參與城市規劃中的決策予以強調。這些可以視為風險社會城市規劃中科學決策的必然要求。“公眾參與在中國發展,也是中國處于風險社會必要的制度建設需要”。[1](13)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是風險社會中強調公眾參與決策以應對政府、領導、專家主導決策所帶來的危機的必要擴展和自然延伸,同時也是城市規劃領域理論規劃思想變革的必然發展。風險社會為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提供了存在的社會基礎。
(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然訴求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利益沖突、權力腐敗、社會矛盾等是影響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城市化進程中發生的涉及城市改造、居民拆遷的上訪乃至極端事件表明,有一些關于城市改造的建設決策和措施并沒能很好地吸納和包容市民的需要和意見。[28](4)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關涉城市社會治安的穩定和城市治理的秩序,進而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大局,因而,這些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解決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公眾參與是權力再分配,通過這種再分配,使那些當前被排除在政治和經濟過程之外的弱勢公民能真正被包含進來,能夠參與到談判和決策中來,使他們的利益得以保護。”[5](23)而強調公眾參與權,則使得民意表達的渠道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有利于更多的民眾參與討論和決策,就解決社會矛盾提出解決方案并進行充分論證,尋找合理的而為各社會主體所接受的可行的解決方法,實現科學民主決策,防止決策失誤而導致的社會混亂”。[29](436)要適應我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發展變化,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使得城市規劃中的相關利益主體和社會公眾參與到城市規劃過程中來,使得利益主體有其利益表達渠道,有效地將社會利益主體的矛盾和沖突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前得到化解;通過參與權的行使,公眾具有“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在此基礎上達成的決策和法律更容易得到公眾的接受和遵守,有助于化解政府決策、法律與公眾之間的矛盾。[15](26)
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有利于公眾對公權力運行的監督,是防止腐敗的有力措施。當權力不受限制和制約時,權力即會被濫用,進而導致腐敗。對權力的限制和制約不僅需要公權力相互之間的制約和平衡,而且同樣需要公民權利對公權力的監督,“公民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對公共權力有效制約的基本條件”。[30](3)這種在公眾參與下形成的城市規劃編制方案和城市規劃過程中運行的公權力,使得公權力受到了公眾的有效監督,因而有利于防止腐敗,有利于化解“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31](20)這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相符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因而有利于城市治理的和諧,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四、結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成為推動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權興起的根本動因,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則內在要求公眾在城市規劃中享有充分的參與權利,風險社會則是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客觀條件,最終通過法律途徑保障公眾在城市規劃中的參與權利,便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1]蔡定劍主編:《公眾參與:風險社會的制度建設》,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2]陳振宇:《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程序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3]Davidof P,Reiner T A.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62,28(2).
[4]Sherry R.Arnstein,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Vol.35,No.4,July 1969.
[5]蔡定劍主編:《公眾參與:歐洲的制度和經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6]孫施文:《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國外城市規劃》,2002年第 2期。
[7]林齡譯:《國際建筑師聯合會第十四屆世界會議:建筑師華沙宣言》,《世界建筑》,1981年第 5期。
[8]張文顯、姚建宗:《權利時代的理論景象》,《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年第 5期。
[9]張文顯:《法哲學通論》,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9年。
[10][美 ]塞繆爾· P· 亨廷頓、瓊· 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中的政治參與》,汪曉壽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
[11]王立京:《中國公民參與制度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
[12]王周戶主編:《公眾參與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13]王錫鋅主編:《行政過程中公眾參與的制度實踐》,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
[14][美 ]羅斯科· 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15][美 ]卡羅爾· 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法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17][美 ]科恩:《論民主》 ,聶崇信、朱秀賢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18]鄧聿文:《將公民參與權作為一項公共品向社會提供》 ,《學習時報》 ,2009-5-4。
[19]陳家剛:《風險社會與協商民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 3期。
[20][德 ]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王武龍編譯,載薛曉源、周戰超主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21][德 ]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
[22][荷 ]沃特·阿赫特貝格:《民主、正義與風險社會:生態民主政治的形態與意義》,周戰超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 3期。
[23][加 ]邁克爾·梅赫塔:《風險與決策:科技沖突環境下的公共參與》,湯濤編譯 ,載薛曉源、周戰超主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24][美 ]詹姆斯· 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胡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25]《雅典憲章》 ,《城市發展研究》,2007年第 5期。
[26][加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
[27]陳占祥譯:《馬丘比丘憲章》,《城市規劃研究》,1979年第 6期。
[28]周江評、孫明潔:《城市規劃和發展決策中的公眾參與——西方有關文獻及啟示》,《國外城市規劃》,2005年第 4期。
[29]何士青:《論協商民主:基于社會和諧的視角》,《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 4期。
[30]賈西津主編:《中國公民參與:案例與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31]張平:《中國轉型社會公共理性特性論》,《湘潭大學學報》,2012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