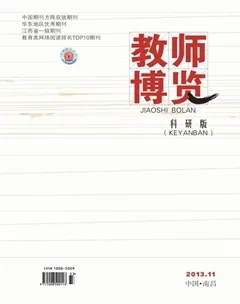西方音樂中的理性與感性調和體
[摘 要]自西方音樂成型以來,理性與感性這對難以調解的矛盾就一直以各種姿態相互對立著,從最早基督教的宗教理性到后來的反宗教人文主義理性,無論是哪種理性都一直與感性的入侵進行著似乎永無休止的斗爭。然而,在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的理性與感性卻得到了暫時的調和,這個時期的音樂將理性的內容與感性的形式較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關鍵詞]理性;感性;內容;形式;浪漫主義
一、理性與感性的歷史演變
“在希臘神話中,音樂有著一種神圣的源頭:它的發明者和早期實踐者是神和半神,如阿波羅、安菲翁和奧菲歐。”[1]可見,西方音樂的源頭可追溯到古希臘的神話中。在神話故事中,太陽神阿波羅崇尚著理性的藝術,而酒神狄奧尼索斯則崇尚著感性的藝術。原來,理性與感性早在神話世界中就已出現。
自公元392年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起,后來占西方音樂主流的宗教音樂便開始了它的發展歷程。作為宗教重要傳播工具之一的音樂,經歷了一個從“思”到“念”,再到“唱”的發展過程。從一開始的思想禱告,到后來的誦念經文,再到最后的吟唱《圣經》,極度理性的宗教音樂其實已經在無形當中打開了一扇通向感性的小門,這其中“唱”與“念”的矛盾就體現出了感性與理性的矛盾。在這之后,這對矛盾沖突不斷發展,從最開始的宗教音樂內部轉變到了宗教音樂與世俗音樂之間。脫離了宗教音樂的極端理性范疇,感性的世俗音樂不斷壯大,并對宗教音樂產生著威脅。終于,感性的世俗因素滲透進了宗教音樂中,孔杜克圖斯(內容與世俗有關,不受禮拜儀式約束的一種宗教音樂體裁)的出現印證了這一點。
除音樂的內容以外,原本單一、理性的音樂形式也受到了感性因素的侵入。而在中世紀表現最為突出的感性與理性形式,則體現在了和聲和復調這兩種音樂織體身上。理性的復調與感性的和聲,從中世紀開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處于爭斗狀態。整個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作為凌駕于一切世俗權力之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思想上壓迫著人們。人們為了擺脫由基督教文化的內在矛盾引發的弊端,決定以文藝復興運動進行反擊。這場在思想文化領域領導的反封建文化運動,以人文主義精神為核心,倡導個性解放,反對愚昧迷信的神學思想。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波及到了音樂的領域,它成功地使音樂同文學藝術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脫離了宗教束縛的音樂,再次向感性靠攏。緊接著的巴洛克時期是一個連接主調與復調的時期,也是一個連接聲樂與器樂的時期。中世紀宗教之所以禁止樂器和主調,就是因為二者有著感性的內在本質。而巴洛克時期對這二者的逐漸重視,又為音樂增添了一份感性特征。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又一大型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啟蒙運動意義上的理性有一個重要特征,這就是:相信經驗、要求與現實生活發生關系,這樣一種思想的背后是相信人的理性的巨大作用。”[2]那么,在這種理性思潮影響下的音樂,自然也就朝著理性邁進了一大步。
二、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內容的理性敘述
當人們談到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的特點時,總是會不加思索地將其與“感性和非規整”相聯系。當然,這一觀點并非不對,它只是概括得過于籠統罷了。這里說的感性實際上是指音樂形式中的感性,然而,浪漫主義時期音樂除了感性的一面,還有理性的一面。那么,音樂內容中的“理性”究竟該如何定義呢?在筆者看來,把抽象、非物象的音符與現實相結合,轉換成可描述的、栩栩如生的現實畫面,從而引起人們內心情感的共鳴,這就是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內容的理性特征。
這一時期較能體現音樂內容感性的音樂體裁大致有三種,即藝術歌曲、標題音樂以及歌劇。藝術歌曲是浪漫主義時期興起的一種音樂體裁,它將詩歌與音樂完美地結合于一體,其內涵豐富,且旋律特別能夠抒發詩歌的內容。舒伯特的《魔王》是以德國詩人歌德的同名敘事詩為詞而創作的一首歌曲,其歌詞內容真實地反映出了處于當時反動社會中的人們內心的壓抑。而另一種能體現內容理性的音樂體裁是標題音樂,它是浪漫主義時期作曲家將音樂與文學、戲劇、繪畫等其他姊妹藝術相結合而產生的又一綜合性音樂形式。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是標題交響曲的代表作品,他試圖通過該作品宣泄自己現實中的情感。除創作的動機和靈感基于現實外,該作品內容的情節也是在現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點在樂章內附著的文字解說中得以體現。第三種足以體現音樂內容理性的體裁是歌劇,以馬斯卡尼的真實主義歌劇《鄉村騎士》為例,該作品選擇了現實生活中的題材,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生活。
以上三種音樂體裁的作品都涉于現實,并且反映社會,如此一來,原本感性的音樂便被提升到了可物象化和概念化的理性水平。
三、音樂形式的感性表達
“浪漫主義音樂是西方理性音樂的最高體現,它既把理性音樂推向高峰,又導致其走向否定——引導出音樂中的非理性。”[3]這里所說的“非理性”,正是形式中的“感性”。
眾所周知,古典主義時期音樂以其理性、嚴謹的外在形式而著稱。與古典主義時期音樂相比,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在形式上就像一匹盡力掙脫束縛的野馬,努力擺脫規整形式所帶來的束縛。而這一形式則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雖以調性音樂為主,但由于半音和聲及遠關系轉掉的頻繁應用,調性略顯含糊;2.在功能和聲的基礎上,和聲的色彩性不斷加強;3.配器手法迅速發展,華麗且多變;4.旋律強調抒情性,節奏多變,樂句結構伸縮性大。從以上四點可知,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無論是在和聲、節奏上,還是在樂句的結構或配器上,都與古典主義時期的音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接下來,我將從旋律、和聲、調式調性這三個方面著手,通過具體作品來挖掘出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形式的感性所在。
(一)個性的旋律
該時期旋律的個性化是感性形式的突出表現,其中以瓦格納的主導動機最為突出。從作品《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可知,他所采用的動機大多短小而集中,且對于同一對象有不同層次上的描述。圖1-a表現的是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的互相欽慕,而圖1-b則表達了兩人在引用藥物后而表露出的更為強烈的愛慕。
(二)豐富的和聲
而作為開浪漫主義之先河的貝多芬,他的部分作品極大地體現出了浪漫主義時期音樂豐富的和聲色彩性。在一些早期的鋼琴奏鳴曲中,大量屬七和弦各種轉位及導七和弦的運用,大大增加了音樂緊張的力度。此外,不協和的降二級和二級七和弦的運用在貝多芬的晚期奏鳴曲中也是隨處可見的,這些因素都加大了音樂內部的不穩定感。圖2是貝多芬第八鋼琴奏鳴曲的片段,調性為c小調,和聲依次為Ⅰ-Ⅵ-Ⅱ(七和弦第一轉為)-Ⅴ-Ⅰ,二級七和弦的轉為運用在此處為音樂增添了一份生機。
(三)多變的調式調性
而調式調性的感性變化則又一次在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奏鳴曲的展開部是將音樂的矛盾沖突進一步尖銳化的部分,在這一部分中貝多芬多采用副調與其遠關系調的調性對比來顯現矛盾,而這在古典主義時期理性的音樂形式中是不常見的。如在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中,副部在降E大調上完滿終止后,展開部卻在C大調上出現;而他的另一部第二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副部終止于E大調后,不久就在展開部的C大調上進入。
當然,除了旋律、和聲、調式調性之外,還有許多因素導致了音樂“整體原則的松動”,如多變的節奏、華麗的樂隊編配等等。正是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對于這種微觀細節因素的突出運用,才成就了它那獨具個性的、不受束縛的感性形式。
西方音樂中的理性與感性在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斗爭后,終于在浪漫主義時期達成了某種共識,即內容理性與形式感性的共同存在。從最開始的宗教理性,再到后來的反宗教人文主義理性,感性因素從未停止過對理性音樂的滲透,也正是由于這一股永不言敗的感性因素,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才能在反映現實以及表現情感上達到如此爐火純青的境界。
參考文獻
[1]唐納德·杰·格勞特.西方音樂史,[M]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9.
[2]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1.
[3]姚亞平.西方音樂的觀念,[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1.
[4] 趙林.西方文化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藍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