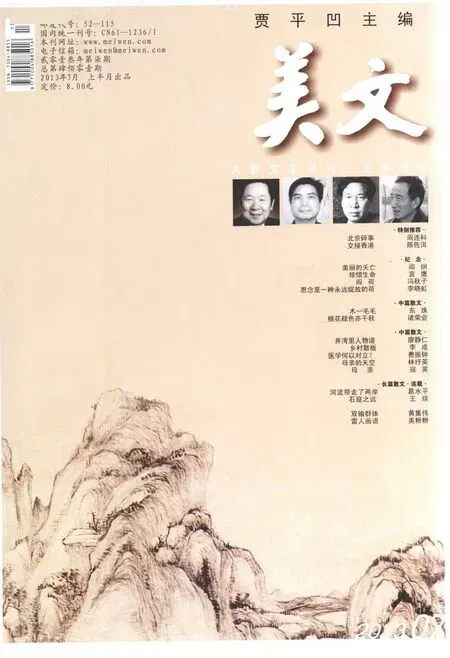大人物智伯
鮑鵬山

智伯要做“唯一”,要獨(dú)占晉國,于是,他的下一個(gè)目標(biāo),就是趙魏韓三家。
智伯做事,已經(jīng)形成了“智氏風(fēng)格”。這個(gè)風(fēng)格就是:恃強(qiáng)凌弱耍無賴,專憑武力不講理。他是一個(gè)強(qiáng)權(quán)崇拜者,實(shí)力崇拜者,以為一切以實(shí)力說話,只要有實(shí)力,可以為所欲為。而無實(shí)力的一方,既無反抗能力,則定無反抗選項(xiàng),只能唯命是從。
強(qiáng)權(quán)和實(shí)力崇拜者的基本思維特征是:不相信弱者有生存的能力,更不相信弱者有生存的權(quán)力,不相信人間社會(huì)有弱者的生存空間并有眾生的合力在維護(hù)這個(gè)空間,不相信天道之中有保護(hù)弱者的慈悲意愿和無形能量。
他們不相信世上還有正義,不相信為人還需道德。不相信正義和道德也有力量,更不相信正義和道德是終極的力量,并且這終極的力量總是站在弱者一邊。
什么叫“信仰”?就是“信”一種在我們上面需要我們“仰”視的崇高。所以,信仰就是讓我們學(xué)會(huì)自卑,有所敬畏,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甚至天下唯一。
何為沒有信仰?就是上面說到的種種“不相信”,他們只信所謂的“實(shí)力”。
一個(gè)沒有德行的“大人物”,他們做事的方法和風(fēng)格往往很小人,智伯的“智式風(fēng)格”就是小人風(fēng)格。他是晉國首屈一指大家族的家長(zhǎng),大貴族,執(zhí)政大臣,按說總該有些貴族風(fēng)格和氣派,但是,他做事風(fēng)格卻形同黑社會(huì),又酷似潑皮無賴。要比較戰(zhàn)國時(shí)代的諸侯大夫和春秋時(shí)代的諸侯大夫,有一個(gè)很大的區(qū)別就是:春秋時(shí)期的貴族,還有些貴族精神,還講些規(guī)則,還顧及自己的身份,不會(huì)做太失身份的事,而戰(zhàn)國時(shí)代的很多諸侯,卻完全是無賴,專以權(quán)詐對(duì)他人,只以成敗論英雄。歷史進(jìn)入戰(zhàn)國,世風(fēng)壞了。
智伯派人去韓康子那里,跟他說:“為了讓國家強(qiáng)大,你們應(yīng)該奉獻(xiàn)。請(qǐng)拿出土地來獻(xiàn)給公室,以體現(xiàn)自己的愛國精神。”
此時(shí)的晉國公室,名義上的代表是晉哀公,實(shí)際上就是智伯自己。所以,獻(xiàn)給國家,就是獻(xiàn)給智伯;愛國家,就是愛智伯。
自古以來,國家就是利益集團(tuán)的人質(zhì)綁票。國家國家,多少私利假汝名義而行!
智伯這樣一個(gè)趕走國君,獨(dú)占范氏、中行氏土地的人,說出這樣“愛國”的高論,簡(jiǎn)直是搞笑。只有厚顏無恥的人,才會(huì)這樣。
但韓康子不覺得搞笑,這太嚴(yán)肅了。土地!簡(jiǎn)直是命根子!把土地讓給別人,簡(jiǎn)直是抹了自己的脖子!
有一個(gè)前蘇聯(lián)的笑話——
赫魯曉夫:我的農(nóng)民兄弟,你愛你偉大的國家嗎?
老農(nóng):“愛!”
赫魯曉夫:“假如你有一百畝田地,你會(huì)獻(xiàn)給國家嗎?”
老農(nóng):“給!”
赫魯曉夫:“假如你有豪華別墅,你會(huì)獻(xiàn)給國家嗎?”
老農(nóng):“給!”
赫魯曉夫:“假如你有一頭驢,你會(huì)獻(xiàn)給國家嗎?”
老農(nóng):“不給!”
赫魯曉夫:“為什么?”
老農(nóng):“因?yàn)槲艺嬗幸活^驢!”
空頭支票,誰都能開;愛國口號(hào),誰都會(huì)喊。但要貨真價(jià)實(shí)真金白銀地獻(xiàn)出來,那就難了,尤其是對(duì)所謂的“國家”不認(rèn)同的時(shí)候。智伯要韓康子把自己的土地拿出來獻(xiàn)給“國家”,拿自己的真金白銀,給自己根本不認(rèn)同的智伯所說的“國家”,韓康子同這個(gè)蘇聯(lián)老農(nóng)一樣,堅(jiān)定地回答:不給!
但是,韓康子的家臣段規(guī)卻勸他給。
段規(guī)也恨智伯,他和韓康子一起被智伯侮辱過。但他此時(shí)比韓康子冷靜。謀臣最重要素質(zhì)就是遇事冷靜,不沖動(dòng),不意氣用事。段規(guī)勸韓康子:“依我看,不能不給。智伯的為人,貪利、傲慢而自以為是。他來要地,我們不給,他一定會(huì)派大軍來,可惜我們又打不過他。所以,您還是答應(yīng)他,給他。”
你給他了,他就一定以為這個(gè)辦法好,會(huì)照此再向其他大夫要地。其他大夫總會(huì)有不聽從他的,碰到不聽他的,智伯一定會(huì)動(dòng)用武力。這樣,我們不僅可以免于禍患,還能靜待事變,窺測(cè)方向,以求一逞。”(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qǐng)地而弗與,則移兵于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qǐng)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變。)
韓康子一聽,好!馬上就派使者告訴智伯,送一個(gè)萬戶大邑給智伯,很爽快。
智伯很高興:不費(fèi)吹灰之力,就得到一個(gè)萬戶大邑,可見這個(gè)辦法好!馬上又照此辦理,向魏桓子要地。
魏桓子與韓康子一樣,第一反應(yīng)是:不給!
但魏桓子手下也有一個(gè)謀臣,叫趙葭,他對(duì)魏桓子說:“智伯向韓家要地,韓家給了,現(xiàn)在向我們要,我們不給,這就顯得我們自恃強(qiáng)大而激怒智伯了,智伯一定會(huì)加兵于我。不如給他。”
趙葭的主張,是弱者的思路。為了不招來更大的禍害,接受強(qiáng)加的損害。這樣的弱者,是沒有志向的弱者,是不會(huì)改變自己命運(yùn)的弱者。
但魏桓子手下,還有一個(gè)人,叫任章,這是個(gè)高人,他對(duì)魏桓子說:“智伯無緣無故向別人索要土地,臨近的國家會(huì)恐懼;挨個(gè)索要貪得無厭,天下會(huì)恐懼。讓天下恐懼的人會(huì)有好結(jié)果嗎?您就照他的要求,給他土地,他一定因此更加驕橫自負(fù)。他驕橫自負(fù)必然輕敵,鄰國則因懼怕他而團(tuán)結(jié)起來。一邊團(tuán)結(jié)一起,一邊輕敵傲慢,智氏的小命不長(zhǎng)了!《周書》上說:‘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所以,您給他土地,就是以此使他更加驕橫傲慢,就是把他推向滅亡。您怎么能為了一點(diǎn)土地,放棄為天下除掉智氏的偉大事業(yè)呢?”
魏桓子一聽,拍案叫絕:好主意!馬上也同韓國一樣,送給智伯一個(gè)一萬戶的大邑。(以上《韓非子·十過》,《戰(zhàn)國策·趙策一》《戰(zhàn)國策·魏策一》)
這個(gè)任章,比段規(guī)還陰險(xiǎn)。段規(guī)只是先自身免禍,然后靜待其變,而任章幾乎是主動(dòng)地、有意識(shí)地通過滿足智伯來把他推向毀滅。
他引用的“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我們?cè)诶献印兜赖陆?jīng)》里也讀到類似的句子,《老子》三十六章:
將欲歙(壓縮)之,必固張(擴(kuò)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qiáng)之;將欲廢之,必固興(扶植)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王弼注釋這幾句話很有意思:
將欲除強(qiáng)梁、去暴亂,當(dāng)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故曰“微明”。(樓宇烈《老子道德經(jīng)注校釋》)
王弼的這幾句話,簡(jiǎn)直就是對(duì)任章策略的哲學(xué)說明。任章通過送給智伯萬戶大邑,給智伯送終。任章就是要順應(yīng)、利用智伯自身的貪婪天性,讓他自取滅亡。
其實(shí),智伯曾經(jīng)利用仇由國君的貪婪滅掉了仇由——可見,老子所講的道理,智伯也是明白的,并且還活學(xué)活用取得成功過,為什么輪到自己就糊涂了呢?還是老子的話:“自見之謂明。”《韓非子·喻老》解釋道:“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
韓魏的做法從自身的角度來說,應(yīng)該是一個(gè)較好的策略。作為相對(duì)的弱者,在面對(duì)蠻橫無理的強(qiáng)大者壓迫時(shí),采取這樣的迂回戰(zhàn)略,在道德和方式上都無可指責(zé)。但是,他們的這個(gè)策略,有些自私,并且,有些冒險(xiǎn)。假如弱者都像他們一樣選擇,就不會(huì)出現(xiàn)他們預(yù)料的結(jié)果,反而強(qiáng)者愈加強(qiáng)大,弱者愈加弱小,下一輪的較量更無勝算之可能,結(jié)果就是惡性循環(huán),直至集體滅亡。
他們的希望,是出現(xiàn)一個(gè)拒絕智伯的人,這個(gè)人不出現(xiàn),就永遠(yuǎn)沒有希望;這個(gè)人一旦出現(xiàn),變數(shù)就出現(xiàn)了,變局也就出現(xiàn)了。幸運(yùn)的是,他們還真的看到了一個(gè)與他們做出不同選擇的人,這個(gè)人就是趙襄子。
當(dāng)智伯又“令人之趙請(qǐng)蔡、皋狼之地”時(shí),趙襄子鐵了心,不給。他派人對(duì)智伯說:我的土地是我的祖宗留下來的,哪里能隨便送給別人呢?語氣里透著狠勁。
趙襄子手下也有一個(gè)家臣,叫張孟談,張孟談在才智上毫不遜色于段規(guī)、任章。但是,張孟談并未勸趙襄子屈服,恰恰相反,他全力支持趙襄子直接正面對(duì)抗智伯。在韓魏都已經(jīng)屈服的情況下,他們這樣做,幾乎沒有外援,甚至,他們幾乎是與智伯和韓魏三家為敵。因此,無論如何,我們先要向這樣敢于直接挑戰(zhàn)強(qiáng)權(quán),而不是虛與周旋,面謾腹誹的人致敬。這個(gè)恃強(qiáng)凌弱的世界,就在他們出現(xiàn)的那一刻,勝負(fù)的天平,開始向弱者傾斜。
當(dāng)然,我這里并不想在智伯和三家之間分出是非正義,我只是對(duì)智伯的貪得無厭和恃強(qiáng)凌弱感到厭倦,希望看到他倒臺(tái)。
我想說的還有,我們很多解讀歷史的人,都喜歡用成敗論英雄。這還不算,他們還要告訴人們:決定成敗的,是權(quán)謀和手段。
這是極端糟糕的。因?yàn)椋谝唬麄冞@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歷史上固然有卑鄙小人一時(shí)得意,高尚君子常常倒霉的情況,但是,歷史自有它的公正:卑鄙小人常常在最后一敗涂地,而正義的一方最終被青史銘記。
第二,他們的這種說法敗壞了價(jià)值。他們這樣宣傳,讓人覺得,要想成功,就必須卑鄙。他們就這樣把人心教壞了。
我們就來看看智伯這樣的貪婪、無賴、毫不相信正義的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下場(chǎng)。
智伯一而再,再而三地耍無賴,他所依賴的,就是他的實(shí)力。因?yàn)橛袑?shí)力,人人都怕他,但是,現(xiàn)在,他碰到了趙襄子。趙襄子是他一路順暢快意無比戰(zhàn)無不勝的人生碰到的第一個(gè)釘子。問題是,就這第一次碰到的第一根釘子,就會(huì)釘死他,并把他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把他這樣的大人物,釘成一個(gè)大笑話,貽笑大方。
那么,處于絕對(duì)弱勢(shì)的趙襄子,為什么會(huì)做出迥異于韓魏的選擇,置自己于如此危險(xiǎn)的境地呢?難道他就不怕實(shí)力懸殊嗎?是什么樣的性格,讓他做出了這樣強(qiáng)悍而孤注一擲的決定?或者,他有什么特別的憑借?
我們知道,趙襄子也是以善于隱忍而出名的,他甚至自我標(biāo)榜,正是由于他能夠忍人所不能忍,才得到父親的賞識(shí),而得以立為太子,并繼承父親做了一家之長(zhǎng)。那么,這一次,他為什么不忍了?
答案是:他受夠了。他對(duì)智伯的忍耐,已經(jīng)到極限了。
如果說,智伯是來硬的,那么,趙襄子則是來橫的。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趙襄子現(xiàn)在也是不要命了——他要和智伯賭命。
智伯要地,從韓康子到魏桓子,一路凱歌高奏,勢(shì)如破竹,沒想到在最后碰了一個(gè)大釘子。此時(shí),貪財(cái)好利而崇尚權(quán)勢(shì)的智伯,無論是為了土地,還是為了自己的威風(fēng),也無法善罷甘休。文的不行,就來武的,他要武力討伐趙襄子。為了壯大聲威,也為了師出有名,還為了綁架韓魏,他拉來韓魏兩家,許諾滅了趙家后,三分其地。韓、魏仍然不敢拒絕,再說還有三分其地的誘惑。于是,三家合兵一處,浩浩蕩蕩殺奔而來。
順便提一下,這大夫之間的自相殘殺,晉國國君晉哀公絲毫不能干涉,他只能在一邊看熱鬧。我這話要讓他聽到,他一定會(huì)傷感地說:哥看的不是熱鬧,哥看的是鬧心。晉國,已不是他的晉國,他已然不是主人,而只是一個(gè)落寞看客。
智伯再加上韓魏,是絕對(duì)的優(yōu)勢(shì),趙襄子是絕對(duì)的弱者。
弱者要想戰(zhàn)勝強(qiáng)者,必須尋找同盟。張孟談建議趙襄子拿出財(cái)寶,賄賂諸侯,讓他們出兵干涉。趙襄子認(rèn)為沒有德行而求助于賄賂,行不通。
那就只剩下一個(gè)同盟。
這個(gè)同盟就是——時(shí)間。
有了時(shí)間,就能慢慢和他們耗。從退卻到相持,然后,耐心地等待時(shí)機(jī),伺機(jī)反攻。這是一場(chǎng)持久戰(zhàn)。
既然要打持久戰(zhàn),就必須尋找一個(gè)戰(zhàn)略上的立足點(diǎn),足以和對(duì)方耗下去。
去哪里呢?
趙家有三個(gè)可供選擇的邑。
第一是長(zhǎng)子邑(即今山西長(zhǎng)子縣)。優(yōu)點(diǎn)是:城墻堅(jiān)固完好,易守難攻。
但趙襄子否定了這一選擇。理由是:長(zhǎng)子城固然城墻堅(jiān)固完好,但那是用盡了當(dāng)?shù)乩习傩盏拿窳π蕹傻摹T?jīng)被逼拼命筑城,現(xiàn)在又要被逼拼死守城,誰會(huì)擁護(hù)我們?
這是一個(gè)政治家的判斷,知道民心才是真正的長(zhǎng)城。耗費(fèi)民心去修筑城墻,實(shí)際上是自毀長(zhǎng)城。長(zhǎng)子城有有形的城墻,卻沒有無形的城墻,不足守。
第二是邯鄲。邯鄲的優(yōu)點(diǎn)是倉庫充實(shí),糧草豐足。
趙襄子又否定了。理由是:倉庫豐實(shí),那是榨取民脂民膏的結(jié)果。老百姓已經(jīng)被榨干活路,現(xiàn)在又要投他們于死路,他們會(huì)幫助我們嗎?(《國語·晉語九》)
這又是一個(gè)政治家的判斷。趙襄子之所以能夠最后勝出,不是因?yàn)樗擒娛录遥且驗(yàn)樗钦渭摇?/p>
老實(shí)說,我讀史,讀趙襄子的故事,到這里,才對(duì)他有些敬意。
因?yàn)椋藭r(shí)的趙襄子,他知道他是什么東西,或者說,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東西。他知道,他不是老百姓的恩主,老百姓也沒有義務(wù)毫無保留地奉獻(xiàn)于他。他知道,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脾氣,并且,老百姓有權(quán)力發(fā)發(fā)脾氣,即使你剝奪老百姓發(fā)脾氣的權(quán)力,但上天會(huì)給老百姓發(fā)脾氣的機(jī)會(huì)。而老百姓一旦發(fā)了脾氣,后果很嚴(yán)重。所以,政治家首先是好好做人,不讓老百姓有脾氣;如果發(fā)現(xiàn)老百姓要發(fā)脾氣了,最好的辦法是:識(shí)相點(diǎn),自己滾遠(yuǎn)點(diǎn)。
作為手握大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你當(dāng)然可以玩弄百姓;但是,老百姓也可以不帶你玩——當(dāng)你倒霉的時(shí)候。
政治家與政客之區(qū)別,就在于政治家知道自己是什么東西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東西;而政客總覺得自己是一個(gè)什么了不起的東西。
趙襄子可能正是因?yàn)槎眠@些,才沒有走錯(cuò)關(guān)鍵的一步。
他最終選擇了去——晉陽。就是今天的太原。
為什么選擇晉陽呢?
當(dāng)初趙襄子的父親趙簡(jiǎn)子派尹鐸去治理晉陽。尹鐸臨行前,請(qǐng)示趙簡(jiǎn)子:“治理晉陽,你是要把晉陽當(dāng)成你的賦稅之源呢,還是要把它作為你趙家將來的屏障呢?”
行家一開口,便知有沒有。這個(gè)尹鐸,他一開口,你就知道他是一個(gè)人物,高瞻遠(yuǎn)矚。不僅我們知道,趙簡(jiǎn)子也知道。趙簡(jiǎn)子也許自己根本沒有想到這個(gè)問題,甚至他就是把晉陽當(dāng)做自己的賦稅之源。但是,尹鐸一問,他就意識(shí)到了這是一個(gè)問題,并且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趙簡(jiǎn)子說:“作為將來的屏障。”
和明白的人說話,真是不累。
明白人不是事事早就明白,而是他可能事先不明白,但你一開口,他就明白。
諸葛亮和劉備說話,不累。諸葛亮和劉禪說話,累。最后累死了。
趙簡(jiǎn)子是明白人,尹鐸便做明白事:他公開或半公開地減少晉陽城納稅的戶數(shù)和納稅的數(shù)目。
趙簡(jiǎn)子當(dāng)然明白他在造假。但他更明白他的目的。彼此都是明白人。
《大學(xué)》說,“財(cái)聚則民散,財(cái)散則民聚”,這樣簡(jiǎn)單的、明白的、永恒管用的政治智慧,也要明白的人,才能明白。
趙簡(jiǎn)子立趙襄子為繼承人后,告誡趙襄子說:“如果將來有難,你不要嫌棄尹鐸年輕,也不要嫌晉陽路遠(yuǎn),一定要把那里作為根據(jù)地。”(《國語·晉語九》)
因?yàn)椋挥羞@里,才有他趙家生死攸關(guān)的民心,尹鐸用散財(cái)?shù)姆绞骄蹟n的人心。
此時(shí),趙襄子想起了父親的話,決定去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