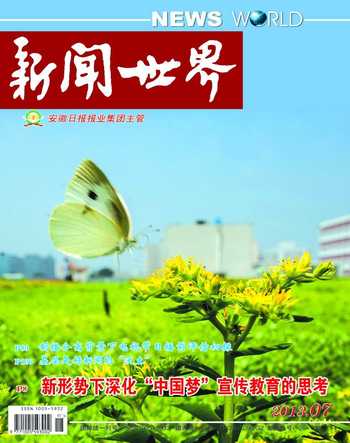央視《看見》欄目解析
趙璟一 鄭晨醒
【摘 要】《看見》作為一檔由紀實和人物訪談構成的專題節目,因其有態度、有溫度、有深度的風格引發了人們的關注。本文以《看見》欄目的周末版為例,從欄目定位、敘事結構、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等角度出發解析其欄目特征。
【關鍵詞】《看見》 敘事風格 人文情懷
《看見》作為一檔記錄現實的專題節目,它用鏡頭向我們描述劇烈變化的現實生活,刻畫新聞背后的人,感知世間的人情冷暖,了解世界,認識彼此,審視自我。
《看見》日播版開播于2010年12月6日,周末版于2011年8月7日開播。伴隨著欄目的發展,日播版漸漸淡出人們視野,并于2012年2月18日停播,形成了周播版的固定形式。《看見》以“看見新聞中的人,尋找生活中的你我”為宣傳語。它分為兩個單元:人物訪談和記錄風格的故事。人物訪談注重對新聞人物心靈世界的追尋和探問。記錄風格的故事不僅關注新聞事件本身,而且關注事件背后的人物。本文將以《看見》的周末版為例,從選題、敘事結構、人文主義情懷等角度出發解析其欄目特征。
一、呈現新聞中的人
《看見》以人為中心,以人為尺度。它讓我們看到新聞事件中的人,在矛盾中既掙扎而又堅持的人,處于選擇中的人。《看見》對人的關注延伸到了對生活的關注,對社會的關注,對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的關注。
尋找個體的普遍性,將個人的體驗感受與時代的變遷結合起來,呈現激流中國的景象。《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拆遷》講的是廣東楊萁村少數留守戶與大多數搬遷戶歷時兩年的對峙,挖溝,斷水,鄉鄰之間矛盾重重。這中間我們不能武斷地說誰是誰非,但是呈現的是拆遷過程中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權利博弈。《刻章救妻背后》講述的是模范丈夫廖丹為了挽救患尿毒癥妻子的生命,假刻醫院公章的故事。從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對苦難夫妻之間相扶相持,中國看病難的問題,社會的溫情愛意以及法理與情共謀。從人的角度挖掘并對事件進行深度解讀,以波瀾不驚的情感打動觀眾,反映當下時代紛繁蕪雜的現實。《看見》是一面反映當下中國現實的多棱鏡。
以一種有溫度的目光去呈現人性。“所有被稱為偉大的故事,都來自偉大的創意,幾乎所有偉大的故事創意中,都有一種人性的展示。”①《告別盧安克》向我們呈現的是德國志愿者盧安克將要離開支教了三年的廣西深山板烈的故事。通過這期節目,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也看了一個至善至真的盧安克,一個面臨追尋自由、堅守理想和承擔家庭責任兩難選擇的盧安克。《旁觀者周星馳》從作為政協委員的周星馳;被外界質疑的周星馳;作為電影導演的周星馳;童年憧憬武俠夢的周星馳;對愛性、感性理解的周星馳五個方面向我們展示一個立體而有血有肉的周星馳,一個接近于現實的周星馳。好的采訪是理解對方,是心靈的交流。在這期節目的結尾部分就體現了這種交流。
柴靜:我可不可以理解說這是一個不由分說的想法,我就想在這個時候說出我一生中想說的這句話。
周星馳:對對對,你有這樣感覺嗎?
柴靜:對。
周星馳:謝謝你,謝謝你。
這是一場心靈對心靈的對話,是一場深入人的精神肌理和心靈角落的對話。將新聞人物心靈探尋作為串聯每個故事的主要支撐點。正如柴靜所說,《看見》也可以看作一個文學節目,文學可能是一種閱讀的態度吧,就是對人靈魂過程的呈現,不輕易做出褒貶或者評判。②
二、邏輯板塊式的敘事結構
電視新聞作品需要通過自成體系的語言符號的一系列有機的組合,才能形成傳達意義的敘事文本,才能被觀眾所解讀。彼得·布魯克斯說:“敘事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口頭或者行動的講述,它通常是復雜的、多層次和持續的”。
“同一事件,不同的視角,不同的介入方式,不同的素材組合,都會影響內容的傳達。”③因此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在今天越來越重要。敘事結構可以增加節目的深度,形成張力。不同的結構方式往往是一個節目風格的表現。
約翰·艾利斯認為電視敘事通過片段,也即通過相對自立門戶、彼此不相銜接的一個個場景來完成的,“從一個片段到下一個片段的運動是一種交替而不是連續”。于是所有的電視敘事都是系列的而不是線性的。④ 《看見》欄目往往采取邏輯板塊式的結構來講述故事。
邏輯板塊式是一種類似于議論文的電視新聞形式,每一個板塊一個中心,板塊與板塊之間有邏輯關系,但是這種邏輯關系不是線性的,沒有時間做承載,而只是為了說明問題,得出結論。⑤邏輯板塊式的結構使得整體節目的結構清晰,每一個板塊看似獨立,卻為共同的中心服務。《看見》的節目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2011年8月14日播出的《專訪藥家鑫案雙方父母》。節目分為6個部分。
第一部分 敘述事情經過,引出話題
敘述藥家鑫案的梗概,以及藥家鑫已經被判死刑,死者張妙也入土為安。
紀實張妙家庭的現狀,采訪張妙父親張平選對結果高興但也同情藥家鑫父母。
藥家鑫父親藥慶衛開微博向死者道歉。紀實藥家現狀和藥家鑫的遺物。
第二部分 反思藥家鑫教育過程,分析其性格成因
藥家鑫父母講述:對藥家鑫教育要求太嚴格、太嚴厲、要求盡善盡美。
藥家鑫自述:小時候練琴被父親嚴打,患網癮被關地下室,曾特別壓抑,想過自殺。
第三部分 藥家鑫極度自卑,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
青春期開始后,從沒照過相;四個月內剪掉60斤肉;大學期間瘋狂帶家教;苛求完美,要干大事。
第四部分 案件真相,解釋疑團
為何在父母的陪伴下自首?起初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為何動刀原因?害怕,慌,農村人難纏。
藥家鑫是富二代?介紹其父母的工作,身份,經濟條件
為什么不早點說出真相? 再多解釋也無濟于事,沒想那么多
第五部分 繼續反思藥家鑫的教育問題
父親拒絕藥家鑫臨刑前捐獻眼角膜的要求。
父親對藥家鑫說話偏激 希望他人以此為戒
第六部分 兩個家庭的和解與寬諒
張平選 希望藥家鑫父母寬心,退回藥家20萬元的賠償費
藥慶衛 承諾幫助照顧張妙的父親和孩子
這六部分的關系看似沒有那么的嚴密,但是完整清晰地解釋了藥家鑫殺人案背后的種種為人不知的事情。邏輯板塊式的敘事結構突破了線性敘事結構的單一性,將藥家鑫之死與網絡輿論對藥家鑫的批判作為采訪點,不僅探究了藥家鑫殺人的原因,也展現了雙方父母對這場悲劇的反思與后悔,更是將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大愛呈現出來。
三、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理念
《看見》欄目在當下浮躁的社會環境下,堅守著專業主義的新聞理念。《看見》不同于《新聞調查》這類調查性報道節目以輿論監督為首要任務。《看見》的突出訴求并不在于輿論監督,而在于引導輿論、揭示人性、尋求化解,其公共服務特色更加明顯,是一種介于政治訴求和經濟訴求之間的社會訴求。
《看見》打破了二元對立式思考模式,引領觀眾看見灰色地帶。節目總是先放下強烈的是非觀,去呈現復雜的事實和人。二元對立滲透在我們世界觀中,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現實生活中,貧富的二元對立,城鄉二元對立,官與民的二元對立,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善與惡的二元對立,美與丑的二元對立。我們常常善于將人和事件標簽化,單一化,兩極對立化。我們常常以一種簡單粗暴的思維模式來看待事件和人。
《看見》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看待事物的思維模式,以寬容的態度,放下成見、偏見去看待問題,給雙方以發言表達的機會。也正是由于此,《看見》成為一個多元的意見空間,使對立雙方溝通,甚至是和解。
在當下這個新聞娛樂化,搏出位、博眼球的媒介環境中,道德力量、輿論的力量常常綁架新聞事實。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往往由于我們的偏見、成見使現實被遮蔽。2011年11月6日的節目《熊之辯》在這期節目播出之前,社會各界圍繞著活熊取膽的話題展開了廣泛的爭論,而歸真堂的創始人邱淑華一句:“反對我,就是反對國家”,將話題引爆。但是此前媒體的討論呈現出一邊倒的傾向,集體聲討歸真堂活熊取膽的行為。《熊之辯》這期節目給了邱淑華一個發言表達的機會,讓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整個事件。在這場事件中沖突的雙方歸真堂創始人邱淑華和動物保護組織代表張小海,雙方都有了發言的機會,努力使報道達到平衡的狀態。《城管來了》這期節目中講述了大家觀念中強勢蠻橫的群體——城管。以大學生城管小宋為中心,向我們展示了城管人與小攤販的生活糾葛。這個片子中我們看到了微薄的工資、工作過程中隨時可能出現危險、相親時被姑娘嘲笑的城管,為看眼病在北京街頭賣爆米花的大爺,賣雞蛋灌餅的小販這些以小攤為生計的人們。我們也看到了城管在執法過程中的無奈與溫情。我們看到了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面臨的矛盾沖突。正如片子結尾評論:“一個社會,事件的哪一方都有說話的機會,都說對方能聽懂的話,也都有誠意去聽對方的話,把意見和矛盾一一陳述,也許在說清楚事實的時候,事情的化解之道也就隨之呈現。”
《看見》,看見復雜,看見多元才能避免偏頗。
《看見》在群像中模糊身影,將臉譜化的個人還原為個性化,豐滿化的生命個體。它踐行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幫助我們努力看清這個復雜的世界。
參考文獻
①[美]威廉·E·布隆代爾:《〈華爾街日報〉是如何講故事的》,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213
②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與央視欄目聯合舉辦研討會,http://media.sohu.com/20120507/n342523108.shtml
③朱羽君、崔林,《電視新聞調查節目的文本結構》,《現代傳播》,2004(6)
④汪振城:《當代西方電視批評理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 :75
⑤曾敏祥:《電視新聞學》,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71
⑥馬俊,《〈看見〉:自媒體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電視研究》,2012(5)
(作者:均為華中師范大學信息與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新聞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