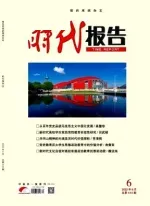周恩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張景山
青年·夢
少年周恩來曾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偉大理想。在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期間,周恩來帶著熾熱的愛國之情從日本留學歸來,投身運動;遂又帶著深沉的愛國之情赴歐勤工儉學,再次尋求救國救民之道。
周恩來用畢生精力實現報國之志,終成一代偉人。
周恩來,生于1898年,1913年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并組織進步學生團體覺悟社。
1920年,他遠赴歐洲,在法國、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學生與工人中宣傳馬列主義。192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并參加中共旅歐支部領導工作,對早期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少年老成
周恩來,生于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他的祖父是紹興讀書人,紹興師爺名聲在外,淮安周家就是由紹興遷徙而來的。
他出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去世。因為祖父生前不事生產,到了周父這一輩,只能靠房產和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日漸拮據。父母為周恩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取乳名為“大鸞”,大鸞是傳說中的一種神鳥,只要大鸞現身,天下便會安寧。在周恩來不滿一周歲時,叔父病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叔父如果沒有子嗣就死去是無顏見祖先的,牌位也不能上祭壇。為了“沖喜消災”,周恩來被過繼給叔父。
從4歲開始,周恩來跟隨叔母識字和背誦唐詩,5歲入私塾讀書。叔母出身于書香門第,擅詩文書畫,略懂醫理。她常給周恩來講神話故事和一些唱詞。6歲那年,周恩來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難免有磕磕碰碰,雖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但是周恩來的生母憑借自己的精明能干,總能公道地解決糾紛。周恩來常跟隨生母去解決糾紛,耳聞目睹了母親的辦事公道,并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在私塾一邊念書,一邊大量地讀小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徜徉。“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后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正當他有意識地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時,兩個母親相繼去世,父親和伯父長年在外謀生,一位叔父偏癱﹑一位叔父早逝。身為長子長孫的周恩來不得不帶著兩個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過早地用稚嫩的雙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為了養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強裝笑臉靠典當借債主持家事,養成了少年老成的穩重性格。
1910年春,12歲的周恩來隨伯父到東北求學,轉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學堂。此時正是形成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重要時期,他告別了私塾生活,進入新式小學堂,對一切都充滿好奇。那些新鮮有趣的課程,諸如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音樂、美術和體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窺探世界的心。這一年,國內時局風云變幻,處在破舊立新的關鍵時刻。周恩來在老師的影響下堅持讀書看報,及時了解國家大事。“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
辛亥革命爆發后,周恩來帶頭剪去辮子,并接觸進步書籍。他讀光復會領袖章太炎的書和同盟會的雜志,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無論是章太炎難懂的古體文,還是梁啟超的近體文,周恩來都認真閱讀。雖然進步刊物的思想側重各有不同,但樸素愛國的道理是一脈相承的。周恩來的眼界隨著閱讀拓寬,思想得到升華,對事物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當其他同學還從未想過為什么要念書時,周恩來已經明確地提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學生運動的主要組織者
由于伯父工作調動,周恩來于1913年隨之遷往天津,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開中學。南開中學是一所仿照歐美方式開辦的私立學校,由嚴修創辦,張伯苓擔任校長。周恩來的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周恩來十分珍惜學習機會,他為自己制訂了五個“不虛度”的要求:讀書不虛度,學業不虛度,習師不虛度,交友不虛度,光陰不虛度。“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來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他的作文曾被評為全校第一名,得到“用筆遒勁,布局綿密”的評語。
因為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的便利條件,周恩來參加組織“敬業樂群會”,取“敬重學業,聯絡感情”之意。他主編《敬業》會刊、《校風》周刊,發表小說和時事評論性文章。周恩來活躍在校園內外:他參加新劇團,扮演女角登臺演出;參加學校演講會、江浙同學會并分別當選為副會長和會長。1915年,周恩來參加了反袁運動,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他組織同學演講、募捐,在“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還不多”的情況下,青年周恩來已經顯示出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
南開中學畢業后,周恩來認為自己應該繼續深造,他籌劃考官費留學生。既是官費,求學費用可暫不考慮。而伯父早已無力負擔學費,又去哪里籌措遠渡重洋的旅費呢?幸好愛交朋友的周恩來為人誠實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費。“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臨別時刻,他給同學贈言說:“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
早在國內,周恩來就了解到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國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來想要實地了解日本的發展情況,探究“中國是否可以實行日本的社會模式”的問題。周恩來看到日本燈紅酒綠的的城市風光,也更多地看到無業大軍呆滯的目光。他漸漸否定了強權救國的想法。周恩來不喜歡條條框框的東西,枯燥的日語學習是件令他頭疼的事。周恩來在沮喪中猛然發現一直未受自己重視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載著一篇篇充滿激情和正義的文章,它們排山倒海般震蕩著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開朗。周恩來手不釋卷,“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正當周恩來準備應考之際,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他在報紙上看到宣傳介紹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漸接觸并研究馬克思主義,先后閱讀過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堺利彥創辦的《新社會》等雜志。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和由他出版的個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深深吸引著周恩來,他的思想開始向馬克思主義傾斜。1919年,《凡爾賽條約》的簽訂最終促使周恩來放棄在日本的學業回到祖國。
中國愛國學生發起了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由北京迅速擴展至全國,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積極參加了天津學生組織的示威游行。為把運動引向深入,他搬進南開校園,和學生運動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團結一致,還以南開大學校友身份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建立起天津學聯自己的輿論宣傳陣地。周恩來在報上發表文章大聲疾呼 :“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地來了!我們要有準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受學生歡迎,學聯會長馬峻稱贊說:“你的社論真鼓舞人心,這比只站在人群前面大喊一陣有用得多。”
為支援山東人民的愛國斗爭,周恩來與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總統府門前示威,他負責后勤供應和宣傳。反動軍閥強行逮捕了天津學生代表,激起更大規模的學生反抗。經過露宿請愿,代表終于被釋放。在勝利返津途中,周恩來、鄧穎超、諶志篤、馬駿等學生提議組成一個更加嚴密獨立的團體——覺悟社,以便領導天津學生進行愛國運動。周恩來提議出版不定期小冊子《覺悟》,并起草了《覺悟宣言》。周恩來是覺悟社的中堅力量。
“五四”時期,周恩來已經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周恩來自己曾說 :“我從事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后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