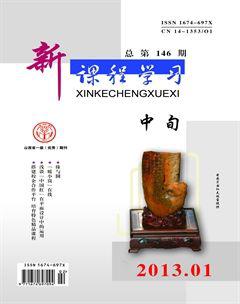傾聽靈魂之歌
何春
題記:傾聽沉默就是傾聽靈魂之歌
近來在教學生品讀屈原的《離騷》的時候,突然領悟到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美德即智慧。”一個人如果經常心系民族命運和人生問題,對于世俗的利益就會超脫未然,那么那些所謂的傷天害理之事一定與之無關。說到底,道德的敗壞是一種蒙昧,當然,這與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識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我很欣賞周國平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更接近人性。“假、惡、丑從何而來?人為何會虛偽、兇惡、丑陋?我只找到一個答案:因為貪念。”人為何會有貪念?佛教對此有個很明確的答案:因為“無明”。通俗地說,就是沒有智慧,對人生缺乏透徹的認識。所以,真正決定道德素養的是人生智慧而非意識形態。人性本然,怨不得己。你只能改變形態,卻改變不了本質。
記得魯迅先生有一首名叫《自嘲》的詩:“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人們往往只記住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句被毛澤東所歌頌的名句,卻經常忘記了魯迅的人生經歷與痛苦經驗。
其實這首詩中最關鍵的是第一句“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試想一下,一個懷著滿腔愛國熱情的文人還沒有凸顯自己的治世才能就被這個萬惡的、腐敗的政府痛擊得死去活來,他怎么能忍下這口惡氣,當然會寫下:“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才是一個真實的魯迅。但是這樣的靈魂叩問,沒有經歷過苦痛的人是無法理解的,準確地說這樣的靈魂叩問太過犀利、太過窒息,讓人無法喘息。但也讓人刻骨銘心,鞭笞靈魂,讓麻木的中國人丑態畢露無所遁形,直至慘淡的面對,不得不變化。
在讀到蘇聯解體是因為“和平演變”時,我覺得西方人的智慧不僅僅是改變一個社會體系的問題,而是西方的哲學家、上位者看到了一個社會的本質問題,即人性的腐敗、道德的淪喪才是導致這個體系改變的根本原因。舉個例子來說:“一個自己有人格尊嚴的人,必定懂得尊重一切有尊嚴的人格。同樣,如果你侮辱了一個人,就等于侮辱了一切人,也侮辱了你自己。”西方是非常講究人權的,其實說白了這就是上位者對人性的一種把握,讓人人都感覺到被需要、被尊重。這也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核心體現。那么這個社會、這個體系就會永遠地被人性所保護,這就是他們道德規則。
一個社會也好,一個體系也好,都會存在不同差異的人性,但是作為一個掌握人性的“上帝”就必須制定“規則”,讓所有的人站在“人性的法則”面前,為自己的貪欲、罪惡、詆毀、謾罵、暴力付出良知的譴責。這是一種“軟制度”而非道德。
而做到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失勢,即站在人性法則的天平
上,做錯事的人要接受道德的審判而非“變相嘉獎”;維護正義的人要受到尊重而非冷漠置之。
正確的主導權力的方向,就是主導一個社會、一個集體的輿論導向,也是一切良性循環的開始。
曾經在公園看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畫面:一個幼兒摔倒在地,自己爬起來。他突然看見媽媽,就重新擺出摔倒的姿態,放聲
大哭。
我們成年人何嘗不是如此,試想種種強烈的情緒,憤怒或者痛苦的姿態如果沒有觀眾在場,其中你有多少能堅持下去呢?
可見,犯錯的固然可怕,但如果沒有圍觀(勢),放棄了姿態還怎么能惺惺作態!
當然,輿論是最不留情的,同時又是最容易受愚弄的,于是有人被輿論殺死,又有的人靠輿論獲利,何去何從難道不是取決于名人的裁判?人人都說要活出個樣兒來。我說,得活出個味兒來。名聲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對人對己都不必衣帽取人。衣服換來換去,我還是我。當鉛華褪盡,你還是如初生嬰兒般悄然離去。人要活出個味兒來,不然梭梭光陰,你豈不是上帝的棄兒,時間的笑話。
在各色領袖中,三等人物恪守民主,顯得平庸;二等人物厭惡民主,有強大的個人意志和自信心;一等人物超越民主,有一種大智慧和大寬容。因為他們會傾聽沉默,傾聽靈魂之歌!
智者的沉默是一口很深的源泉,從中汲取出的語言之水雖然很少,但是滴滴晶瑩,必含很濃的智慧。
(作者單位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第二十九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