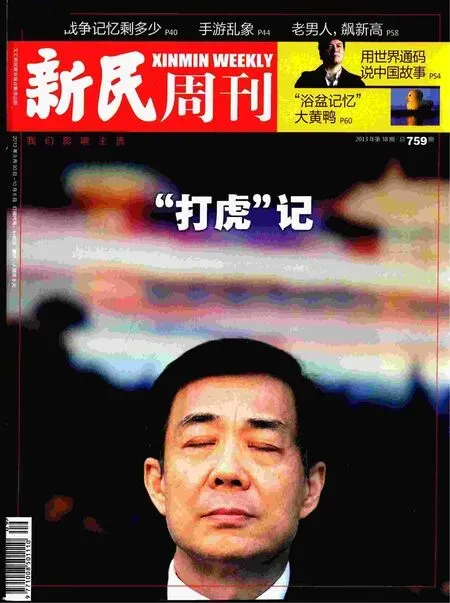世界永遠年輕
孟暉
霍布斯鮑姆在其《極端的年代》中這樣評判上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對我們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過《圣經》為我們命定的七十壽數的時代生還者而言,這是唯一一件至今動機依然純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標。當年如此,今日回顧依然如此。”
然而,在我這一代人的經驗中,通過文藝,通過海明威、洛爾加、聶魯達、奧登們的偶像化, 那一場正義之戰卻日益變成了浪漫事件。形形色色的文藝作品中,國際志愿者慷慨奔赴西班牙捍衛民主與共和的義舉,越來越像一群不靠譜的文藝青年逃避現實、找尋自我的任性行為,仿佛與窮游世界也沒什么區別。倪慧如、鄒寧遠《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卻展示了更為真切的事實:當年來自53個國家的4萬多志士當中,不僅有歐美文化精英,也有工人、農民、海員、廚師,包括作為華工前往法國謀生、不識字的中國人劉景田,以及有著同樣華工經歷的張瑞書、閻家治。
倪慧如、鄒寧遠是由臺灣到美國生活和工作的華人科學家,1988年,這一對夫婦偶然發現,昔日為民主西班牙而戰的“國際縱隊”里依稀似有中國人的身影,從此開始執著追索一段塵封的往事。多虧這兩個有心人的堅持,如此值得我們驕傲的功業才得以重現在陽光之下:當初,自愿奔赴西班牙參戰的中國人竟然多達數十人甚至可能近百人,“臨近西班牙純潔的前額,沉默堅定,如黎明前的鐘”,保衛“受圍攻的自由”(聶魯達《國際軍團到馬德里來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年輕的陳文饒一樣,犧牲并長眠在美麗而陌生的土地。盡管這般無私的獻身曾長久被同胞遺忘,但其實早已獲得海明威至誠的禮贊:“沒有人比在西班牙陣亡的人還要光榮地入土,這些光榮入土的人士,已完成人類的不朽。”
幾年前,我曾經在西班牙《世界報》上偶然讀到一篇夢魘般的文章,說巴塞羅那市準備將一條大街逐段翻開,尋找洛爾加的尸骨,因為很多人相信這位詩人一直就被埋壓在那條街的街面之下。但也沒有見到后續的報道,看來翻找并無結果。在西班牙人那里,佛朗哥及其獨裁統治始終是處于清算過程中的黑暗噩夢。對此,今天的中國人當然很難感同身受,畢竟“那是一個陌生國家的戰爭”、“一個陌生國度的苦難”。《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卻告訴讀者,所謂的“西班牙內戰”并不是什么“兄弟鬩于墻”的紛爭,相反,乃是反動勢力對民主制度的圍剿,是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土地上第一次展露其獠牙,因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場序幕。尤其是,當西班牙在炮火中不屈抗爭的同時,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全面爆發,相隔萬里的兩個戰場,其實屬于同一場戰爭,屬于全人類范圍內壓迫與反抗壓迫的同一場殊死大搏斗。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白求恩等多位曾經在西班牙救死扶傷的醫生隨即趕赴中國,在抗戰前線舍生忘死。這些洋醫生來自不同國家,包括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因為相同的經歷,在當時被中國人賦予了一個特殊的統稱——“西班牙醫生”。我們自能感念這些醫生對于中國的恩惠,那么又怎會不理解他們對西班牙人的意義?
讓我感佩不已的是,2011年6月,書的作者之一鄒寧遠參與了“國際自由船隊”的行動。“國際自由船隊”是美國、西班牙、加拿大等20多國的仁人志士組成的一支船隊,試圖沖破以色列對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鎖,其中最高齡的一位成員是“二戰”時進過納粹集中營的86歲猶太老人。這一義舉展開時,我曾通過一位西班牙議員的博客了解事情的進展,當時卻沒想到,還有華人同胞參與其中。
市儈也許會嘲笑這些努力都是無謂。但正如加繆就西班牙內戰所發出的宏音:“除非全人類獲得自由,否則沒有人是自由的。這種民主才是唯一值得我們為它犧牲的民主。”
只要為人類自由的抗爭存在,世界就永遠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