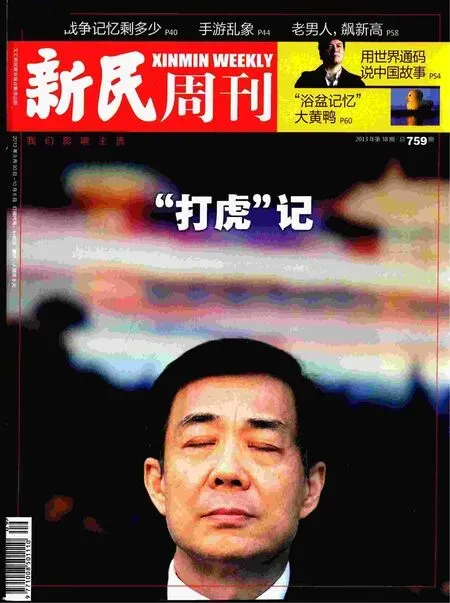自由、永恒與兵營
瘦竹
讀完美國作家詹姆斯·瓊斯的《從這里到永恒》之后,我猜想,如果海明威或者普魯斯特是它的讀者又會怎樣?我想海明威一定會覺得它太啰嗦,而普魯斯特又覺得它不夠啰嗦。《從這里到永恒》厚厚800多頁、洋洋灑灑近80萬言之巨,卻沒有像前面兩位大師那樣搞點什么文本實驗,在20世紀各種文學實驗風起云涌之際,倒顯得有些另類。
與《從這里到永恒》可以相提并論的反映美國軍營生活的小說包括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但評論家查爾斯·羅洛卻對《從這里到永恒》情有獨鐘,他這樣評價說:“迄今還沒有一位小說家如此詳盡透徹地記敘軍隊生活,也沒有一位小說家如此忠實地記錄下士兵的談話,讓我們讀到原汗原味的士兵語言。”《從這里到永恒》反映的自然遠不止于這些。
《從這里到永恒》從主人公普魯伊特從軍號班調至步兵七連開始,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普魯伊特被意外擊斃結束,通過短短幾個月發生在普魯伊特以及他所在的七連的一系列事件描繪了一幅美國軍隊和平時期生活的全景畫,在這幅全景畫里的美國大兵眾生相與好萊塢大片里的美國大兵形象大相徑庭。在《從這里到永恒》里我們看不到美國精神、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等好萊塢大片里宣傳的所謂美國主旋律,我們看到的只是陷入困境的美國大兵,看到他們的墮落生活,等級森嚴,以及那些為了自由而付出慘重代價的年輕生命。
在《第二十二條軍規》里有這樣一個悖論:“如果你能證明自己發瘋,那說明你沒有瘋。”在《從這里到永恒》里,也有一個類似的悖論。
在軍人監獄,頗有些彌賽亞意味的杰克·麥洛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公民們,在這個世界上要獲得自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為自由而死,可是死了以后自由對他一無用處,這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
面對美國軍營的自由困境,《從這里到永恒》里的幾個主要人物選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先知式的杰克·麥洛伊選擇了逃跑,普魯伊特選擇了反抗,軍士長沃爾登選擇了妥協,因為他們不同的選擇,他們的結局也大不相同。杰克·麥洛伊逃出軍人監獄之后等待他的是飄忽不定的命運。普魯伊特因為自己的反抗,導致了他身上的一連串不幸事件的發生,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他最后并沒有死于反抗而是死于返回連隊的途中,他反抗森嚴的等級制度,卻無比熱愛軍隊,這是他的困境所在,他的死也可以說死得其所。沃爾登選擇了妥協,但他也不是沒代價的,那就是他永遠不可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在一起。
其實《從這里到永恒》只要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會邁入整個人類的自由困境中而不只是軍營。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曾有一句這樣的臺詞:“這些高墻還真是有點意思,一開始你恨它,然后你會對它習慣,等相當長的時間過去,你還會依賴它。”類似的意思在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的《巢》中也可以看到,幾位東歐知識分子在擺脫了極權體制逃到美國之后,陷入了迷茫之中,他們發出了這樣的疑問:“自由到底是迷宮的出口,還是迷宮本身的延伸?”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從這里到永恒》的主人公普魯伊特是真正的大徹大悟者,也許只有他看到人類無論如何突不出自由的困境,所以即使在他痛不欲生、瀕臨絕境之際都沒有想過逃跑。
既然他們突不出自由的困境,也許性、愛情、女人可以為他們提供暫時的出口,但即使在愛情上,其實他們也是迷惑的,而女人們,無論是艾瑪還是卡倫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評論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的《跳房子》時,我曾這樣寫道:“當男人們淹沒在形而上的河流里,當男人們因為深深地陷入絕望而瘋、而死的時候,她們正在形而上的上空輕盈地飛翔,奧利維拉們盡可以對她的無知進行嘲笑,但她們劃過天空的翅膀勝過他們任何深沉的思考。 ”這些話用在普魯伊特們與艾瑪們的對比上也是合適的。
其實對于這些士兵們來說,多年以后,當他們回憶起自己的軍營生活,那深深地印在他們記憶里的,正是那些痛苦的或者快樂的每一瞬間,正如《超期服役布魯斯》的歌詞里寫下的他們軍營生活的點點滴滴,正如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所寫下的那句話:瞬間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