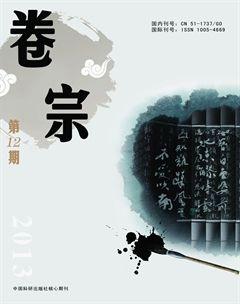儒法之思
敖苒?鄧君韜
摘 要:以賀麟著作為主線,圍繞其思想中對儒家、法家的闡述,兼及人治、法治、德治探討與法治類型說等諸多議題,進而嘗試挖掘出賀麟儒法思想中對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有意義的本土智識資源。
關鍵詞:賀麟;儒法思想;法治建設
基金項目:本文獲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宜賓學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2012年度項目(SXJZX2012-009)資助。
1 引言
賀麟先生從封建王朝的末端走來,見證了動蕩中的神州大地,尋出了依仗于這片黃色土地最堅實最綿延的物件——思想。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飽受宋明理學文化浸淫的賀麟又毅然邁出國門汲取西方文化精華。在這樣的游學背景下再次回到祖國,開始了漫長的中西文化匯集之路。作為“新心學”的創始人,賀麟在發揚儒學文化的同時,將儒學的理念寄存于法學,這兩類學術傳統的交匯貫通給后人留下諸多啟示。
概覽賀麟諸多論著,大部分都提及并盛贊其致力于儒法結合的智識貢獻。在探索中國法治的路途中,他的貢獻便成為重要一環。在愈加倡導國學文化、挖掘法治本土資源的當下,將賀麟的理論考據再次梳理,以求明晰國學與律法的關聯傳承,或可為當下法治建設提供點滴貢獻。
2 儒法之匯
2.1 歷史上的儒法交匯
受傳統巫覡的影響,帝王之身借鬼神之名得以實現在思想上統治臣民的目的,而儒學的源起便在這樣的巫覡文化之中。《漢書·藝文志》及劉向《七略》均認為儒“出于司徒之官”,而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則以儒為術士之稱,“儒”實與初民社會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動有關。孔孟傳承下的禮制思想風氣,使得儒與法作為治理群體秩序的規則,二者便結下了不解之緣。
自三代始,法便寓于禮,國家通行“禮治”。儒和法在歷史中默契存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真正建立,儒法兩家自此開始了德教與刑罰、變法革新與王道政治、法治與禮治等長達五百年的論爭。至秦朝,法家傲立于世、獨占鰲頭;直到漢以后,儒法對立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儒家思想再次勃興,融入并統帥了律法之治,“唯法獨尊”的法家走向末路;儒法融合演進逐步形成了我國“德主刑輔”的古代治理模式。
2.2 當代的儒法貫融
儒法兩者締結起中國傳統思想的主要脈絡。各大學者對儒法之間的關系及對當代中國的理論價值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李澤厚先生曾在訪談中表示支持新法家的觀點,即可以用新一輪“儒法互用”來統合西方的三權分立(可加上“輿論”這第四權),可以包容司法獨立等原理、體制——這種結合了中國傳統并轉換性創造的新形式,不同于牟宗三從“道德形上學”開出民主、自由或蔣慶的“公羊學”。
李錦全認為儒法因其儒學的包容性,故而禮法應是互補,其互補的結合點在于禮法相通,刑德并用。他認為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其產生背景都在于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下,源于鄉土中國的血緣關系,其目的應該是一致的,只是在手段和方式上有所不同,最終都會殊途同歸。“總得來說,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形成,固然是以儒學為主體的綱常名教、道德倫理不斷豐富、完善、發展的歷史,但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思想不可能完全實行自我封閉,它不得不接受各家思想的沖擊, 從矛盾中取得融合,或是進行互補工作。”李錦全以儒學為基本,探尋的是法律所本源的東西,中國不同于羅馬等國法律源于市民階級的城邦革命。雖然中國與羅馬等眾多的古國一樣有著悠遠的神話傳說和神靈信仰,但是因為中西文化的差異,中國本著“仁”的傳統理念尋思著治理民眾的方式。儒學的強制力畢竟僅僅源于內心道德,在客觀上難以起到規制人的顯現行為,所以在嚴君之下,律法的產生也為社會秩序的完善埋下深根。
徐忠明認為法律指導著思想中的禮法觀念,并且禮法融于法律之中。戰國末期的荀子提出“以禮釋法”替代了孔孟所倡導的“以人釋禮”,并且在李錦全教授研究的禮法同歸的思想指導下延伸出無論是禮教還是法治都在于建立一個“有道德的社會”。從儒法相爭演變為儒法相容,可從《唐律疏議》中窺探法律融入儒學的現實狀況:《唐律疏議》的“八議”到“七出三不去”再到“不孝”為罪都體現著法律源于最本真的人性道德,即為儒之精藝所在。此外從唐代的“按喪服制”以及“乘輿服御”等規定可以得出“以禮釋法”的結論,古代的律例循著倫理道德的影響,無論是在法治還是在人治的征途中都貫通著儒法互釋。
在諸多學者討論儒與法的問題上均出現一個共通的問題,即或停留在古代的文化環境中或滯留在純學術的氛圍之中。在儒與法的討論之間,很少有學者像賀麟一樣提出具體如何讓儒和法在現今社會中予以結合的解決路徑。
3 賀麟的儒法思考
學者們多以賀麟“新心學”思想為基點,研究他所提倡的以西方的哲學發揮儒家的理學,以“學治”來補充儒家的理學,在延續中華儒家傳統思想的同時,以思索人治與法治的特征關系為宏線來研究法治的內核、類型和價值等主題。
3.1 法治與“三個主義”
1.法治與禮治
儒家“禮治”主義是以尊卑宗族為核心的制度,并形成一定的秩序來規范社會。賀麟先生認為“法律乃正是發展人性、保障公民自由的一種具體機構,且是維持公共生活和社會秩序的客觀規律。”法治同禮治都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有相同的歷史產生背景和共同的設定目的。
“禮治”的建立存在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土地私有化集權性的王權社會,其產生的緣由本就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生成“親親”和“君君”兩大原則。在賀麟看來“要求新的工業文明在中國生根,在中國本土內發榮滋長,決不是沒有絲毫精神基礎,不具備適當的社會、政治、法律的條件所可達到的。”即無論是社會體制還是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的體制都應當在新社會發展的洪潮中成長,符合時代的需求。儒學以“禮治”為綱是在西周的社會制度之下,同樣是符合時代的特性。
賀麟在發揚中國諸子之學的過程中結合西方近代精神探討制度秩序和道德思想等方面重新對其發展做出新的闡述。社會民主化的過程逐步加深,打破公和私的對立,建立新的社會民主體制思想,克服社會發展與思想不一致存在的矛盾,從而達到適時的目的,使法治建設發展與古代的禮治社會存在一樣能夠適應社會生活,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的發展。故而,發展中的時代性便成為儒與法相加并行的共同歸因,在儒學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諸多與社會法治建設相關的理論。
2.法治與德治
儒學在教化人的過程中,注重無論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在這種教育人物邪逆之心的過程中穩定社會。在德治與賀麟所提出的法治類型說中不僅僅存在背景和目的相似,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類同:
首先,兩者都提出以意識形態維系社會秩序。儒家的德治,以思想意識在人民大眾中樹立一個標尺,以內心力量規避不正當的行為,以達到國家穩定的狀態。賀麟認為新心學的主體是一個抽象的精神主體,并非一個實踐的、歷史的主題,在哲學的層次上他把文化因素看做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賀麟作為一名哲學家,對于思想的研究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將德治中的“仁”與法治相互交容,在思想上相容以尋求實踐中的突破。賀麟回敬那些極端的物質決定上層建筑、物質條件決定想法觀念的人,說:如若所有的文化制度、思想道德都是由客觀存在而決定,那么文化精神根本就沒有發展的必要,完全由外在物質決定便可。賀麟的某些觀念雖然有些激進,但也反映出其在文化意識等方面極大的研究。在他提出的法治類型說中即有一種為“諸葛式法治”,即統治者具有極高的智慧和深厚的道德修養,為“德治”所共通。這種“諸葛式法治”講求以道德思想感化臣民,在內心信仰中建立威信以期社會和諧。
其次,兩者都存在意識形態的發展性。雖然賀麟在外留學汲取西方部分基督教義的文化,但終究沒有忘記本國文化中明朱理學中人倫的觀念,認為人倫為常道,人肩負社會秩序的維系的責任。并且人倫兼有倡導等差之愛以達到普愛的目的,所以賀麟所主張的法治思想同樣認為法律是“發展人性、保障公民自由”的客觀規律,這與儒家的人倫觀之分相似,不過在人倫的兼愛上發展到當今社會人們對于民主自由的熱切向往。這都體現了賀麟從傳統文化統治觀念向現代法治文明的適應性轉變。
最后,德法兼容。賀麟對那種認為“儒家重德治反對法治”的觀念進行了批判。大多數儒法相爭中兩大學派均相互排斥,可是在進步中各自的取長去短才是發展之道。賀麟看到從孔孟到周敦頤、朱熹等人,在倡導儒學發揚的過程中并不排斥法家的參與。就類似“諸葛式法治”在對馬謖惜才動容之刻也不能打破法治制度的強制性,在德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不遷就道德也不違背法律。這與賀麟所提出的另外一種“申韓法治”是不同的,刑法雖然嚴苛但內里不乏情理,所以賀麟所提出的合理性的法治方式便是依據道德的情感力量揮發出柔與剛的雙重力道。
3.法治與人治
提到“人治”,又不得不提到賀麟的成長背景。賀麟出生于清代末期,在私塾接受過幼年教育,即便后來民主文化開始在賀麟先生的頭腦中發展,但依舊不能抹去童年教育的影子,近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影響。不僅孔子認為“為政在人”,古希臘思想家也提出哲人治國的思想,人治的影響力早已扎根于華夏民族。
首先,從上層領導來看,都需要賢人。賀麟曾說過“故真正的法治,必以法律的客觀性與有效性為根本條件。”“所謂有效性,指立法者與執法者以人格為法律之后盾,認真施行法律、愛護法律、尊重法律,使其有效準而言。”在本源上“儒學”和“法學”都是一種“學治”,若要儒法融于實踐,必須要使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在良法的同時需要一位哲人來掌控。傳統的“人治”注重于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但是賀麟所推崇的“法治中的人治”則以大多數人的幸福作為幸福,實際上是民主的一種體現;而法律實施所獲取的有效性必須建立在維系法律的人必須賢能,并且為公共大眾著想。這是與我們現今政治相符合的,高層政府組成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素養并有兼濟天下之心,保持政府內部的廉潔作風、從嚴治吏、肅清貪瀆;此外,人民的道德受到教化,在有效的法治之下維護和遵守法律,做到良法之治中守法的良民,才能達到有效性和客觀性的雙重結合——這才是賀麟所意圖描述的“真正的法治”。
其次,從治國方略來看,人與法相融。中國古代雖然是君主專制,但是依舊有很多制度對皇權進行限制,明朝有言官對皇帝進行言詞記錄和監督,宋代有相權對皇權進行限制。賀麟所提及的法治制度“乃是自下而上,以人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為原則。政府非教育人民的導師,而是執行人民意志的公仆。”當今社會法的設立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穩定、司法的公正裁判可以讓人民繼續追求自由、“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賢人治國的同時,法律以民主來進行制定,以硬性的規則規范人為性治理的不確定因素,構成人民自愿守護的法治社會。
3.2 法學與新心學
賀麟是新儒學者,并創立了“新心學”,其最大的貢獻在于調和兩個對立面并使之融合。他開始了“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論述,知行合一新論與直覺論是“新心學”的主要理論。
1.中西融合
賀麟自稱“西化儒者”,認為自己是質上的西化而并非胡適等人所停留在的量上或者表面上的西化。在民主法治中,賀麟將西方“仁惠的干涉”和“開明的專制”也納為法治類型說中最高級的民主法治,亦是一種結合人治和德治的法治。在對未來法治發展的期待中,賀麟提出“欲整飭紀綱,走上新法治國家的大道,不在于片面地提倡申韓之術,而在于得到西洋正宗哲學家法治思想的真意,而發揮出儒家思想的法治。”賀麟認識到黑格爾和柏拉圖所提出的法治都與儒家思想有相近之處,走上新的法治道路,并非在于排斥一家所言,而在與融匯百家所長,在儒法相容的同時,貫通西方的法治思想,滋長中國民主法治文化。
2.知行合一
賀麟在發展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理論基礎上,分為自然的知行合一和真理的知行合一。賀麟在法治理論中并不排斥功利主義,提倡“體用兼賅”。在儒法互用的基礎上以功利性討論法治在實踐中的可用性。雖然功利主義為諸多學者所排斥,但賀麟認為功利與非功利本身就不是對立的,也符合其在儒學探索中“和”的思想;在知行問題上,他更是將理論置于實踐的社會經濟體制甚至經濟體制方面,加以驗證知與行的新觀。
3.直覺論
直覺是就是人的突然而覺的意識,但直覺并非憑空產生的,賀麟認為“意思謂直覺是一種幫助我們認識真理,把握實在的功能或技術。”賀麟將“直覺辯證法化”和“辯證法直覺化”交互來看,在對未來法治發展的愿望中,賀麟表示在“諸葛式法治”之上更期待走向憲政的法制即最高層的民主法治。
3.3 儒法之交中的缺陷
在賀麟提出的所有觀念中都非常強調一個概念,便是“人”。或許是循著儒家思想的偏重性,賀麟所提出的法治理念上過分依賴個體的作用。
一方面,從法的制定上來看,需要賢能的人進行法律制定。事實上,法律的制定應依靠民主的力量,符合民主、科學原則。依靠個體,很難保證賢能的個體所代表的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需求,且評判良法的標準又各不相同,無法用個體的標準去衡量群體的要求;另一方面,從法律的遵守來看,法律制定以儒家“仁”的思想原則進行,恐怕難以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賀麟在法治的類型和對未來法治建設中都過于依賴個人作用,他將法治分為申韓式、諸葛式和近代民主法治三種,無論是申韓式還是諸葛式都仰仗于一群賢能的政治首腦。賀麟認為人為的東西都可以依靠人治。若以唯心主義來關照人治,便會太過偏向于主觀的作用,這對人的道德素質或內心強制要求很高,在價值主觀主義和道德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或許難以實現。
4 結語
以大歷史史觀觀之,儒和法一直都是緊緊相隨、綿延發展的。現代中國法治中依然有傳統儒學思想的影子。賀麟從一位儒學者的視角看到了對現代法治建設有益的經驗并予以闡發、建構,是古今中西學術通透徹悟后的表現。既不厚古薄今,又不妄自菲薄、直接施行“拿來主義”,在批判中繼承,擷取古今中外學學說合理資源為中國法治建設提供可用素材,或許才是一種秉持正確史觀下的負責態度,而賀麟先生顯然是這種努力的先行者、探索者。
參考文獻
[1]賀麟.文化與人生[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2]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M].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0.
[3]李錦全.李錦全自選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4]徐忠明.“禮治主義”與中國古代法律觀念[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8.
作者簡介
敖苒(1990-),女,重慶人,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2013級法律碩士,主要從事法理學研究。
鄧君韜(1981-),男,四川綿陽人,西南交通大學法律碩士教育中心副主任,法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法理學、刑事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