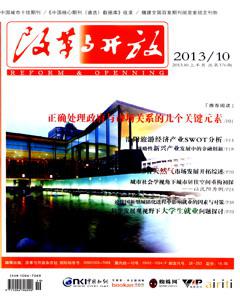探討高等院校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幾個法律問題
方亞琴
摘 要:加強教師的進修培訓以提高師資水平,不僅發展中國家,即使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十分重視。而為確保教師進修培訓后能回校履行服務義務,我國高等院校目前廣泛采取與教師簽訂進修培訓協議的方式,但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以及實踐中對協議性質的誤解,致使協議訂立的程序、內容、法律效力、糾紛解決都存在問題。本文圍繞院校與教師所訂立的培訓協議,從法律性質、訂立程序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關鍵詞:高等院校;教師;進修培訓;協議;行政合同
人才是國家興盛的關鍵,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是影響我國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高等院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要機構,提高師資水平、加強教師的進修培訓自然成為國家人才戰略中最為重要與迫切的環節。我國《教師法》以及前國家教育委員會1996年制定的《高等學校教師培訓工作規程》等作出專門規定。而鑒于市場經濟內生的人才自由流動需求引發人才的安全問題,各高校普遍實行與進修培訓教師簽訂協議的做法。但相關法律法規不盡完善,致使協議的訂立、內容的擬定、法律效力的界分以及糾紛解決均在一定程度上顯得無所適從。
一、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法律性質
現階段我國高等院校教師進修培訓形式主要有:崗前培訓、教學實踐助教進修班、骨干教師進修班、短期研討班、國內外訪問學者、在職攻讀碩、博士學位等。其中,高等院校主要針對教師申請國內外訪問學者以及在職攻讀碩、博士學位等與教師簽訂進修培訓協議。但這類協議究竟為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勞動合同抑或其他,我國學界尚無相關的論述。2001年河南焦作市某區法院曾對河南焦作中央醫院訴湯躍卿及漯河市人民醫院一案,適用勞動法判決被告敗訴。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第1條則明確規定:事業單位與其工作人員之間因辭職、辭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發生的爭議,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處理。若依此,我國高等院校與公立醫院同為事業單位,實行相同的人事管理制度,其與教師簽訂的進修培訓協議當然也屬于勞動合同。但筆者以為,焦作市某區法院的對該案的判決,適用法律是不當的。我國《勞動法》第2條第1款明確排除事業單位對勞動法的適用,第2款“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顯然不針對公立醫院的醫生。就高等院校教師而言,其為學校提供的教學、科研服務雖有一定的勞動因素,但教學、科研本身的長期性、遠效性、復雜性以及產出衡量的不確定性,使得教師與學校之間無法適用《勞動法》的規定。那么,這類協議是否可歸屬于民事合同而適用《合同法》呢?按《合同法》第2條規定,民事合同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高等院校與教師簽訂的進修培訓協議,其主體為高等院校與教師,兩者存在管理與被管理關系,而非平等主體。因此,教師進修培訓協議也不是民事合同。
事實上,按公共產品理論,對教育這種準公共產品的提供屬于政府的職責,而高等院校教師提供教育服務本質上也即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政行為。校方對教師的管理自然屬于行政管理的范疇,他們之間簽訂的進修培訓協議無疑應是行政合同。我國近年來有步驟地在各級各類學校推行聘用制改革,這僅是依據我國《教育法》以及《教師法》對學校管理模式的革新。德國雖對教師實行公務員制度管理,但德國的大學一般也與教師訂立關于職業訓練返回訓練費用的契約;美國加利佛尼亞州《教育法》更詳細規定了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簽訂的程序與內容。我國臺灣地區《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同樣有相關規定。關于協議的性質,盡管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學界及實務界曾有過私法契約說與行政契約說的分歧,隨著德國學者對行政契約標的理論的提出,后者逐漸被人們贊同而成為通說。在行政合同理論上,行政合同有對等關系行政合同與隸屬關系行政合同之分。按德國學者的一般見解,如行政合同主體的雙方或多方均為行政主體則為對等關系行政合同;如一方為行政主體,另一方為公民時,則為隸屬關系行政合同。而隸屬關系行政合同按合同當事人是否互付給付義務再細分為和解合同與互易合同,因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為具有隸屬關系的校方與教師互付給付義務的合意,顯然可進一步歸屬于隸屬關系行政合同中的互易合同。
二、高等院校與教師訂立進修培訓協議的程序
雖然我國《教師法》以及《高等學校教師培訓工作規程》對高等院校教師的進修培訓作出了一些規定,《規程》第23條并許可校方與教師訂立服務合同,但對訂立的具體程序未設條文。實踐中各高等院校由于對協議性質的誤解或法律知識欠缺,在協議訂立程序上普遍采用類似于行政處分的做法并有“乘人之危”之嫌。目前碩、博士培養單位招收研究生雖已不需要原工作單位簽字同意,但在職教師存在轉人事檔案或支付委培費的問題,教師出于各方面考慮此時不得不在協議書上簽字。實質上即校方利用學校管理權對教師締約自由權的強行剝奪,這不論從民事法或勞動法的角度,還是依行政法的規定來衡量都是違法的、不合理的,也是造成教師不愿履約的首要原因。
如前所述,教師進修培訓協議屬于隸屬關系行政合同中的互易合同,而隸屬關系行政合同“在于與本欲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訂立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所以,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訂立程序當然不同于行政處分。而鑒于隸屬關系行政合同當事人地位不平等,從而存在“出賣公權力”或利用公權力欺壓合同相對人的可能。如德國《德國行政程序法》第56條對互易合同訂立規定的限制條款有:(1)人民所給定之給付,須符合特定之行政目的;(2)人民所約定之給付,須為履行公法上任務;(3)人民之約定給付內容與行政給付內容是相當的;(4)禁止雙方給付內容有不合理之聯結。我國至今未制定行政程序法,在《教師法》及其他教育法律法規存在明顯法律漏洞的情況下,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訂立程序能否比照《政府采購法》第43條的規定適用《合同法》呢?筆者認為不可。因為政府采購合同雖為行政合同,但理論上屬于私經濟行政范疇,契約標的雖具有公益性,但也可為私法標的。行政機關在公法的限制范圍及其管轄權限內享有私法上的“契約自由”權,該類行政契約的訂立程序當然可適用私法規定。而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標的主要是教育服務的提供,不可能成為私法標的,其訂立程序自無適用《合同法》的余地。所以,現階段在我國相關教育法律法規修改完善之前,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訂立程序必須并且也只能遵循理論上有關行政程序法的公開、公正、合理、參與、順序、效率等一般原則;并依互易行政合同的法理,側重對教師權益的保護,限制校方的訂約自由。因此,進修培訓協議在要約、承諾階段,校方負有必須訂約的義務,并不得撤回其意思表示。另外,需強調的是行政合同本質上是國家行政“民主化”“效率化”的產物,其既為“以行政法上之法律關系為契約標的,而發生、變更或消滅行政法上之權利義務之合意”,當然應是合同當事人間充分協商的結果,校方因其管理者的優勢地位使其必須切實保障教師參與及協商的權利。
三、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內容
教師進修培訓協議訂立程序的違法、不合理性直接導致協議內容的違法或不恰當,雖各高校與教師簽訂的協議內容不一,但問題較嚴重的基本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1.關于進修培訓費用的約定
因教師進修培訓的重要性,我國及世界其他各國或地區都將其作為政府的強制性義務,進修培訓的經費由高等院校及主管教育行政部門負責。而對教師進修培訓費用的具體負擔原則,臺灣地區視教師進修培訓是由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當局指派或保送還是教師經學校同意而不同。我國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學校教師培訓工作規程》第28條也規定:教育行政部門和主管部門,要設立教師培訓專項經費;各高等學校的教育事業費中,按不同層次和規模學校的情況,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教師培訓;各高等學校根據需要和計劃安排教師培訓的費用必須予以保證。為充分發揮教師參與進修培訓的積極性,《規程》并不區分教師進修培訓的兩種情形,于第29條規定:根據需要或計劃安排參加培訓的教師,學習及差旅費用應由學校支付。并且,第22條規定:為保證培訓計劃的落實,保障教師參加培訓的權利,對按計劃已安排培訓任務的教師,教研室、系和學校一般不得取消。因此,“根據需要或計劃”絕不如目前一些高等院校管理者所認為的意在授予其自由裁量權,可據此與教師約定進修培訓費用的負擔方法。目前教師進修培訓協議中對進修培訓費用的約定條款,如“約定”校方負擔一半或三分之一或只負擔一個具體的數目等,已然構成行政合同理論上的 “跛足之互易契約”,這是最為典型的以公權力欺壓相對人的行為,行政立法對此當然厲行禁止。不過,如教師參加學校業已確定不需要的或學校業已制定的計劃外的進修培訓項目,則校方不負支付進修培訓費用的公法義務,此時校方與教師協商約定費用負擔方法是允許的。
2.關于教師進修培訓期間的工資、津貼、福利、住房等待遇的約定
該項內容體現的主要是校方及教師在經濟上的利益,具有較明顯的私法屬性。所以,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在側重保護教師權益時也強調雙方利益的平衡,但這主要體現在教師享受上述待遇的程序上,至于實體上則均應保證教師如同工作中一樣享有上述待遇。美國加利佛尼亞州《教育法》為保障學校及教育當局的利益不受到損失,第88224條規定:教師培訓或學習回校后,培訓或學習期間的工資、福利等待遇采取補償的方法,即在回校服務的兩年內,學校按替班人員的工資補償給教師,差額部分由教育當局填補。我國教育部制定的《規程》第30條規定:根據需要或計劃安排,在校內或校外培訓的教師,其工資、津 貼、福利、住房分配等待遇,原則上應不受到影響。同時也可視情況在教師全部或部分享受之間進行協商,但應遵循行政合同中“禁止不合理之聯結”的法理。
3.關于教師進修培訓后回校服務期限的約定
回校履行服務義務作為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根本內容及主要目的,一方面事關各高校自身的發展利益,另一方面也直接影響人才自由流動及人才安全機制的正確建立與健康運行以及教師的個人發展。所以,立法得著眼于各國或地區的實際盡可能地在兩者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如美、德、法等發達國家一般沒有服務期限的限制。而我國臺灣地區《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12條規定:全時進修、研究者,其服務義務期限為帶職帶薪間的兩倍;留職停薪進修、研究或部分辦公時間以公假進修、研究者,其服務義務期限為留職停薪或公假之相同時間。我國目前的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對此卻未設任何規定,實踐中各高校校方行使著“完全自由裁量”權,其不合理性不言自明。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立法對之作出限制規定勢在必行。其中,對在職進修培訓以及留職停薪脫產進修培訓應沒有服務期限的要求,而帶職帶薪的脫產進修培訓則以脫產時間的兩倍為宜。
4.關于違約責任的約定
目前大部分教師進修培訓協議都有違約責任的“約定”,且基本針對教師一方,如“約定”教師如違約需要退回進修培訓期間的所有工資、津貼、福利、進修培訓費用。并且在這之外一般還“約定”教師需向校方支付違約金。毋庸置疑,違約責任的約定作為擔保合同履行的重要手段,構成私法合同的主要條款。然而,在教師進修培訓協議中作如上“約定”,卻值得懷疑。首先,依《規程》第23條規定:教師參加半年以上培訓后,未完成學校規定的教育教學任務或未履行完學校合同即調離、辭聘或辭職的,學校可根據不同情況收回培訓費。顯然,違約責任的約定應以培訓費用的部分或全部返還為限。“約定”教師退回進修培訓期間的所有工資、津貼、福利于法無據,同時這種“約定”也極不合理,因為教師依學校“需要或計劃安排”參加進修培訓已不簡單的是個人行為,它實際上是在履行學校確定的培訓義務,完成學校的任務,本質上已構成教師工作的一部分,當然具有獲取工資、津貼、福利等待遇的權利。臺灣地區《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13條也僅規定:教師進修、研究后,如未履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之事由外,應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研究期間所領之薪給及補助。其次,教師進修培訓協議中對違約金的“約定”,顯然對教師具有懲罰性。這不僅《規程》及其他教育法律法規沒作規定,即便在勞動法中,不少國家都明令禁止,我國學者也認為在勞動合同中約定違約金條款與勞動立法規定相違背,以及因其不同于民事合同的性質,以及其適用的不對等性、造成對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限制等原因,勞動合同中的違約金條款約定必須受到限制。私法合同中雖普遍約定違約金條款,但也以填補損失為原則,如我國《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適當減少。
四、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的法律效力與糾紛解決
1.教師進修培訓協議法律效力的確定
教師進修培訓協議既屬于行政合同,其法律效力的確定當然遵從行政立法的規定與法理要求。德國《行政程序法》第59條規定:民法典中合同無效制度準用于行政合同。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也借鑒其規定,在第141條第1款規定: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但臺灣學者對此反對意見較大,認為民法有關契約無效的范圍太廣,與行政契約本質上不應使其動輒無效而盡量縮小其無效原因之特征不盡吻合,況且行政合同本意與私法中的合同相區分,此一規定極易造成混亂,影響行政契約法的穩定性與適用性。所以,行政合同的效力有無應只受行政程序法的約束,如行政機關超越訂約權限或違反法律法規關于不得締約的規定而訂立的行政合同無效;行政機關訂約時,未履行告知及相對人參與程序者無效。對此,澳門《行政程序法》第172條更進一步規定行政合同的效力尚取決于相關行政行為的效力,在訂立行政合同所取決之行政行為無效或可撤銷時,該行政合同亦為無效或可撤銷,且適用本法典之規定。所以,筆者認為,教師進修培訓協議法律效力的確定,首先應依《教師法》《規程》等教育法律法規的規定,對校方的訂約行為應嚴格體現“依法行政”的要求。首先,在訂立程序上未保障教師參與協商的,無效;協議內容違反上述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無效;若法律法規未作規定或設有授權性規定時,則依合理性確定協議的效力;同時,協議部分無效應不影響其他部分的效力,并且協議無效不影響教師要求賠償的權利。
2.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糾紛的解決
一般來說,行政爭議的解決有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兩種形式。而對行政合同糾紛,尚可通過仲裁的辦法。如澳門《行政程序法》第175條規定:容許依據法律規定采用仲裁。依據我國人事部1997年發布的《人事爭議處理暫行規定》,以及1999年的《人事爭議處理辦案規則》和《人事爭議仲裁員管理辦法》,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糾紛可通過人事仲裁解決。目前我國也已有27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制定了相應的人事仲裁條例或實施辦法,對人事仲裁的法律救濟,各地一般規定可要求再行仲裁,僅《北京市人事爭議仲裁辦法》規定:“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第2條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并賦予了人事仲裁司法強制執行的效力,即:當事人對人事爭議仲裁裁決不服的,自收到仲裁裁決之日起十五日內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間內不起訴又不履行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執行。然而,當事人不服人事仲裁裁決向法院起訴,屬于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最高法院的規定與《北京市人事爭議仲裁辦法》都未見明文。若依最高院《若干問題》第1條規定,似屬民事訴訟。但該條誤將教師進修培訓協議視為勞動合同,不恰當性已如上文所述。并且該條的錯誤也使第2條的適用無所適從,因人事爭議的仲裁在實體法上必然依據有關人事管理法律法規,而不服仲裁裁決提起訴訟則如第1條規定適用《勞動法》,這不僅在訴訟法理論上是極其荒謬的,訴訟的實體判決也與仲裁裁決存在天壤之別。因此,在明確了教師進修培訓協議屬于行政合同之后,當事人如對人事仲裁結果不服的,當然應如同《政府采購法》第58條的規定一樣,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總之,教師進修培訓協議糾紛的解決應包括三種途徑,即向高等院校的上級主管教育行政部門申請行政復議;申請人事仲裁;提起行政訴訟。并且,行政復議并非必經程序,當事人可直接向法院起訴,但人事仲裁卻是訴訟的必要前置程序。
參考文獻
[1]http://www.cctv.com/program/lawtoday/01/in dex.shtml.
[2] 翁岳生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669-770.
[3]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calawquery.
[4] 林嘉.勞動合同若干法律問題.法學家, 2003(6).
[5] 翁岳生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784-785.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