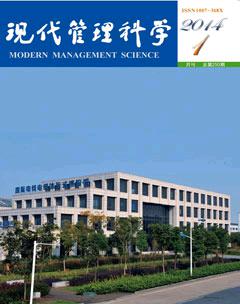基于最低質量標準的創新激勵研究述評
馮磊東 顧孟迪
摘要:文章界定了縱向產品差異化中最低質量標準的內涵和意義,對不同市場條件下最低質量標準的影響以及在不同領域的應用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評述了現有研究的理論貢獻和不足,指出了有待繼續研究的方向和切入點。
關鍵詞:最低質量標準;消費者剩余;社會福利;創新激勵;網絡外部性
一、 最低質量標準的內涵和意義
由于研發能力、生產成本和經營方式等因素,競爭性企業生產的同類型產品可能存在縱向差異化。一般而言,縱向差異化市場中,產品的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 Quality Standard,MQS)都是以質量為標的,必須達到的最低限度,常用來增加市場上產品的質量水平。Leland(1979)首次引入MQS的概念,并把MQS看作是代表某一質量水平的許可標準,是強制執行的,低于此質量水平的產品被禁止供應。
在各行業中,由于消費外部性,或企業為降低價格競爭而開發具有差異性的產品,或為提升產品質量和社會福利水平等原因,政府或規制者常考慮設立最低質量標準。直覺上:MQS的規制能夠增加消費者剩余,但同時產品質量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會增加生產成本以及質量的研發成本,從而造成企業利潤的降低。因此,衡量MQS的規制對社會總福利的影響取決于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相對大小。
二、 最低質量標準的理論研究
通過學者的研究發現,最低質量標準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結論有較大差異。產品縱向差異化模型中,關于質量成本一般有兩種假設:固定質量成本和可變質量成本。企業為了生產某一質量水平的產品,需要投入固定成本以研發相關的技術,這部分沉沒成本一般被稱為固定質量成本。而生產過程中隨產品數量變化的成本稱為可變質量成本。大多文獻是在兩種成本以及不同競爭類型下討論MQS的影響,結論總結如表1所示。
1. 固定質量成本。較為重要的文獻是Ronnen(1991)使用Shaked和Sutton(1982)的理論框架研究MQS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在二次固定質量成本下,MQS縮短了兩企業產品的質量差距,導致更為激烈的價格競爭,從而增加了消費者剩余、低質量企業的利潤和社會福利,然而降低了高質量企業的利潤。Constantatos和Perrakis(1998)認為:MQS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是否在進入市場之前就確定質量水平。如果企業在進入后才確定質量,MQS將會產生“親競爭效應”,增加社會福利;如果進入之前選擇,則會產生負效應,減少社會福利。Valletti(2000)認為:兩企業的競爭類型決定著MQS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與Bertrand競爭的結果恰恰相反,兩企業進行Cournot競爭時,規制MQS并不提高社會福利。也就是說,在數量競爭時,規制者不宜設定MQS。現實情況也是這樣:雖MQS提升了產品質量,但也增加了成本和價格,反過來又縮減了產量,對消費者剩余的影響并不明確。不同于Ronnen(1991)和Valletti(2000)的兩競爭性企業的對稱性(即兩企業的成本函數相同),Jinji(2004)考察了質量成本函數不對稱條件下兩企業競爭均衡的內生質量選擇。研究發現:在Bertrand競爭下,與未規制時的低質量充分接近的MQS提高了社會福利,因為MQS增加消費者剩余的幅度遠大于兩企業利潤的損失;然而Cournot競爭下,MQS對社會福利產生負的影響。Lee和Phuyal(2013)考察了在MQS規制下在位者與進入者各自的策略,研究了與MQS相關的允許進入和阻止進入的條件。如果在位者不再限制質量,在多種情況下,MQS都將增加社會福利。
2. 可變質量成本。Crampes和Hollander(1995)在可變質量成本和市場完全覆蓋假設下,認為:適當的MQS能夠增加低質量企業的利潤,相反高質量企業的利潤會降低。僅僅當低質量企業的質量提高,而高質量企業的反應較弱甚至沒有反應時,消費者獲益,同時社會福利水平提高。Lambertini和Mosca(1999)比較了影響社會福利提高的兩種調控手段:對某一質量的產品稅收或補貼、最低質量標準。不同市場結構下兩種手段的有效性截然不同:壟斷情形下,對于社會福利而言,兩者等價;雙寡頭壟斷下,MQS的作用不如前者。Ecchia和Lambertini(2001)考察了當企業內生選擇產品質量時,政府如何規制最優的MQS以提高社會福利。
當存在邊際生產成本以及質量跟隨企業(或潛在進入企業)有固定進入成本時,Noh和Moschini(2006)研究在位企業的進入阻止策略和潛在進入企業的質量選擇。當進入企業的固定成本充分小時,在位企業的最優策略是容許進入,且選擇高于壟斷時的質量使得均衡時進入企業在較高質量與較低質量間是無差異的;當進入企業的固定成本處于中等水平時,在位企業在跟隨者進入市場前提高自己的產品質量以阻止其進入;當進入企業的固定成本充分大時,進入將被封鎖,在位企業仍選擇壟斷質量。進入被容許后,消費者剩余增加了,但社會福利不一定提高;然而當市場上消費者對質量要求足夠高時,阻止進入可使社會福利提高。
Kuhn(2007)與傳統模型不同,假設消費者除享有與質量相關的效用外,還享有與質量無關的基本效用。關于MQS的影響,作者認為:當基本效用極大時,消費者剩余和企業利潤驟降,社會福利降低;中等水平時,并沒有明確的影響;充分小時,提高社會福利。
三、 MQS在不同領域的應用研究
1. 國際貿易領域。產業組織領域的MQS模型經常被置入到國際貿易領域,考察兩國設定MQS對本國以及他國的影響。Ronnen(1991)基于一個市場,并未涉及國家間的相互影響。而Boom(1995)研究了MQS對市場分離兩國的影響,認為:如果兩國都沒有企業因為較高的MQS而退出市場,那么兩國的消費者剩余及產品質量都較高。大多文獻分析MQS對社會福利的影響,通常的假設是:一國收入水平服從均勻分布且產品市場能夠完全覆蓋,并得出MQS會降低一國社會福利的結論。高建剛(2008)則假定市場不完全覆蓋,且拓展了收入服從均勻分布的假設,通過對收入不同國家的比較,探討MQS對社會福利和市場結構的影響。鄭尊信和陳潔(2006)基于市場消費者結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考慮,設置不同水平的MQS,探討進口和本國企業之間競爭的博弈均衡演變及社會福利的變化。俞靈燕(2005)在服務貿易中研究了MQS政策的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既要積極采用適當MQS規范本國對外開放的服務市場,又要加強與發達國家磋商,爭取對方的MQS能夠包容本國有比較優勢的服務出口。
現有的文獻,在質量規制的市場中,關于阻止競爭對手進入的激勵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Lutz(2000)在兩國間的策略博弈中研究了MQS對阻止對手進入的貿易效應。且Lutz和Lutz(2010)構建了高質量企業和低質量企業的非對稱成本模型,國內的高效企業和國外的低效企業可以同時在國內市場競爭,作者認為:規制MQS能使國內企業將國外企業逐出國內市場。也有學者把MQS作為貿易技術壁壘的因素考量。如魯文龍和陳宏民(2008)在開放的經濟體中,研究作為貿易技術壁壘因素的MQS如何對企業利潤及社會福利產生影響。劉瑤和王榮艷(2010)則假設各國企業生產成本存在差異,通過兩國博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設置技術貿易壁壘后,若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企業能夠通過研發、投資(或政府補貼等方式)達到MQS而繼續出口,則兩國企業的產品質量均會提高,且發達國家高技術企業的利潤會下降,生產成本的差異也會影響均衡時兩國企業的質量選擇和政府的最低補貼。與以上思路不同,何理(2006)把消費者對進口產品質量偏好的最下限作為技術性貿易壁壘,認為:發達國家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設置,降低其產品進口的需求,導致市場均衡價格和均衡利潤均下降,但我國出口企業利潤下降幅度更大。若我國出口企業能夠提高產品質量積極應對,產品的市場需求和企業利潤就將上升,相反發達國家本國生產的產品需求和企業利潤將下降,但其消費者的福利卻有提高。
2. 其他領域。對政府來說,MQS是規制產品質量的良好工具。現實中有很多與MQS相關的例子,如電子設備和汽車的安全標準、食品和藥品的成分標準以及能源或化工產品與環境相關的標準等。從產品的生產是否對環境造成危害的角度考慮,Lambertini(2012)將MQS應用到污染產品的縱向差異化模型中,同時引入環境負外部性因子,用于衡量生產對環境的負影響程度。分別在質量固定成本和質量可變成本兩種框架下,考察價格和數量競爭中MQS及負外部性的影響。在Bertrand競爭中,MQS降低了產品的差異性,從而造成兩方面的影響:產量增加,污染也隨之增加。顯然,對消費者而言,產品產量和平均質量的提升,消費者剩余也增加。但從環境考慮,污染程度加深。如果污染的負外部性大于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政府或規制者則不會采用MQS以提升平均質量水平。相反,在Cournot競爭中,MQS降低了產量和污染。產量和污染的降低以及平均質量的提升,這兩者間的整體作用是否能夠增加社會福利,成為規制者采用MQS的關鍵。
四、 簡要評述
1. 現有研究的理論貢獻。
(1)研究角度的突破。大部分文獻基本上考察MQS規制對價格、生產者利潤、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的影響。關于高質量企業對新技術的投資激勵與MQS的關系,相當少的文獻對此進行研究。產品的質量水平與技術創新密不可分,因而探究MQS對創新激勵的影響是研究角度上的一大突破。Maxwell(1998)在最低質量標準模型中首次引入技術參數,用于反映使質量成本下降的創新的激勵。結果顯示:MQS產生了負效應,降低了高質量企業對更高效技術的采用激勵。正在進行創新的企業一般都期望:一旦自己完成創新,政府或規制者就設定MQS以防止后來者過分模仿或進入市場。與未規制情況相比,MQS的引入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激勵,導致較低水平的社會福利。
(2)靜態到動態的轉化。傳統認為,如果企業進行Cournot競爭,MQS將對社會福利產生負影響。然而這僅僅關注MQS的靜態效應,忽略了可能的動態效應。Ecchia和Lambertini(1997)、Napel和Oldehaver(2011)考察了MQS內生選擇的動態效應,特別是對兩企業合謀穩定性的影響。
Hackner(1994)在固定質量成本下外生選擇MQS以考察合謀的穩定性,認為:產品質量水平越接近,即差異化程度越低,價格合謀的狀態就越持久。因為隨著差異化的降低,高質量企業的優勢也趨于消失,而當兩企業的產品可充分替代時,合謀的激勵就越大。直覺上,如果高質量企業能在與競爭對手產品的較大差異化中獲取較高的利潤,那么獲利較少的合謀策略相對就缺少吸引力,高質量企業將放棄合謀。Ecchia和Lambertini(1997)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兩個方向的擴展:①內生選擇MQS使社會福利最大化;②MQS造成產品差異化的降低,是否會導致兩企業為了保護利潤而合謀。假設產品生產需要投入外生固定的沉沒成本以及可變質量成本,作者得到如下結論:內生選擇的MQS增加了社會福利,低質量企業和低收入消費者的獲益超過了高質量企業和高收入消費者的損失。并且,如果消費者充分富裕(或者隨收入增加,產品變得充分可替代),MQS使企業很難進行價格合謀。結論之所以與Hackner(1994)截然不同,主要是因為假設可變質量成本。作者研究發現:MQS不僅在靜態上增加了社會福利;從長遠看,也產生了支持競爭阻止合謀的動態效應。Napel(2011)考察了在Cournot競爭下MQS的影響。盡管從靜態考慮與Valletti(2000)一樣有損失,即MQS降低了社會福利;但MQS也使得合謀的激勵降低。因此,MQS也產生了阻止合謀的動態效應。
(3)競爭企業數量的擴展。大部分文獻認為MQS對社會福利產生正的效應,但這樣的結論幾乎完全依賴于雙寡頭競爭。Scarpa(1998)在固定質量成本和Bertrand競爭下,首次對三個競爭性企業進行研究發現:并非所有質量水平的反應函數都是增函數,且MQS降低了三個企業的利潤水平、最大質量水平和平均質量。而Pezzino(2010)則在同樣條件下考察了Cournot競爭,卻得到相反的結論:平均質量水平增加。如果三個都是國內企業,則國內總福利降低。然而,如果允許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則結論可能不同。
2. 現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1)放寬條件限制,研究更廣泛意義上的創新激勵。盡管Maxwell(1998)引入技術參數衡量創新激勵,是在技術創新和MQS之間建立聯系的一大突破,然而如Bacchiega(2010)證明所示:不管MQS是否存在,Maxwell(1998)的結果與市場完全覆蓋的條件并不相容,即在市場完全覆蓋下并不能準確判斷MQS對高質量企業的創新激勵產生何種影響。由此,可以得到啟示,完全拓寬研究思路,在更一般的條件下(如固定與可變質量成本、Cournot與Bertrand競爭、市場完全覆蓋與否以及多個競爭企業等),探索MQS對創新激勵的影響,從技術創新角度得到更深層次的理論,對現實情形進行合理的解釋。
(2)網絡外部性的拓展。傳統經濟學中的外部性,指一個(群)人的行動和決策影響到其他人的利益,而行為人不完全承擔從事經濟活動時的成本與后果。網絡外部性是傳統經濟學中外部性在網絡系統中的表現,廣泛存在于電信、航空等領域。網絡外部性,即消費者使用某一物品的效用,隨其他消費者對該物品或該物品的兼容產品的消費的增加而增加。用戶總人數越多,每個消費者得到的效用就越高。在網絡外部性的條件下,探索MQS對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利潤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同時考察MQS對創新激勵的作用,更符合實際情況,能夠得到更具意義的成果。
參考文獻:
1. Jinji N & Toshimitsu T.Minimum quality s- tandard under asymmetric duopoly with endogenous quality ordering: a note.Journal of Regulation Economics,2004,26(2):189-199.
2.Kuhn M.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nd market dominance in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duopo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 nization,2007,25(2):275-290.
3.Lambertini L & Tampieri A.Do minimum qua- lity standards bite in polluting industries. Research in Economics,2012,66(2):184-194.
4.Lee S & Phuyal R.Strategic entry deterr- ence by limiting qualities under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2013.
5.Lutz M B & Lutz S.Pre-emption, predation, and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International Eco- nomic Journal,2010,24(1):111-123.
6.Lutz S. Trade effects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with and without deterred entry.Jou- 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000,15(2):314-344.
7.俞靈燕.技術壁壘作用機理及其在服務領域的表現——一個基于MQS模型的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2005,(7):64-68.
8.高建剛.MQS對社會福利和市場結構的影響.當代財經,2008,(8):25-29.
9.鄭尊信,陳潔.最小質量標準及其設計,工業工程與管理,2006,(2):95-100.
10.魯文龍,陳宏民.最小質量標準及設定動機研究.系統工程學報,2008,(4):194-200.
11.劉瑤,王榮艷.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保護效應研究——基于“南北貿易”的MQS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10,(7):49-54.
12.何理.技術性貿易壁壘的Bertrand博弈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06,(4):40-43.
13.陳紅文.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及對策.管理世界,2005,(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企業研發網絡、技術創新能力演進及其相互促動機制”(項目號:71132006)。
作者簡介:顧孟迪,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馮磊東,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