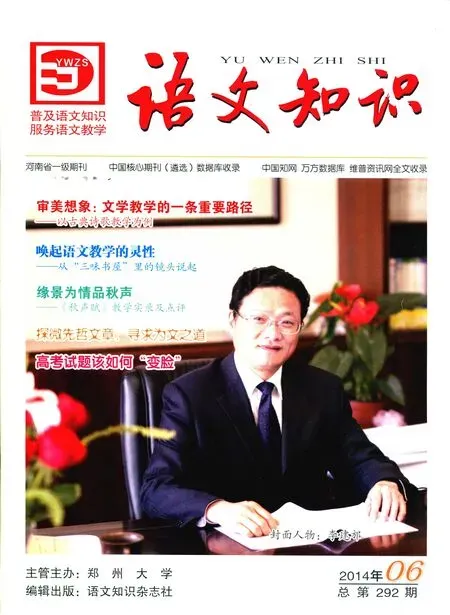《廉頗藺相如列傳》注釋商榷三則
◆ 南陽師范學院五年制管理中心 逯 靜
《廉頗藺相如列傳》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名篇,先后被多家教材和古文選收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實驗修訂本·必修)語文第六冊亦收入此文,然筆者研讀時發現,其中個別注釋值得商榷。現將其條陳如下,以就教于諸位同仁。
一、宜可使
《廉頗藺相如列傳》一文中對“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中的“宜”,教材注為“應該”,與此相應,配套使用的《教師用書》譯文中將“宜可使”翻譯為“應該是可以出使的”。如此作解,單從此句來看,也似可通,但細思之,便覺不妥。這是宦官繆賢對趙王所說的話,封建社會等級制度森嚴,臣對君進言,總是要謙卑有加才是,若將此句的“宜”譯為“應該”,則對趙王不敬,要派誰出使,是趙王做決定的,作為臣子不能很絕對地說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蘇教版語文教材第三冊亦收錄此文,注“宜可使”為“可供差遣,宜,適宜。”“宜,適宜”,語氣也較肯定,亦不妥。我們認為:此處的“宜”當為“副詞,表示一種情理上的推測,可譯為大概、似乎、也許等”。“宜”的這種用法,雖然在現代漢語中不常見,但是在古代漢語中習見,如:
[1]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左傳·成公二年》)
[2]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孟子·公孫丑下》)
[3]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史記·陳涉世家》)
[4]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漢書·佞幸傳》)
訓“宜”為副詞,表推測,有訓詁為證,如:
《經傳釋詞·卷五》:“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曰: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離婁篇》宜若無罪焉。宜并與殆同義。”《經傳衍釋·卷五》:“《孟子》信斯言也,宜莫若舜。言殆莫如也。”
再查閱古漢語虛詞類工具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寫的《古漢語虛詞詞典》,何樂士等編寫的《古代漢語虛詞通釋》,李靖之、李立編寫的《文言虛詞詮釋》,王力編寫的《王力古漢語詞典》等,“宜”字均收錄“副詞,大概”之義項。《文言虛詞詮釋》“宜”字“副詞,表示對情況的推測。可譯為也許、大概”之義項,所用書證,正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宜可使”句。
可見,人教版和蘇教版對“宜可使”中的“宜”所作之注,均誤虛為實,不確。此句可以翻譯為:“臣私下里認為他是勇士,有智謀,大概可以出使(秦國)。”
二、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其中“間”字,課本的注解是“間道,小路。這里用作‘至’的狀語,‘從小路’的意思。”與之配套使用的《教師教學參考書》將此句翻譯為:“我實在怕受大王欺騙而對不起趙國,所以派人拿著璧回去,已經從小路到達趙國了。”這樣的注解和翻譯,筆者認為很有商榷之必要。
間,沒有“小路”之義,只有“間道”“間路”才指“小路”。間,字本作“ ”,《說文》無“間”字,“間”為“ ”之俗體字。《說文》:“ ,隙也,從門,從月。”徐鍇《系傳》:“夫門當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間隙也。”段玉裁注:“會意也。門開而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如《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為相,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由門縫引申出空隙。如《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再引申為人與人之間有隔閡、嫌隙。如《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曰:‘諸侯有間矣。’”引申為乘隙,乘間。如《國語·魯語下》:“昔樂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左傳·僖公三十年》:“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楊伯峻注:“間,猶言乘隙,今曰鉆空子。”間由乘隙之義虛化,進一步引申可以用作副詞,秘密地。如《史記·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司 馬貞《索隱》引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又引孔文祥云:“竊伺間隙,不欲令眾知之。”《漢書·高帝紀上》:“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顏師古注:“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皆可證,“間”有副詞,“秘密地”之義。查《王力古漢語字典》“間”字,收錄義項“副詞,秘密地”,且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間至趙矣”作為首條書證,王先生此說甚確。
其實我們只需按常理推之,就可知道教材釋“間”為“小道”主觀臆測成分較大。當時的形勢,藺相如一看情形不妙,肯定是派遣手下人喬裝打扮秘密攜和氏璧潛回趙國,至于是走大道還是小道,他肯定是不得而知。不管大道還是小道,只要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秘密潛回趙國就達到了目的,再說,從秦國到趙國,也不一定走小路距離就近,走大道距離就遠。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秦國發現,所以釋“間”為“秘密地”既與“間”的詞義引申系統相吻合,更與情理相一致。教材所注,欠妥。
三、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
對文中“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中的“為好”教材注為“和好”。如此,該句就要翻譯為“秦王派遣使者告訴趙王,想要和趙王和好,在西河外的澠池相會。”從字面意思上看,這樣解釋也無可厚非,完全可以解通,但是我們查閱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標點本《史記》,此句皆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加標點,我們認為非常準確,人教版教材拆雙為單,所加標點,不確。此處的“好會”乃是一個雙音節詞,不能分而解之。“好會”作為雙音節詞連用,《史記》中除《廉頗藺相如列傳》1例外,還有5例,如:
[1]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史記·世家第二》)
[2]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史記·世家第一○》
[3]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史記·世家第一○)》
[4]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史記·世家第一七》)
[5]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史記·世家第一七》)
除《史記》外,其他典籍亦很常見,如:
[6]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說苑·卷第十二》)
[7]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李善注引《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
綜上,“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的標點,應如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史記》的標點改之,即去掉第二個逗號,變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從句法上講,“欲與王”之“欲”為動詞,“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整個小句作賓語,小句中的“與王”是修飾語,“為”是動詞,“好會”是賓語,“于西河外澠池”是地點狀語,誦讀時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整個句子可以翻譯為:“秦王派遣使者告訴趙王,想和他在西河外的澠池舉行友好會見。”
[1]何樂士等.古代漢語虛詞通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李靖之,李立主編.文言虛詞詮釋[M].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4.
[3]中國社科院古漢語研究室主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4]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字典[Z].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社,1992.
[5]羅竹風.漢語大詞典[Z].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