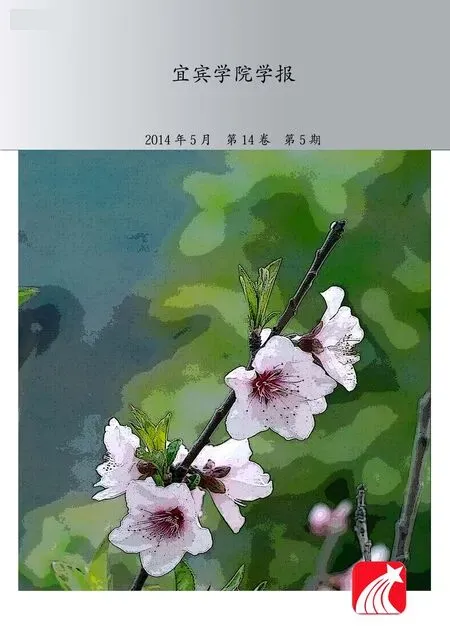關于“民國機制”命名和定義研討的反思
——兼與李怡等學者商榷
徐詩穎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21世紀以后,“民國”聲音的出現給正深陷如何為“文學史”格局進行新的開拓和建構等問題而焦慮的學術界注入了新的研究活力。其中,李怡提出的“民國機制”是此類研究中最晚發出的一種聲音,卻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它是一個立體的概念,建立在“民國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繼承了“民國史視角”的“‘歷史還原’還需刻不容緩”[1]的觀察問題角度,突破了“民國文學史”單純用“時間概念代替意義概念”[2]的歷史敘述框架。
據李怡對“民國機制”的定義和相關學者的理解,筆者初步對“民國機制”所反映出來的屬性概括如下:機制性、結構性、主體性、民國性、還原性。每種屬性都可以反映出“民國機制”的獨特意義,但不是各自為政,而是共同作用于“民國機制”。這些屬性讓我們從具體的國家歷史情態中重點挖掘歷史文化的諸多細節,更真實地展現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等多種元素,以及研究這些元素在如何相互結合和包容中形成影響我們語言交流和精神互動的“格局”,仔細分析它是如何決定和影響了我們的生存需求、愿望和興趣。
然而,任何洞見必定要在遮蔽其他現象的基礎上才能有所顯現,“民國機制”也不例外。當一種理論或觀念變得“日常化”的時候,它的“洞見”最終會變成文學史的“盲視”。[3]此種敘述范式在命名和定義上還有一些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第一個引起省思的問題是“民國機制”的命名。這里強調一下,“民國機制”實際指的是民國文學機制。[4]從許多文章的稱呼上面可以看到,“民國機制”一名已經形成共識。然而,問題就來了,“民國機制”跟“民國文學機制”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開始,李怡用的是“民國文學機制”一名,這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我們怎樣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民國”意義》兩篇論文里可以證明,可是后來很多論文都把“文學”二字省略了。這是否能說明作者在有意拔高概念本身所闡釋的范圍呢?然而,僅從概念闡釋作用的對象和支撐其背后的力量來看,兩者是不能處于等同地位的。先以“民國機制”作分析。筆者把它拆成“民國”和“機制”兩部分來理解。實際上,“民國機制”只可以充當技術性的時間指稱,偏向的是社會學和政治學范疇的術語,探討的是民國時期諸種“結構性”力量綜合之于民國發展作用的考察。而“民國文學機制”才是李怡真正要研究的敘述范式,探討的是民國時期諸種“結構性”力量綜合之于文學發展作用的考察。李怡對此定義的研讀更加著重于“文學機制”四個字。他所定義的“機制”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學表現形態,突出強調了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共同作用,彼此配合,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此時,概念一目了然。李怡要研究的就是民國時期下的文學機制,起于“清王朝覆滅”,改變或者結束于1949年的政權更迭。[5]更進一步來說,這些研究表面上看屬于社會體制的考察,其實質應是“體制考察與人的精神剖析”的相互結合。[5]機制指涉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它聚焦更多的不僅是如何解讀歷史,還需要有對文化和文學的內在“結構性”元素的還原和總結。
第二個需要省思的問題是“民國機制”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內涵是充滿矛盾的。在定義里,李怡突出強調諸種綜合性的社會力量共同作用于中國現代文學。雖然他突破性地提出了“文學機制”的敘述范式,但事實上,它作用的對象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實質未能跳出“現代”意義的內涵,只不過多了一層要摸索中國自己的“現代經驗”與“現代思想”而已。李怡說:“‘民國性’就是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現代性’的真正的落實和呈現”。[6]他認同民國時期的文學有值得挖掘的“民國性”。李怡在《文學的“民國機制”答問》一文里提出暫且未能將多種文體,特別是舊體詩詞、通俗文學等納入“民國機制”平臺進行討論。對此,筆者提出另外一個疑問:“自由主義作家、海派作家等是否能與新文學作家、左翼作家等接受同等待遇呢?”眾所周知,“現代”內涵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解析,特別從西方傳入中國后,起止時間、作用范圍和實質意義等都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回首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一度中國現代文學成為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翻版。[7]這種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使中國的“現代”缺失了啟蒙、平等、理性、自由等西方“現代”所包含的因素,僅僅單一以政治判斷作為價值尺度和評判標準。李怡對此還是很清楚的:“我們提出‘民國機制’最終還是為了解決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若干具體問題……‘民國機制’才更能發揮‘方法論’的作用。”[5]那么,從以上的分析可初步得出結論,由于民國機制背后的價值立場還是暗含很強的“現代”意味,所以它并沒有在文學史觀上有實質性的突破,只是在方法論上有所改進而已。
第三個值得省思的問題是劃分“民國機制”研究邊界的依據。在第一點引起省思的問題上,如果以“民國文學機制”命名作為討論的前提,李怡著重強調的便是“文學機制”四個字。既然他已經把形成“民國文學機制”的時間和作用于機制的各種力量所醞釀的時間定在1912年民國成立以后,那么可以看出他是選擇以國體和政體作為劃分“民國機制”邊界的依據。有些學者質疑這種劃分依據的合理性,筆者也想提出類似的疑惑。李怡對“機制”的另外一個解釋為:“清王朝覆滅以后,新的社會形態(民國)中逐步形成的影響和推動文學新發展的種種的力量,或者說,因為各種力量(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文化結構、精神心理氛圍等)的因緣際會最終構成了對文學發展肯定,同時在另外的層面上也造就了某種有形無形的局限。”[4]毫無疑問,機制的形成是逐步的,而不是一瞬間就能完成的。然而,奇怪的是,在談到為什么叫“民國機制”的時候,李怡的答案是:“形成這些生長因素的力量醞釀于民國時期,后來又隨著1949年的政權更迭而告改變或者結束。”[5]這里用了“醞釀”一詞,問題便出現了:“影響和推動文學新發展的種種力量”真的是在“新的社會形態(民國)”中醞釀并逐步形成的嗎?晚清、辛亥革命時期西方(特別是歐美日)對中國的影響就沒有嗎?民國成立之后,它們對深陷在水深火熱的中國,或者是整個中國文學界真的有翻天覆地的影響嗎?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要想逐步形成具有“民國性”的現代文學需要醞釀,也即需要時間。事實上,李怡并沒有否認文學的發展是復雜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就是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下人們的心理情感變化。人們的心理情感是一種主觀現象,因人而異,其豐富性導致了文學的復雜性。”[8]李怡還提到:“它的存在推動了精神的發展和蛻變,最終撐破前一個文化傳統的‘殼’而出”。[9]前后表述的不一致讓人疑惑不解,一個學者為什么對這些理由的表述會如此不同呢?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梳理清晰,那么這種“一刀切”的“二元對立”思維是否還能在定義里面成立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和遺憾的事情。可以看出,要想徹底根除在學者頭腦里面的“二元對立”思維其實是很不容易的。這個問題和近幾年不少學者提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邊界應“向前移”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對于“向前移”的問題,思路也是一樣的。以“1919”年為界限,主觀上否定了晚清和民國成立對現代文學的影響,武斷地認為它是“五四”文學革命的起點和它的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性質。當然,討論的前提是不能有意降解“五四”。溫儒敏在《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及“價值尺度”問題: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現狀的梳理與思考》一文里對此也作過相關敘述。如果“前移”是有利于文學史觀的調整而不是徹底顛覆,那么這種研究是可行的。鴉片戰爭以后,世界文化與文學大潮從不同渠道傳入中國,對傳統文化形成威脅,對中國的文化和文學產生重大影響,不少學者被迫或者主動向西方學習。量變才能引起質變,民國的各種結構性力量其實從晚清就開始逐步醞釀,不可能是民國以后才來一個跟以前完全決絕的新開始。進一步說,民國時期的各種有利條件給機制力量的迅速轉型和壯大提供了持久的保障,但是它們的起源不應該定在1912年清王朝覆滅。
文學史不是編年史、不是社會政治史。它記錄著文學發展的歷史,同樣有自身形成的標準和獨特超越的地方,不一定完全跟政治的發展亦步亦趨。在中國乃至在世界,都沒有不受政治約束的文學,但當前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要盡可能考慮周全和客觀,不能把所有因素的形成都歸結于政治的變動和影響。文學創作是復雜的,它要依靠復雜而實際的國家歷史情態,并非與建立新政權的時間亦步亦趨。概念里面特別強調“民國”的作用,有故意夸大國體和政體對文學影響的潛在傾向了。這便重走了舊有文學史敘述的套路,即說到民國往往是政府與國家混為一談。[10]筆者對作為特定社會文化結構產物的“機制”在民國形成的觀點毫無異議,但有關機制的“醞釀”問題,實在值得作進一步的思考。
這里也牽涉到討論“民國機制”時空影響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民國機制”在當時的影響是否如李怡等學者所估計的效果那樣明顯呢,它是否真的能成為主導性和全局性因素呢?從定義出發,李怡極其強調結構性力量包括社會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民國經濟方式的保證與限制,也有民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圍合,甚至還包括在民國社會形成的獨特的精神導向。實際上,能影響現代文學的主導文化與民國政權的關系并不是特別密切,反而與世界文學發生發展的背景聯系在一起。民國到底在中國存在的實質性影響有多大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小農經濟實際上還是處于根本地位,何以能說明民國私有制經濟在全國已經扎下根來呢?實際上,民國只是作為一個政權符號存在著。它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松散體,何以能在經濟、文化上對大陸乃至臺港澳等地區產生實質性影響呢?文學真的能受到民國經濟的保證與限制嗎?政治和文化氛圍能決定文學的發展特征嗎?不否認民國政府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但民國政府根本沒辦法統籌全國各地區的發展。從1912年至1949年,內亂和外侵一直困擾著中國,在民國時期逐步形成的各種結構性力量基本都處于畸形狀態,要想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談何容易?在這樣的情況下,本身在畸形狀態下成長起來的民國文學機制又有什么實力充當“老大”呢?研究者對其內部力量作過相關討論,他們認為:“這種機制是否全面地影響了新文學作家,作家的主體心理結構是否又固化到文本之中,文學文本與民國機制是否就一定有某種聯系,這是值得思考的一系列問題”[11]。客觀來說,民國文學機制不能“滋生”、只能“影響”其他機制,與其他機制共同構成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全景圖。同時,它與其他文學機制,特別是延安文學機制做到的只能是對話和相互影響,并不能產生決定作用,最根本的是二者經濟基礎并不相同,而且支撐它們后面的結構性力量也不一樣。因此,筆者還是贊同“民國機制”作為新的方法論和視角探討結構性力量的相互作用及其解決具體的文學問題,這樣才能突顯民國性。
從對以上四點疑惑的省思當中,筆者隱約體會到李怡研究的概念應是民國文學機制,并且意識到了“民國”與“中國現代”的同構關系,支撐民國文學機制背后的理論基礎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語境,“醞釀”研究對象的時期應在晚清(具體時間仍需探索),它作用的時空范圍是1912年清王朝覆滅后文學機制所能影響和對話范圍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因此,如果說這個概念具有極大的包容性,那也只是包容在民國文學機制作用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現代”的本質仍是我們需要繼續研究的話題。由于李怡并沒有對文學史觀和價值評判標準作出一個完整的解析,所以對于民國機制“能包容錯綜復雜的文學現象”這個命題仍受質疑。另外,不確立好這兩個本體,即使李怡等學者在方法論上貢獻了許多重大性的成果,那還是不能消除筆者提到的所有疑惑,并不能對概念后面的本質意義作出更進一步的闡釋。因此,所謂突破性的實質意義也只能打上問號了。長期下去,如何讓“民國機制”安身立命也必會成為我們所擔憂的問題。
反思“民國機制”作為新的敘述范式所反映出來的種種現象,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出其仍需繼續改進的地方。近年來,民國文學研究正面臨著新的機遇,“民國機制”的形成有利于“民國文學”研究往縱深發展以及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本土規律。如果我們能在命名和定義上做得更為嚴謹一些,那么它將會產生更大的學術價值。事實上,“民國機制”并沒有消亡,在臺灣仍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兩岸學者在這方面必將實現重大的開拓與合作。
參考文獻:
[1] 周維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民國視野”述評[J].文藝爭鳴,2012(5):64.
[2] 張福貴.從“現代文學”到“民國文學”:再談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問題[J].文藝爭鳴,2011(13):69.
[3] 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轉型[J].南方文壇,2003(1):5.
[4] 李怡.從歷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機制的發掘:我們怎樣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民國”意義[J].文藝爭鳴,2011(13):62.
[5] 李怡,周維東.文學的“民國機制”答問[J].文藝爭鳴,2012(3).
[6] 李怡.“民國文學”與“民國機制”三個追問[J].理論學刊,2013(5):114.
[7] 王學東.“民國文學”的理論維度及其文學史編寫[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4):151.
[8] 李怡,李直飛.是“本土化”問題還是“主體性”問題?——兼談“民國機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158.
[9] 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J].中國社會科學,2012(2):175.
[10]秦弓.現代文學的歷史還原與民國史視角[J].湖南社會科學,2010(1):136.
[11]王澤龍,王海燕.對話:關于“民國文學機制”與現代文學研究[J].江漢學術,201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