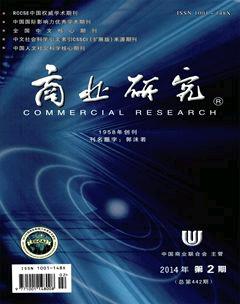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意愿分析
李海廷
摘要:本文運用實驗法對危機情境下企業社會責任(CSR)與消費者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危機嚴重性感知對CSR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危機嚴重性感知水平越高,購買意愿對社會責任水平的敏感性下降越快;消費者社會責任支持度與社會責任水平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高社會責任支持者對CSR更加敏感,顧客認同在CSR與消費者購買意愿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購買意愿;危機嚴重性感知;顧客認同
中圖分類號:F7135 文獻標識碼:A
從消費者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社會責任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由于營銷領域中發生的危機事件有日益增強的趨勢,企業以前的社會責任表現會為其提供免于危機傷害的“保護傘”或減緩危機傷害的“緩沖劑”作用。因此,若能驗證危機情境下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正面效應以及其存在條件,無疑會為企業主動實施社會責任活動提供了理論支持。
一、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
許多學者就企業社會責任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盡管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但得出的結論基本類似,即高水平或積極的社會責任會帶來高的購買意愿。如Mohr & Webb(2005)通過設置消費情景,研究了兩類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公益事業和環境保護)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會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產生積極影響;相比于高水平的社會責任行為,低水平社會責任行為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意向[1]。實際情況也佐證了理論研究結果,如在2002年進行的一項針對美國消費者的調查結果顯示,89%的被調查者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非常重要,并表示會通過轉換品牌、拒絕購買企業股票,懲罰那些被認為不負責任的企業(Blumenthal & Bergstrom,2003)[2]。
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也類似,如謝佩洪、周祖城(2009)在研究中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會對消費者的企業認同、企業聲譽,以及購買意愿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而且還通過企業聲譽、企業認同等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產生間接影響[3]。本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在危機情境下同樣適用,企業發生危機前的社會責任表現會留給消費者或好或壞的印象。由于這些社會責任表現是構成消費者企業信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危機發生后,消費者會根據以前信念來決定其后續行為,由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設:
H1: 在危機情境下,企業社會責任水平對購買意愿產生正向影響;相比于消極社會責任活動,若企業采取積極社會責任活動,會產生較高的購買意愿。
(二)危機嚴重性感知、社會責任與購買意愿
產品傷害風險管理方面的相關研究,發現良好的企業聲譽可以對處于危機中的企業起到保護作用,即良好的企業聲譽能夠降低消費者的風險感知水平,減緩消費者購買意向的下降(Siomkos & Kurzbard,1994)[4]。由此可以推測作為企業形象、企業聲譽構成部分的企業社會責任,也能對危機中的企業起到保護作用,減緩甚至消除危機對企業的不良影響。
隨著顧客對危機嚴重性感知的不同,顧客的反應(心理反應和行為反應)也會呈現出差異性。當消費者認為危機不嚴重時可能會原諒企業的過失,而當消費者意識到危機非常嚴重,甚至超過消費者所接受的心理底線時,無論以前企業表現如何,消費者很有可能無法原諒企業的過失。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危機嚴重性這一變量,如Brown & Beltramini(1989)在對服務產品的研究中發現,即服務失敗嚴重性越大,則顧客抱怨傾向就越大,負面口碑也越強[5]。Hoffman et al.(1995)在實證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即服務失敗嚴重程度與服務補救成功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服務失敗程度越嚴重,則補救成功率就越低[6],由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設:
H2: 危機嚴重性感知對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與消費者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即相對于低危機嚴重性感知,消費者的高危機嚴重性感知會削弱社會責任水平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
(三)社會責任支持、社會責任與購買意愿
消費者自身特征會對企業實施社會責任活動的效果產生很大影響,由于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認識差異很大,這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看問題視角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些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能主動承擔其社會責任,而有些消費者則不能;另一方面,對企業應否承擔社會責任看法也各異。如Webb & Mohr(1998)在研究中提到一些消費者,對企業將一定營業額捐獻給非盈利組織或慈善事業的做法持保留態度[7]。社會責任意識強的消費者,在個人消費過程中會更加關注整個社會的福利、環境保護、社會資源保護等問題,同時對提供產品的企業在道德方面的問題(如是否違法雇傭童工、工人權益是否得到保障等)也會予以關注。
Sen & Bhattacharya(2001)通過實驗法證實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評價具有積極的影響,與企業正面的社會責任信息相比,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更易受到負面社會責任信息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關系會受到消費者對社會責任活動支持度的調節作用[8]。Bhattacharya & Sen(2004)認為匹配度和社會責任支持度對消費者反應會產生交互影響,只有當消費者支持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且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有高的匹配度,并且企業產品質量高,而消費者又不會為社會責任活動額外支付溢價時,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行為之間的關系才能呈正相關關系[9],由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設:
H3: 社會責任支持度對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與消費者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高社會責任支持度消費者相對于低社會責任支持度消費者而言,社會責任水平與購買意愿之間關系較強。
H4: 社會責任支持與危機嚴重性感知二者交互作用,對社會責任水平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作用。
(四)顧客認同、社會責任與購買意愿
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牢固關系部分來源于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正是基于消費者自我概念和社會身份而產生的,它們驅使消費者與特定的組織發展出一種關聯性(Bergami & Bagozzi,2000)[10]。以往認同理論主要應用于組織成員與組織之間關系的研究,但正如Scott & Lane(2000)所指出的,不只是組織成員有尋求認同感的需求,一些不隸屬于組織的人員也有對組織產生認同感的需求[11],認同理論也可以被應用到消費者與企業之間關系的研究上。學者們把消費者感覺到的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或者說消費者感知到的自己特征和企業特征之間的契合程度稱為顧客認同(Sen & Bhattacharya,2001)[8]。顧客認同感可能會驅使消費者作出有利于企業的行為,如忠誠、口碑等,即這些消費者反應變量可以視為顧客認同的結果變量。
顧客認同也是消費者社會責任反應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和變量,消費者從對企業社會責任聯想的一致性感知中獲得了自我定義需求的滿足,當消費者認為他對企業的認同感具有持續性、獨特性,并且能夠提高自己的自尊、彰顯自己個性,或者通過購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的產品能提升自己形象時,更有可能與企業取得認同。如Sen & Bhattacharya(2001)認為在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企業評價的正向影響中,顧客認同起到中介作用[8],這種認同感有助于滿足消費者自我定義的需求。Bhattacharya & Sen(2003)提出了一個關于“消費者-顧客認同”的概念模型,認為消費者對顧客認同水平越高,越容易對企業產生有利的消費者反應,如高忠誠度、高產品試用率與產品推介,以及好的口碑等[12]。Marin & Ruiz(2007)提出了一個企業認同吸引力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支持會對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契合度產生正面影響,進而對企業認同吸引力產生影響[13]。在Maignan & Ferrell(2004)提出的概念模型中,顧客認同感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一個重要結果變量,并且顧客認同還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其他利益相關者行為變量中起到中介作用[14],由上提出以下假設:
H5: 企業社會責任水平對顧客認同產生正向影響,相比于消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水平,積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水平會增強消費者的顧客認同感。
H6: 社會責任支持度對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與顧客認同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相對于低社會責任支持度而言,高社會責任支持度會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與顧客認同之間的關系。
H7: 顧客認同對消費者購買意愿具有正向影響作用;顧客認同度越高,消費者購買意愿就越高,反之顧客認同度越低,消費者購買意愿就越低。
H8: 顧客認同在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意愿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五)危機嚴重性感知、顧客認同與購買意愿
Bhattacharya & Sen(2003)指出在一定承受范圍內,消費者對企業認同水平越高,其對企業負面信息方面的抵御能力就越強[12]。但當超出消費者承受范圍時,消費者對顧客認同水平越高,消費者對企業負面信息的反應會越強烈和持久,尤其是當這些負面信息與認同感有關時。
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感能為企業帶來利益,但也是一把雙刃劍,也能為企業帶來潛在的危險。Bhattacharya & Elsbach(2002)發現當個體認為其個性與組織特性發生沖突時,會導致個體自我概念與組織自我概念相分離,進而產生組織失調[15]。可以推斷當危機超出一定程度時,消費者很有可能與危機發生企業也產生“分離”現象。顧客認同感的這種雙刃劍性質還表現在對企業要求不斷升級上,Dutton & Dukerich(1991)認為當外部變化威脅到產生認同感的消費者的自我意識時,他們可能會抵制企業,并游說企業與其最初的身份保持一致[16]。通常來說企業為了取得消費者的認同,通過使消費者融入組織,企業會不知不覺地提高了消費者的影響力。有時候消費者之間的認同感要超過對組織的認同感,這時消費者會聯合起來向企業施加壓力。總之,這些行為都可能導致消費者對企業擁有更強大的影響力,進而會減少企業的自主權利。因此,基于同樣的道理和邏輯,當企業危機嚴重性增加,甚至超出消費者可接受的范圍時,社會責任支持度對購買意愿的正面影響也會發生逆轉變化,由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設:
H9: 危機嚴重性感知對顧客認同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高危機嚴重性感知消費者相對于低危機嚴重性感知消費者而言,即使顧客認同感強,社會責任水平與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也較弱。
綜合以上假設,本研究提出以下模型,如圖1所示。
二、研究設計
(一)實驗設計
為了驗證上述假設,采用2(企業社會責任水平)×2(危機嚴重程度)二因素被試間隨機實驗設計來收集調研數據。其中企業社會責任包括積極的企業社會責任和消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所謂積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積極主動承擔本身義務之外的社會責任行為;消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所從事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自身身份、地位不相符,低于公眾的期望,甚至未履行基本的社會義務。另外,危機嚴重程度包括危機嚴重程度高和危機嚴重程度低。為了鑒別社會責任水平是否真正對因變量產生影響,設計了控制組,針對控制組的問卷不涉及任何企業社會責任信息。
(二)實驗情境
實驗情境的設計根據Mohr & Webb(2005)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消費者去運動品商店購買運動鞋這一實驗情境進行改編[1],考慮到若采用現實中存在的企業名稱或品牌,消費者很可能會受以前所接受信息的影響,從而會影響到調研數據的質量,因此采用虛擬企業名稱。實驗情境為虛擬被試去一家運動品專賣店購買運動鞋,情境中企業社會責任內容選擇環境保護、贊助慈善事業和員工社區公益活動三項;對企業社會責任水平的操控通過虛擬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排行榜”中的排名來控制;危機事件嚴重性程度通過產品質量事件來控制,高危機事件用運動鞋核心部件出問題來表述,低危機事件用運動鞋鞋幫開膠事件來表述。
(三)實驗過程
在實驗研究中,學生樣本因其同質性可保證實驗結果較少受意外因素干擾而經常被選為被試對象。本研究以高校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在進行正式實驗之前進行預實驗,以檢測實驗情境的設計是否合理。共有27名大學生參加了預實驗,發現被試對企業社會責任兩個水平的感知差異顯著(MCSR積極=621,MCSR消極=302,p<001);被試對危機嚴重性感知也表現出顯著差異(M危機高=584,M危機低=326,p<001)。這說明實驗條件操縱成功,可以進行正式實驗。
在進行正式實驗時,將閱讀材料分兩部分讓被試閱讀。首先讓被試閱讀情境材料(不包含A企業運動鞋出問題一段),然后讓被試填寫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支持度、顧客認同等變量的測項,接下來再讓被試閱讀關于A企業運動鞋產品出問題的材料,然后再讓被試填寫關于危機嚴重性、消費者購買意愿等變量的測項。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模型的邏輯性,顧客認同測項必須在危機材料展示之前填寫,最后共有240名大學生參加正式實驗。
(四)變量測量
量表構成如表1所示,采用7點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分,“1”代表“完全不贊同”,“7”代表“完全贊同”。
三、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與主效應分析
本文運用三因素被試間方差分析(three-way between-subjects ANOVA)對調研數據進行分析,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相比于危機嚴重性程度低時,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購買意愿較低(M危機高=315;M危機低=380),可以初步判斷消費者對危機嚴重性程度的感知會對購買意愿產生影響。當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消費者購買意愿會下降。在社會責任水平作為主要自變量情境下,總體上看對社會責任支持度高的消費者購買意愿要相對較高(MCSR支持高=390;MCSR支持低=312),但在社會責任水平積極和消極情境下差異還是很大。當社會責任水平積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購買意愿要遠高于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M CSR支持高=507;MCSR支持低=369);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與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在購買意愿上并無差異(M CSR支持高=254;MCSR支持低=254)。也就是說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即使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但因為企業并未在社會責任行為上有良好表現,也并不會對消費者的實際購買意愿產生影響。從總體上看,無論危機嚴重性程度、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低,總體上看,社會責任水平積極組消費者相對于消極組消費者表現出更高的購買意愿(MCSR積極=434;MCSR消極=254)。
(三)實驗過程
在實驗研究中,學生樣本因其同質性可保證實驗結果較少受意外因素干擾而經常被選為被試對象。本研究以高校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在進行正式實驗之前進行預實驗,以檢測實驗情境的設計是否合理。共有27名大學生參加了預實驗,發現被試對企業社會責任兩個水平的感知差異顯著(MCSR積極=621,MCSR消極=302,p<001);被試對危機嚴重性感知也表現出顯著差異(M危機高=584,M危機低=326,p<001)。這說明實驗條件操縱成功,可以進行正式實驗。
在進行正式實驗時,將閱讀材料分兩部分讓被試閱讀。首先讓被試閱讀情境材料(不包含A企業運動鞋出問題一段),然后讓被試填寫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支持度、顧客認同等變量的測項,接下來再讓被試閱讀關于A企業運動鞋產品出問題的材料,然后再讓被試填寫關于危機嚴重性、消費者購買意愿等變量的測項。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模型的邏輯性,顧客認同測項必須在危機材料展示之前填寫,最后共有240名大學生參加正式實驗。
(四)變量測量
量表構成如表1所示,采用7點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分,“1”代表“完全不贊同”,“7”代表“完全贊同”。
三、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與主效應分析
本文運用三因素被試間方差分析(three-way between-subjects ANOVA)對調研數據進行分析,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相比于危機嚴重性程度低時,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購買意愿較低(M危機高=315;M危機低=380),可以初步判斷消費者對危機嚴重性程度的感知會對購買意愿產生影響。當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消費者購買意愿會下降。在社會責任水平作為主要自變量情境下,總體上看對社會責任支持度高的消費者購買意愿要相對較高(MCSR支持高=390;MCSR支持低=312),但在社會責任水平積極和消極情境下差異還是很大。當社會責任水平積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購買意愿要遠高于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M CSR支持高=507;MCSR支持低=369);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與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在購買意愿上并無差異(M CSR支持高=254;MCSR支持低=254)。也就是說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即使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但因為企業并未在社會責任行為上有良好表現,也并不會對消費者的實際購買意愿產生影響。從總體上看,無論危機嚴重性程度、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低,總體上看,社會責任水平積極組消費者相對于消極組消費者表現出更高的購買意愿(MCSR積極=434;MCSR消極=254)。
(三)實驗過程
在實驗研究中,學生樣本因其同質性可保證實驗結果較少受意外因素干擾而經常被選為被試對象。本研究以高校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在進行正式實驗之前進行預實驗,以檢測實驗情境的設計是否合理。共有27名大學生參加了預實驗,發現被試對企業社會責任兩個水平的感知差異顯著(MCSR積極=621,MCSR消極=302,p<001);被試對危機嚴重性感知也表現出顯著差異(M危機高=584,M危機低=326,p<001)。這說明實驗條件操縱成功,可以進行正式實驗。
在進行正式實驗時,將閱讀材料分兩部分讓被試閱讀。首先讓被試閱讀情境材料(不包含A企業運動鞋出問題一段),然后讓被試填寫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支持度、顧客認同等變量的測項,接下來再讓被試閱讀關于A企業運動鞋產品出問題的材料,然后再讓被試填寫關于危機嚴重性、消費者購買意愿等變量的測項。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模型的邏輯性,顧客認同測項必須在危機材料展示之前填寫,最后共有240名大學生參加正式實驗。
(四)變量測量
量表構成如表1所示,采用7點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分,“1”代表“完全不贊同”,“7”代表“完全贊同”。
三、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與主效應分析
本文運用三因素被試間方差分析(three-way between-subjects ANOVA)對調研數據進行分析,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相比于危機嚴重性程度低時,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購買意愿較低(M危機高=315;M危機低=380),可以初步判斷消費者對危機嚴重性程度的感知會對購買意愿產生影響。當危機嚴重性程度高時,消費者購買意愿會下降。在社會責任水平作為主要自變量情境下,總體上看對社會責任支持度高的消費者購買意愿要相對較高(MCSR支持高=390;MCSR支持低=312),但在社會責任水平積極和消極情境下差異還是很大。當社會責任水平積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購買意愿要遠高于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M CSR支持高=507;MCSR支持低=369);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高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與低社會責任支持消費者在購買意愿上并無差異(M CSR支持高=254;MCSR支持低=254)。也就是說當社會責任水平消極時,即使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但因為企業并未在社會責任行為上有良好表現,也并不會對消費者的實際購買意愿產生影響。從總體上看,無論危機嚴重性程度、社會責任支持度高低,總體上看,社會責任水平積極組消費者相對于消極組消費者表現出更高的購買意愿(MCSR積極=434;MCSR消極=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