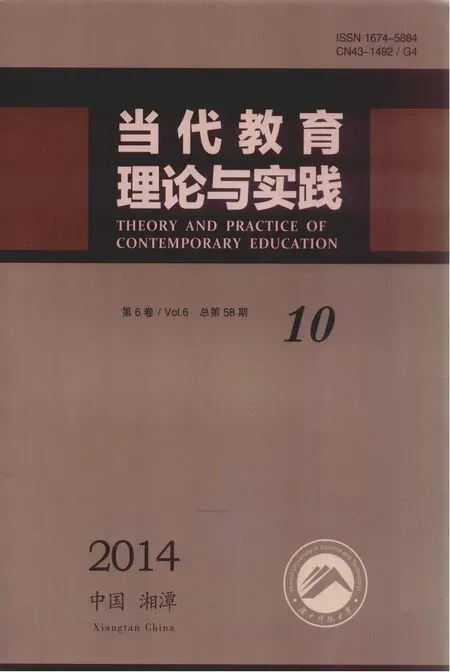汪曾祺戲劇研究綜述
李 婷,劉郁琪
(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汪曾祺一直以小說家和散文家的身份聞名于現當代文學界,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專業戲劇創作家。在四十幾年的戲劇創作生涯中,汪曾祺留下了12部精彩的戲劇作品(很多和他人合作的作品沒有署其名,還有幾部沒有本子保存)。
汪曾祺一直以“兩棲類”作家自居——小說家和戲劇編劇,可見在他心里,戲劇同小說一樣,都占據著重要地位。然而就筆者所搜集到的資料來看,相比于他的小說和散文研究,目前國內外關于其戲劇的專業性研究很不充分,而且呈極不平衡的面貌。首先,汪曾祺的小說和散文很富盛名,掩蓋了他的戲劇才華。而他也不是像曹禺、夏衍、郭沫若等這樣的戲劇名家,研究者們很少專注其戲劇,故研究成果總量不多,只有100篇左右。其次,汪曾祺主筆的《沙家浜》是“文革”期間的樣板戲之一,影響力巨大,具有經典文本的地位。所以研究者都專注于《沙家浜》(96%的論文以《沙家浜》為研究對象),使得其戲劇研究呈現極不平衡現象。2010年以來,漸漸有人注意到汪曾祺戲劇的創作個性,或從整體探究或從具體作品分析,可惜這樣的論文只有4篇。本文僅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對有關其戲劇創作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評述。
1
京劇《沙家浜》的劇本創作與修改前后經歷整整七年。1963年11月,汪曾祺作為主要執筆人加入滬劇《蘆蕩火種》改編創作組,開始一段風波迭起的創作歷程。1964年,改編后的《蘆蕩火種》在全國上演幾百場,取得巨大成功,被稱為繼《紅燈記》之后京劇革命化的又一個樣板。后來江青親自插手創作組的修改與論證,最后終于在1970年《紅旗》雜志第六期發表定稿。至此,《沙家浜》作為“樣板戲”成為文革期間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食糧。
從1960年代起,《沙家浜》就一直是汪曾祺戲劇研究的重點,相關研究按發表時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1965年,《戲劇報》首發5篇文章,集中探討《沙家浜》如何踐行當時的文藝政策,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京劇<沙家浜>評論集》收集發表在各大刊物上的37篇相關文章;其次是1993年至今,《沙家浜》研究的多元化階段,研究者們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剖析。在這兩個階段中間(1966~1992)是長達26年的研究空白期,筆者未搜集到相關文學研究。
1965年,《戲劇報》連發5篇文章評論《沙家浜》,江之水從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指出《沙家浜》對滬劇《蘆蕩火種》的改造是相當成功的:它“鮮明地突出了一條思想紅線,這便是戰無不勝的毛主席的武裝斗爭思想”[1]。第五期還以新聞稿的方式報道了“京劇革命化的又一個樣板《沙家浜》在上海受到熱烈歡迎”這一事件(《京劇革命化的又一個樣板<沙家浜>在上海受到熱烈歡迎》,《戲劇報》,196505)。同時《蘆蕩火種》的原創者——上海市人民滬劇團提出要學習北京京劇團的革命精神[2]。李希凡就人物關系、角色形象、場幕設置和劇作主題等方面高度贊揚了《沙家浜》用戲劇表演的方式踐行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提出“《沙家浜》再創造的成功,是在于它仍以阿慶嫂和這十八個人的活動為中心,將突出武裝斗爭作用的思想,延伸到整個戲劇情節里去。”[3]北京京劇團作為創作集體還寫了一篇文章——《<沙家浜>修改過程中的一些體會》,主要從政治與藝術的關系、生活與傳統的關系兩個方面談論劇作改編中遇到的問題,并且提出最終以在平衡情況下的政治統帥藝術,生活戰勝傳統的標準解決[4]。
《京劇<沙家浜>評論集》選出了1965年之前報刊上發表的部分相關文章,編成論文集出版。所選文章分為兩部分,一是三篇《北京日報》評論《蘆蕩火種》的文章,第二部分是評論《沙家浜》的文章,主要有“關于向《沙家浜》學習的號召和綜合評論;關于《沙家浜》劇本的文學分析;關于《沙家浜》表演藝術(包括武打)的評論和體會;對《沙家浜》的音樂唱腔、舞臺美術的研究;工農兵群眾對《沙家浜》的評論;最后是《沙家浜》的修改過程和創作體會”[5],評論集里包括了《戲劇報》所發5篇。這些文章雖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這部劇作(比較學、語境論、歷史考證和創作談等),但實際內容都指向了同一個主題:贊揚《沙家浜》是京劇革命的勝利成果。與滬劇《蘆蕩火種》相比,它更切實地踐行了毛澤東文藝思想:“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要突出武裝斗爭的作用,強調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等。《沙家浜》在泛政治化環境里問世,劇作本身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銘文,同時期的評論文章帶上頗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966~1992年間文學評論界未有分析《沙家浜》的論文,原因是復雜的。從1965年到1977年,文藝界由于“文革”的特殊政治文化氛圍,很少有專業的文學評論文章發表。而且作為江青控制文化戰線的一個成果,《沙家浜》被尊為“樣板戲”,其性質已定,更加沒有太多人再對此有所評述。同時期被定為樣板戲的《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等在這一時期內也很少成為評論家的研究對象。而在1977年到1992年間,“文革”時占主導地位的紅色“樣板戲”影響式微,大眾、文藝界對江青一伙的政治工具甚為反感,不愿意將其放到文學討論對象的位置。隨著1990年代以來學術界逐漸以一種相對客觀與理性的態度重新梳理文革文學,人們又重新開始了對《沙家浜》的研究。
2
1993年以后的《沙家浜》研究逐漸走向多元化局面。評論家們已經不再集中在它的泛政治意識形態性,而是從各個角度、運用多種批評方法對其進行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五種類型:歷史考證型、形式分析型、比較型、語境分析型和人學批評型等。其中以歷史考證為主,據統計有29篇,占1993年以后資料的50%。
對《沙家浜》進行歷史考證的研究數量相對比較多。而且從論文發表時間來看,其歷時時間也非常長,從1993年到2013年,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有數篇相關論文出現。1994年,黃烽將軍回憶自己曾參加的軍事活動,指出京劇《沙家浜》根據一定歷史事件改編,并在其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升華(《黃烽將軍談京劇<沙家浜>》,福建黨史月刊199404)。1997年,田京輝試圖通過訪問汪曾祺和楊毓珉同志還原《沙家浜》著作權糾紛事件的始末[6]。2005年,袁成亮發表《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誕生記》(黨史縱覽,200502)介紹了《沙家浜》的前世今生。2006年,陳立對京劇《沙家浜》的人物原型——四位新四軍傷病員的事跡進行調查[7]。2009年,柴建才從劇作者生活歷程的角度整理了汪曾祺對“樣板戲”的復雜情結[8]。2013年,汪曾祺研究會會長陸建華又發一文,以人物傳記的方式重新梳理汪曾祺參加《沙家浜》創作的前后過程[9]。
由于《沙家浜》本身復雜的歷史屬性,對它的歷史考證研究可能還將繼續下去。但是研究者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研究層次,而應深入挖掘、多向拓展,從多個角度切入劇作文本。事實上評論界也沒有僅停留在此。
首先,人們注意到,作為1960年代的現代京劇代表,《沙家浜》在藝術形式上,除繼承我國古典戲曲優秀傳統外,在唱詞唱腔、音樂設計等方面有很多創新之處。顧鑫浩就從藝術表現形式上將《沙家浜》與傳統戲曲進行對比,尋找其形式上的創新之處,“對樣板戲的藝術性進行重評”[10]。盧愛華對“智斗”一場中三人對唱唱段的音樂進行了專業分析[11]。
其次,也有評論者從比較學的視角研究不同文本、不同文類的四個《沙家浜》(滬劇《蘆蕩火種》、京劇《沙家浜》、薛榮的小說《沙家浜》以及電視劇《沙家浜》)。如宋光祖在《開不敗的蘆花——滬劇<蘆蕩火種>與<沙家浜>對讀》(《東方藝術》,199301)中“具體地分析滬劇《蘆蕩火種》在設計奇特情節、通過斗智塑造能人(阿慶嫂、陳天明與刁德一)等所取得的高度藝術成就”12,同時也提出《沙家浜》的改編“在中心人物布局的角度上,硬將中心人物由阿慶嫂改為郭建光,使‘改編工作漸入誤區’,沒有抓住滬劇原作的主旨,‘豈不可嘆!’”[12]這是將同文類的劇本進行對比。還有張海濤從性別視角出發比較戲劇《沙家浜》和小說《沙家浜》中的“阿慶嫂”形象,“通過對‘阿慶嫂’性別符碼的解讀來探討隱身其后的現代性認同的變化”[13],這種變化表現為指向公共空間的現代性認同轉換為指向私人空間的現代性認同。趙勇則企圖通過考察電視劇和戲劇形態的《沙家浜》,探究紅色經典劇改編的困境[14]。這兩篇是將同一故事母題的不同文類文本進行比較。
再次,這個時期對《沙家浜》的意識形態研究已經和1965年完全不同。不再是一邊倒地歌頌其踐行毛澤東文藝政策,而是冷靜客觀地分析《沙家浜》本身的意識形態銘文,或者考察在結束輝煌時期以后,這部紅色經典戲劇如何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保持生命力,新時代的觀眾如何看待它、接受它等問題。惠雁冰就指出“樣板戲”《沙家浜》是一個高度符號化的意義單向的政治文化隱喻系統[15]。劉中望以現象與接受美學理論解析了由于不同時期讀者的審美經驗、期待視野、接受方式等差異引起的對文本閱讀評價不一的情況[16]。
最后,許多評論者都注意到《沙家浜》對人性的殘忍閹割這個問題,并在論文中有只言片語的體現。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專論其人性的文章只有一篇,即陳婧的《終極關懷式微下的人性追問——從人道主義看樣板戲<沙家浜>》(景德鎮高專學報,201304)。文章具體批評《沙家浜》在“三突出”文藝原則的規范下,對人物人性的某些部分進行毀滅性處理,導致其在刻畫人物上有缺憾。
評論界對《沙家浜》的研究可謂歷時時間長、涉及角度廣。從現在的研究趨勢來看,對這個紅色經典劇本的研究將不會停止。而且,隨著評論者的文化歷史背景的變化、理論閱讀視野的更新,這種研究的深度將會更加拓展下去。
3
盡管研究內容豐富,但由于《沙家浜》是集體創作,即便汪曾祺是主要執筆人,在各家的解讀中還是很難見到對劇作家創作個性的分析。而且大量歷史考證型論文也使得對《沙家浜》的研究沒有很好地形成學理化局面。從另一方面講,不管《沙家浜》在汪曾祺的戲劇創作中占據怎樣重要的地位,這也只是他四十多年戲劇創作生涯中的一個作品。而且他不但寫戲劇,還有自覺的理論意識,只不過這些被他的小說散文的光輝所掩蓋了。近年來,隨著對汪曾祺的研究向深度擴展,評論界逐漸有人將目光投向了他的戲劇創作,在小說和散文外,向世人打開了汪曾祺研究的另一扇窗。然而,這扇窗還只是打開了一個小角。與《沙家浜》相比,這方面的研究還相當少,只有寥寥4篇,且最早的一篇也是直到2010年才出現。這4篇論文可以分成兩種,一是在整體研究型,一是具體作品分析型。
其中有三篇是整體研究。最早的是席建彬的文體研究。他關注到到汪曾祺的小說與戲劇創作間的互通關系。他認為:“關于小說的抒情觀念仍然以一種歷史慣性影響到戲劇創作,成為影響后者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這構成了其戲劇創作與小說寫作的互文性,使得戲劇創作成為作家小說觀念的跨文體實現,在思想內容、敘事方式、語言風格等文本形態方面表現出明顯的抒情特質,個中的糾著與縫隙,客觀上使得作家的戲劇創作成為某種跨文體性的復合物”[17]。席建彬的這篇論文創造性地論述了汪曾祺“兩棲”創作之間的互文關系,指出汪曾祺戲劇之所以現代性和文學性強,很大程度在于他的小說創作慣性:他將現代性的文學技巧與思想融匯進中國傳統戲曲故事的編排中,把戲劇“變成一種現代藝術”;他時刻不忘記文學性的追求,企圖糾正傳統戲曲文學性不強的弱點,在戲劇中書寫人生詩情。同時席建彬也指出汪曾祺在強調詩意文學的同時有消解戲劇敘事性的情況,導致“人生詩情的介入在賦予文本較強文學色彩的同時也就改變了戲劇的敘事結構等戲劇性空間,削弱了戲劇傳播的世俗基礎”[17]。汪曾祺的小說被稱為“詩化小說”“散文化小說”,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戲劇也可以被稱為“小說化戲劇”。
第二篇是汪曾祺戲劇觀研究。2006年,段春娟將汪曾祺寫的有關戲劇的文章整理編成《汪曾祺說戲》一書,基本上囊括了汪曾祺的戲劇創作理念。2010年,施小瓊通過對汪曾祺的戲劇作品及其戲劇理論的總結,寫出了《略論汪曾祺戲劇創作觀》(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009)。該文主要從對“樣板戲”的反思、對京劇危機和出路的思考以及劇本創作等方面來探析汪曾祺的戲劇創作觀。施文指出了汪曾祺的一些核心思想:辯證地看待文革期間的“樣板戲”;認為京劇的出路在于抓住年輕觀眾、融入現代化思想和技巧;試圖打通戲劇、小說和詩歌等文體的界限;注重戲劇的文學性:“決定一個劇種的興衰的,首先是它的文學性,而不是唱念做打”[18]等等。
第三篇是對汪曾祺戲劇現代性特征的研究。盧軍認為汪曾祺的戲劇創作是“把戲劇變成一種現代藝術的嘗試”,他以汪的幾部雖改自中國傳統舊戲(或小說)卻有現代意蘊的戲劇(《范進中舉》《一匹布》《大劈棺》《一捧雪》等)為例,分析其在關注現代社會問題、提高戲劇的思想性、塑造圓型性格人物以及創新曲辭格律等方面做出的努力。最后得出結論:“汪曾祺的現代戲劇理想,是融會了東西方美學思想的。汪曾祺的戲劇創作正體現了他的現代戲劇觀念”[19]。
具體作品分析型的論文只有一篇,那就是柯玲的《梅開二度香飄千秋——談汪曾祺對〈范進中舉〉的改編》。柯玲認為,汪曾祺清醒地把握住小說與戲劇這兩個文類之間的血緣關系,指出“汪曾祺對《范進中舉》的改編主要通過增加、改動、調整等方法實現對原作的二次創造”[20]。雖然這篇論文是對個例的分析,卻分析了汪曾祺改編戲劇的常用手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
這4篇論文深入剖析了汪曾祺戲劇創作的個性特征,在《沙家浜》外打開了汪曾祺戲劇研究的全新視野。打開了這視野后,我們可以進一步開拓其空間,豐富其戲劇研究內容,進而為整個汪曾祺研究充實材料。
[1]江之水.從《蘆蕩火種》到《沙家浜》[J].戲劇報,1965(2):33,16.
[2]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啟示·教育·鞭策——看《沙家浜》,向北京京劇團學習[J].戲劇報,1965(7):36-37.
[3]李希凡.毛澤東思想照亮了革命現代戲的創作——評京劇《沙家浜》再創造的成就[J].戲劇報,1965(7):25-30.
[4]北京京劇團.《沙家浜》修改過程中的一些體會[J].戲劇報,1965(7):31-35.
[5]中國戲劇家協會.京劇《沙家浜》評論集[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5.
[6]田京輝.心平氣和話署名——就《沙家浜》著作權糾紛訪汪曾祺、楊毓珉同志[J].上海戲劇,1997(2):16-17.
[7]陳立.京劇《沙家浜》的創作原型——四位新四軍傷病員的事跡[J].中共黨史資料,2006(2):172-178.
[8]柴建才.試論汪曾祺與“樣板戲”的復雜情結[J].名作欣賞,2009(10):81-84.
[9]陸建華.汪曾祺與京劇《沙家浜》[J].翠苑,2013(4):4-13.
[10]顧鑫浩.評“樣板戲”《沙家浜》[J].文教資料,2009(18):174-175.
[11]盧愛華,季銀鳳.京劇《二進宮》《沙家浜》三人對唱唱段的音樂分析[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10(2):95-99.
[12]周錫山.京劇《沙家浜》對滬劇《蘆蕩火種》的侵權與改編得失[J].上海戲劇,1997(2):17-19.
[13]張海濤.現代性與性別表述的兩個空間——從戲劇《沙家浜》到小說《沙家浜》[J].戲劇文學,2012(1):80-84.
[14]趙 勇.紅色經典劇改編的困境在哪里——以《沙家浜》為例[J].社會科學輯刊,2006(6):128-145.
[15]惠雁冰.“樣板戲”:高度隱喻的政治文化符號體系——以《沙家浜》為例[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3):41-47.
[16]劉中望.“沙家浜”現象與接受美學視野[J].溫州大學學報,2005(6):42-47.
[17]席建彬.從小說到戲劇:敘事消解中的詩意跨越——汪曾祺戲劇創作論[J].中國文學研究,2010(1):116-118,127.
[18]汪曾祺.從戲劇文學角度看京劇的危機,汪曾祺說戲[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19]盧軍.把戲劇變成一種現代藝術的嘗試——論汪曾祺的戲劇創作[J].文藝爭鳴·當代百論,2013(4):155-158.
[20]柯玲.梅開二度香飄千秋——談汪曾祺對《范進中舉》的改編[J].藝術百家,2013(3):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