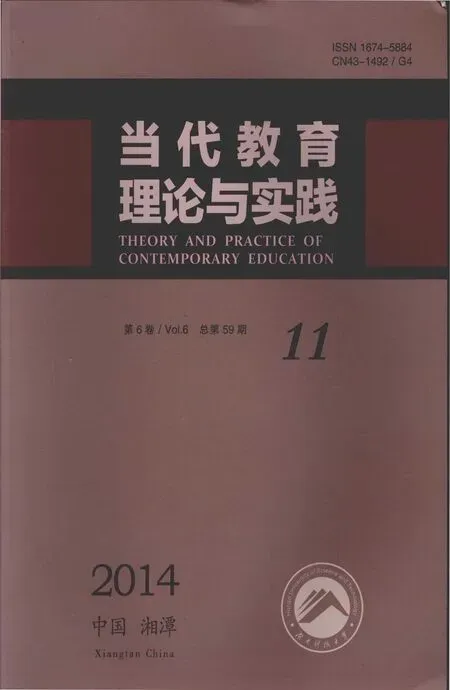論《美發簡史》中巴恩斯對自然與文明沖突的反思
余依婷
(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英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集自由撰稿人、電視評論家、作家于一身的他擁有著豐富的文學生涯。這使得他寫出了具有獨特風格的短篇小說集、散文集,還有一些評論性的文章。迄今為止,巴恩斯共著長篇10余部。其中,《福樓拜的鸚鵡》《英格蘭英格蘭》《亞瑟與喬治》3部小說均獲得2005年度布克獎提名。在這些風格多樣的小說中,巴恩斯打破傳統小說創作的一般模式,大膽嘗試多種實驗創新手法,被譽為“英國文壇的變色龍”[1]。當代著名作家馬丁·艾米斯認為與同輩作家所嘗試的各類形式的實驗相比,巴恩斯的實驗是真正屬于天賦型的,因為“他的作品總是深邃而卓爾不群”[1]。的確,巴恩斯的小說不僅以獨創的形式實驗手法著稱,而且富有深刻的哲學辯證性。
如今,這位活躍在當代英國文壇的優秀小說家的創作,受到了國內外大量學者的關注。在英國,巴恩斯被視為與馬丁·艾米斯、伊恩·麥克尤恩等文壇大腕齊名。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他對歷史、藝術、形式創新的鐘愛,他卓越的智慧與輕快的漫談風格,堪與納博科夫、卡爾維諾和昆德拉媲美”[2]。中國對朱利安·巴恩斯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近幾年來發展迅速。大部分的學者如楊金才、張和龍、羅媛等都選取了巴恩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福樓拜的鸚鵡》《亞瑟與喬治》《終結的意義》等作為研究對象,并對巴恩斯作品中的歷史與真實、時間與死亡以及后現代藝術手法這3個主題進行了探討,體現了巴恩斯作品中“既有藝術形式的創新,又有多元文化的共鳴,展示了英語文學幽默反諷的精髓”這一鮮明特點[3]。然而,目前為止,對巴恩斯的《檸檬桌子》研究極少。《美發簡史》則是屬于這部短篇小說集中的第一個短小故事。本文將從自然與文明的視角切入,通過分析故事中的自然與文明的沖突,以體現巴恩斯崇尚自然、追求自然與文明和諧統一的思想。
1 “自然代言人”格雷戈里與“文明化身”理發師
廣義上的自然是指無窮多樣的一切存在物,與宇宙、物質、存在、客觀實在等范疇同義,包括人類社會。自然還指人或事物自由發展變化,不受外界干擾。自然事物就是自然存在,不依賴人類的反應活動而獨立自在的事物。而與之對應的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也指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表現出的狀態。它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人類開始群居并出現社會分工化,人類社會雛形基本形成后開始出現的一種現象。
《美發簡史》描述了主人公格雷戈里幼年、青年以及老年三個不同時期的剪發經歷。在幼年時期,提到他喜歡以前理發店“漆了顏色的舊木頭,一圈圈色彩回轉環繞其上”而成的“旋轉彩燈柱”這類“粗俗東西”[4]。然而主人公格雷戈里喜歡的“粗俗東西”是沒有受到文明與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損害,而依舊保持著原生態模樣的東西。在故事的第一個階段,巴恩斯花了一些筆墨來描寫主人公年幼時的生理特征。無論是在主人公的青年時期還是老年時期,他在理發店都體現了其“稍稍打理一下自然”的座右銘。在短篇故事《美發簡史》中,“頭發”“陰莖”“生命”作為自然事物,以及主人公對自然的堅持與熱愛,使得格雷戈里成為了自然的代言人。
由于“頭發”的自然生長,“理發師”這個職業便應運而生。隨著文明與科技的發展,故事中的理發師,所運用的理發工具是“電動的”,美發產品是可以“改善你頭發的生長狀況”的“護發素”,這些都為理發師披上了文明的外衣。理發師在故事中所提及的“十字軍”的“結果是貴族階級的削弱,市民階級和王權的加強,以及農奴解放的開始”[5]。市民渴望自由,要求打破種種封建枷鎖,擺脫天主教會的精神壓迫。他們崇尚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禁欲主義。“如果說,中世紀后期西歐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演變,為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孕育的土壤,那么,十字軍東征就是一針催化劑,促使文藝復興運動于14世紀在意大利進發”[6]。可見,十字軍對于文藝復興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它成了歐洲中世紀文明進步的催化劑。在《美發簡史》中理發師多次向主人公提到“十字軍”是“很不錯的組織”,并建議他加入該組織。這又為理發師成為文明的化身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2 “自然代言人”與“文明化身”的沖突
文明的進步就是不斷的改造自然、打破自然,這必然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關系,打破人與自然原有的和諧。人類為了生存,不斷與自然對抗。文藝復興時期,人類確立了“人是萬物之尺度”的觀念;科學革命時期則形成了“人定勝天”的思想;工業革命時期,將物質文明發展推向了一種極致,沒有兼顧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看作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是一切價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內在價值而只有工具價值”,并且把“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關懷的范圍之外”[7]。由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存在,人們在實踐中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總是從人類的自身需要出發,忽略其它自然存在的利益從而造成了自然生態危機。而人類現在之所以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與我們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有密切的關系。“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其中的‘知識’就是指‘科學’”[8]。文藝復興以來,尤其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科學逐漸取代了宗教成為闡釋自然的主要依據,它被認為反映了自然的本質規律,是絕對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客觀真理。
然而巴恩斯受福樓拜思想影響嚴重。他指出,福樓拜是“不相信進步”的,尤其是不相信道德意義上的進步,因為他生活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是一個“愚蠢”的時代,而普法戰爭后的所謂“新時代”在福樓拜看來就“更加愚蠢”了,因為在這樣的時代,任何意義上的“進步”,都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進步,而資產階級從來都是那么可鄙,那么猥瑣,那么可氣可恨。正如在巴恩斯《包法利夫人》中的“俄麥精神”就是指“進步、理性主義、科學、欺騙”一樣,《美發簡史》中,所呈現的3個不同時期的剪發經歷,也體現了這種資產階級所崇尚和擅長的一切“俄麥精神”。在《包法利夫人》中,“牧師代表宗教正統,俄麥代表科學,包法利則代表罪愆”[9]。而在《美發簡史》中,主人公以頭發、陰莖、生命為代表成為了一個自然的整體,而美發師便是文明的化身。理發店一直便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文明社會”。代表自然的主人公將文明的化身“理發師”戲謔為“瘋子”“變態鬼”“牙醫”“園林造型師”;美發師修剪頭發這個行為譏諷為“修剪籬笆”“屠殺”;將理發店電動的“旋轉彩燈柱上的一條條鮮紅的色帶”比喻成理發師弄得顧客鮮血直流時,顧客“手臂上纏著的那條繃帶”;而“理發店的標志”則是“一只碗,用來盛你流出來的血”(《檸》:15)。這無疑都體現了作為自然代言人的主人公對文明化身的理發師的不滿。
“在當代英國文學史上,朱利安·巴恩斯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經常被相提并論,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未被人重視:他倆都對“進步”話語提出了強烈的質疑”[10]。在《福樓拜的鸚鵡》中兩位守護尸體者不顧體面地“伏在尸體上”睡著了:“他們起初只是由于某種哲學錯誤而走到一起,但很快便在共同的鼾聲中達到了深層次的統一。”[11]與之相仿的是,在《美發簡史》的第一部分,巴恩斯毫不避諱地談及到主人公年幼時裸泳的情景。對游泳池里男性的生殖器官的描寫時,突然寫到“這真下流,可千萬不能讓老師看到”。“老師”是“進步”思想與“文明”的象征,而裸泳的場景雖是自然、原生態的,但在文明的社會環境下,這就是下流的。此外,巴恩斯還在主人公進入到人生的青年時期,對“進步”的文明進行了諷刺:“不過我敢肯定您是比我聰明的人,您可是上過大學的。”,“聰明到不相信上帝了吧”。正如阮煒評價《福樓拜的鸚鵡》所說,“巴恩斯對福樓拜勾勒出的這一極富洞見的守靈場景的闡釋是:宗教與科學一起保衛著罪惡,或者說,宗教與科學在罪惡面前勾結起來,與罪惡形成了某種可恥的三角關系”[9],巴恩斯的《美發簡史》也體現出了宗教與科學在理發師身上相互勾結,融為一體,并一起對抗著自然的代言人格雷戈里。
3 探尋文明與自然沖突之下的出路
在生態批評的浪潮聲里,人類中心主義早已成眾矢之的,而作為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文化淵源的《圣經》也成為討伐的對象,因為正是它確定了人類對地球的統治權力。科學史家懷特指出“基督教是世界上人類中心主義最嚴重的宗教”,“只有拒絕自然為人而存的基督教信念才能遏制生態危機”。《圣經·創世紀》被認為是人類統治自然的文化緣起,也是人類中心主義話語權威。但在《美發簡史》中,這個權威話語遭到了挑戰和解構:“他只敢在一幫懷疑論者面前否定上帝”。然而,面對現代文明進步中人類中心主義和唯科學論帶來的生態危機,巴恩斯在《美發簡史》中試圖尋找解決危機的途徑。正如他在《10 1/2章世界歷史》中體現的思想一樣,它沒有寄希望于科學的未來發展,因為這無異于“采用導致危機的手段來解決危機”[12]。
在主人公幼年時,所有的理發店給他的印象是:“折磨人的椅子,手術室的味道,還有磨刀皮帶和合著的剃刀——合著是合著,讓人看了不覺安全,反而更像是一種威脅”。青年之時,他認為理發店還是一個充滿“保守主義的主仆體制、一切做作的交談、階級意識與付小費”“臭名昭著”的地方。當他邁入人生的年老階段時,在他眼里,“美發店籠罩在混雜的氣氛中,宛若一個歡歡喜喜的門診部,大家都無大礙”。通過主人公三個階段對理發店心態的變化,可以看出格雷戈里由年輕時對文明的憎恨轉變到年老時對文明的淡然。
正如人類的年老與死亡一樣,文明與自然的沖突不可避免。于是,在死亡面前,面對文明與自然的沖突,主人公所采取的態度是適應文明卻不摒棄自然。在他年老時,他終于“花了整整二十五年”才學對理發店里顧客與店員相互之間“半真半假”的戲謔。他還懂得了在回應“是否擔憂當今的世界狀況”的詢問時,“不要老老實實地說‘是’,也不要拋出一個沾沾自喜的‘不’。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總能給自己臺階下”。對于文明社會中的一些事物,主人公格雷戈里并沒有像年幼與年輕時那樣反應激烈。在老年階段,他這樣回顧自己的人生:“我現在已經不再害怕宗教和理發師了”。理發師在故事中連續3次提及與教皇權勢上升以及宗教復興有關的“十字軍”,宛如一個“福音傳道者”,急切希望一切自然事物都有受到宗教觀念統領。由此可見,“巴恩斯顯然在順著福樓拜的思路發揮福樓拜的社會批判精神,在附和福樓拜,等同于福樓拜。”[9]巴恩斯認為宗教界靈魂升天是虛假的承諾。他也從沒加入過十字軍。讀書時,他還總是躲避目光熱切的福音傳道者。而現在,“每當禮拜早上門鈴響起的時候,他就知道該如何應對了”。大體上說,巴恩斯的文化政治立場是保守主義的。但“他傳達這種立場的方式既然是使用福樓拜這面透鏡,讀者得到的東西最多只是一種折射的印象”[9]。
巴恩斯在《10 1/2章世界歷史》所說的“過去”與《美發簡史》中的拿鏡子看經過理發師所打理之后的“后腦勺”寓意相反,它是指與現代文明相對的,沒有受科學技術污染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而在《美發簡史》中,主人公最后說“我不想再看后腦勺了”。他更希望自然與文明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正如巴恩斯的藝術觀認為最好的藝術揭示人生的最高真理一樣,他以平日生活中最常見的事情展現自然與文明的沖突,呼吁自然與文明須和諧共處,而我們人類不能過激地反對一切文明。
4 結論
巴恩斯作為活躍于今日文壇的英國小說家,并不像后現代主義作家那樣把小說看作純粹藝術形式,而是對社會現實問題更為關注。在人類中心主義影響下,現代文明在追求進步中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毫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造成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而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危機,尤其是高科技的濫用更威脅到整個生態系統,甚至是地球本身安全。這些反思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所在,反映出人類生態危機的嚴重性,以及解決生態危機的緊迫性。要解決生態危機就要摒棄人類中心主義,拋棄科學烏托邦的幻想,立足于地球本身,把人類自身視為自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重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應該以真實的自我需要進行選擇,在精神層面上擺脫外在的奴役,保持獨立的人格,順乎天性的發展;再通過自身努力,追尋和吸收文明社會形態中蘊涵的真善美的行為方式,找到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之間的平衡點,從而根本上取得內在靈魂的真正自由和外在世俗生活的寧靜與幸福。雖然巴恩斯對待現代文明的態度有些悲觀,但為人類盲目追求自身發展敲響了警鐘,體現出強烈的生態關懷和責任。
[1]Mira,Stout.Chameleon novelist[N].New York Times,1992-11-22.
[2]Merritt,Moseley.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7.
[3]瞿世鏡.當代英國小說[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
[4]朱利安·巴恩斯.檸檬桌子[M].郭國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5]朱 寰.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6]徐臺榜.論十字軍東征對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推動作用[J].寧夏大學學報,2004(4):19-24.
[7]胡志紅.西方生態批評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8]田 松.唯科學·反科學·偽科學[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9]阮 煒.巴恩斯和他的福樓拜的鸚鵡[J].外國文學評論,1997(2):51-58.
[10]殷企平.質疑“進步”話語 三部英國小說簡析[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6(4):12-19.
[11]朱利安·巴恩斯.福樓拜的鸚鵡[M].湯永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2]朱利安·巴恩斯.10 1/2卷人的歷史[M].林本椿,宋東什,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