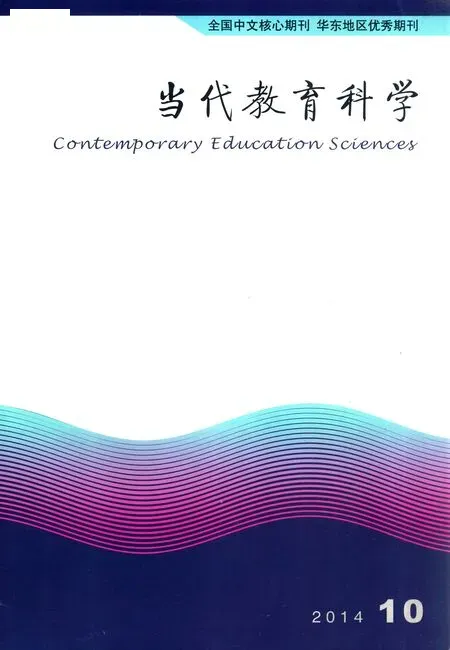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表征及消解*
● 胡 靜
葉瀾說過,教學就其本質而言,是師生通過對話在交往與溝通活動中共同創造意義的過程。審視當前課堂教學活動,教學活動過程被當作向學生灌輸知識的過程,甚至淪為教師話語霸權淋漓盡致展現的過程。提問作為傳統教學的重要方法以及師生在課堂中進行互動交流的重要方式,通過大量的師生對話實現教學目標,它天然具有著師生對話的教育意蘊,然而,在傳統教學的課堂上教師仍然處于提問話語權力的主導地位,霸占著提問的話語權,教師與學生的對話情境更像是充當話語主角的教師和沉默少語的學生,課堂提問無形之中成為教師話語霸權產生的高發地帶。
一、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表征
課堂提問活動是由一系列復雜變化的因素構成,教師處在一個開放的網絡中,各種因素誘發教師話語霸權的形成。對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的實踐形態進行深入剖析發現,存在話語濫用,話語偏見和話語專斷三種教師話語霸權現象。
(一)教師話語濫用
對學生的心理承受力和學生心理特點兩個方面錯誤地預計導致教師對教學時間把握不夠,從而引發教師話語濫用。課堂提問的完成需要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配合。作為學生來說,思考問題和回答問題之間有一個時間的等待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生需要時間來組織語言表達思想,而作為教師來說,需要的是耐心的等待,給學生充分的時間思考,不急于告訴學生現成的答案,寬容地給予學生糾錯的時間和反思的時間。如此,學生不至于因思考時間不充分或是精神緊張等原因倉促作答而導致回答錯誤。維果茨基將人的認知結構分為三個層次,根據學生心理特點,“已知區”的問題學生能夠輕松回答。“未知區”的問題難度太大,學生回答不出來。問題太易使得學生產生思維疲勞,問題太難學生容易喪失對問題的思考興趣。教師的問題應該處于每個學生的“最近發展區”處。提問活動中的教師往往擔心在規定的教學時間內不能完成一定量的教學任務,常常不顧及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特點,不給學生足夠的思考和糾錯的時間,又急于告訴學生現成的答案,采用情緒化的言語刺激學生。這些言語常常缺乏理性思考,隨口說出。事實上,教師擁有的話語權利本應用于引導激勵學生,而不是刺激學生,濫用話語。
(二)教師話語偏見
教師在課堂提問中對待學生的回答截然不同的態度隱藏著教師的話語偏見,表現為兩個極端:教師對優秀學生的贊揚以及對落后學生的主動沉默。對于不同學生的回答,教師常常不自覺地會做出不一樣的反應。[1]優秀學生回答問題,教師常常特別有耐心地進行言語上的指導。對于優秀學生提出的質疑,教師也主要回以鼓勵性的話語,認為優秀學生有主動思考問題的能力。教師的話語偏見所導致的話語霸權使課堂提問中優秀學生成為教學順利進行的推動劑。優秀學生的積極性和進取心被極大地調動起來,而其它學生則成為了教師與優秀學生對話的觀眾。與優秀學生相比較,落后學生在課堂提問中往往處于“伴讀”狀態,沒能受到教師的悉心教導與關注。通常,教師似乎沒等落后學生參與回答,就預先認為落后學生不能很好的回答問題,對落后學生給出答案的評價中帶著不滿與抱怨,或是保持主動沉默的姿態,不給予評價。課堂提問成為一種象征性地民主,一種虛假的和諧。教師對落后學生回答問題表現出無耐心、無信心,少鼓勵的話語偏見使得落后學生越來越游離于課堂提問的邊緣。落后學生對待學業逐漸喪失自信,漸漸打消回答問題的積極性。
(三)教師話語專斷
課堂提問的核心是問題,問題由師生問與答的互動構成。一個完整的問答環節包括問題的選擇,分析和總結。教師的話語專斷主要集中在提問的問題。首先,在問題的選擇上。愛因斯坦說“學生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對于學生來說,選擇問題,是在對教材知識的充分理解的前提下的積極思考。然而,在以知識本位為主導的思想下,教師借助知識的擁有者、理性的權威、天然引領者的角色,對專業知識的話語霸權早已深入課堂提問中,對提問問題的選擇有著絕對的權威。[2]因此,在提問開始時,教師就事先假定學生是沒有足夠的知識水平來思考專業的問題。于是乎,教師理所當然成為提問的主體,學生成為被問的對象。顯然,對問題的選擇的話語專斷并不利于學生對知識的理解。
其次,在對問題的分析上。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途徑之一是培養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3]然而,當下的學生對問題的分析正確與否依據的是教師掌握的知識和教師作出的決斷。提問活動中總是不缺乏以下情形:當學生回答問題后,教師只用“對”或“錯”來結束互動,而此時學生還不清楚自己為什么對,為什么錯,錯在哪里,教師卻沒有繼續對問題加以闡述。教師僅僅是象征性地和學生進行一問一答的互動。看似和諧的課堂,學生卻往往不能完全領悟教師對問題的思考過程,學生的回答似乎成了一種擺設,可有可無。問題分析的過程中學生的思想沒能通過話語傳達給教師,思維能力發展受到來自教師話語專斷的阻礙。學生在課堂提問中的熱情日漸衰退,思維逐漸禁錮,對教師話語的權威由挑戰走向服從,處于教師話語霸權下話語恐懼的狀態。
最后,在對問題的總結上。“以本為本”的傳統教學觀念意味著教師在提問中以教材結論為標準。[3]教師允許學生在一定范圍內發表與教材敘述不同的言論,并給予學生一定的自由,但規定學生按文本思路對問題進行思考。學生的話語也要按照教材的話語標準闡述,于是,出現學生的問題和答案與教材的如出一輒的怪象。這種將學生當成教材的“復印機”式的結論,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發展。強調學生在教師的話語系統內表達思想的行為,導致學生的思想屈從于教師的教材,促使教師成為教材的代言人。由此可知,教師將師生課堂提問平等傳遞轉變為教師控制學生思想的平臺,教師成為提問活動的獨白者,學生則游離于提問環節之外。異化的師生提問活動產生的教師話語霸權使得學生處于話語缺席者的狀態。
二、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的消解
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現象的危害很大。消解教師話語霸權還應回歸課堂提問活動本身。從提問的實踐形態看,提問是師生之間對特定內容進行互動交流、達成相互理解的過程。因此,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的消解有賴于互動的話語主體,和諧的話語氛圍和理性的話語行為。
(一)達成雙主體的話語共識
當前教師課堂提問的話語霸權本質上堅持的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觀念。為此,消解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的基礎是要轉變師生話語觀念。提問的目的是促進學生的發展,為學生提供主動思考的空間。傳統的課堂提問中教師成為提問的主體,學生淪為教師的附屬,成為提問過程中的缺席者。因此,打破教師單一提問主體的觀念,需要建立教師和學生共同課堂提問的雙主體意識。教師不僅僅要提出問題,還要與學生平等地進行交流和溝通,主動傾聽學生內心的聲音,啟迪學生思考,共同思考問題。教師通過提問過程中的言行,鼓勵學生思考,進而幫助學生獲得主體地位的回歸。另外,學生作為課堂提問中的一員,要有與教師平等的地位的覺醒,學生應該認識到教師不是支配者,而是學生的引導者與啟發者,學生不是被支配的對象,是創造者和發現者,學生還應該具有主動提問的意識與表達自己的見解欲望,從教師話語霸權的依附者轉變為提問過程中的主動者的意識。
(二)創建和諧的話語氛圍
消解課堂提問中教師話語霸權,創建和諧的話語氛圍有助于加快學生擺脫話語恐懼,激發學生提問的積極性。哈貝馬斯說,“在交往關系中,不存在外在力量強迫的問題,不存在約束和被約束的問題,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之間的平等交流、解釋、對話,相互理解、求同、合作。”[4]因此,和諧的話語氛圍對于教師來說,能更好地與學生進行平等的話語互動,發現學生身上潛藏的生命活力。首先,和諧的話語氛圍需要尊重不同話語主體。尊重不同話語主體應該遵循平等與公平的原則。遵循平等原則,教師應該向學生打開思想的大門,不因外界賦予教師特殊的地位而限制學生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的機會。給每個學生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享受教師同等的鼓勵。遵循公平原則,教師面對不同學生,都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使每個學生都得到照顧,對不同水平的學生提出不同難度的問題,對于學生回答問題后的評價,應一視同仁,客觀地評價問題。其次,和諧的話語氛圍需要承認并重視課堂提問中話語主體的權利。認識到教師用單一霸權的方式進行課堂提問對解放學生的思想,建立和諧的提問氛圍起著反作用,教師就應該允許學生在提問中享有話語權利。允許學生有提問權,教師與學生雙方在相互問答的過程中,學生不斷生成新的知識,獲得新的體驗,使學生對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與體悟。允許學生在提問中的質疑權,學生知識的獲得經由質疑產生,學生的質疑表明學生積極參與思考問題。教師通過合理引導學生的質疑,進而使學生發現更多的問題,從而解決問題。
(三)形成師生理性對話交往行為
在提問中如果只有師生雙方具有平等對話的意識和良好和諧的話語氛圍,實際上只是形式上的對話,這種對話只會離霸權越來越近,會導致對話中存在教師壓抑學生個性的后果。因此,主張師生間形成理性的對話交往行為以實現真正的對話。如何形成理性的對話交往行為?哈貝馬斯認為,消除師生對話障礙,應該打破師生對話交往的界限,創設師生交往的對話場域,這種對話場域需要遵循理性原則,即在理性層面上進行對話交往。[5]理性對話需要教師摒棄單純地關注人與物的工具性關系,轉向關注人與人的民主平等關系。理性的師生對話交往行為的形成有賴于提問中師生雙方人的價值的實現。因此,課堂的提問不是灌輸知識的手段,而是促進師生協調互動的方式。教師與學生本著溝通與對話的目的,采用協調互動的提問方式敞亮自我與邀請他人共同解決問題,在問與答中實現自我反思,自我提升,互利互惠。當然,在提問過程中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需要師生雙方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在理解中達成對問題的普遍共識。
[1]牛海彬,曲鐵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視閾下的教師話語建構[J].外國教育研究,2010(5):85.
[2]徐輝,謝藝泉.話語霸權與平等交流——對新型師生觀的思考[J].教育科學,2004(6):49.
[3]金備生.構建以學生發展為本的課堂教學[J].學科教育,2003(8):38.
[4]姚本先,劉世清.教育交往中的言語困境探討[J].課程.教材.教法,2004(2):81.
[5]余靈靈.哈貝馬斯傳[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