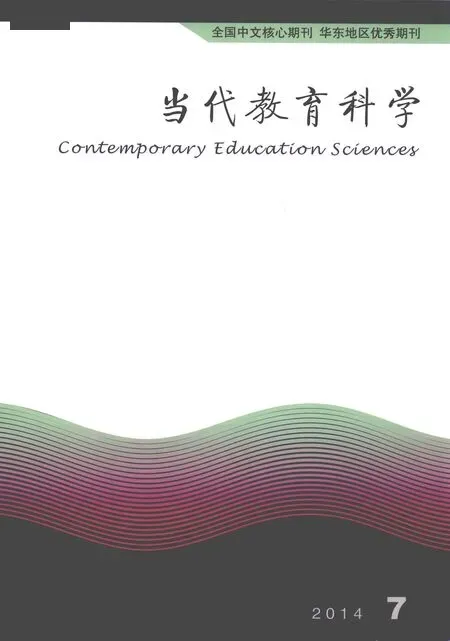論復雜性理論視域中的課程研究*
●李舒波
論復雜性理論視域中的課程研究*
●李舒波
以莫蘭、普利高津以及美國圣塔菲研究所為代表的復雜理論研究,其理論精髓是對西方近代以來經典科學研究中簡單性思維的批判、修正與超越。借鑒復雜理論的方法論透析課程研究中的簡單性思維,其意蘊在于有利于理解課程實踐的復雜性以及審視課程理論的界限性。復雜理論對課程研究的具體啟示至少體現為:課程本體從存在到演化的當代定位;課程知識從對立到互動的范式置換和課程方法從構成到生成的內在轉變。
復雜理論;課程研究;方法論
自課程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領域,無論博比特的活動分析法、查特斯的工作分析法,還是堪稱經典的泰勒原理,課程領域所掀起的科學化運動折射出濃烈的簡單性情節與旨趣。這種以“簡單性”為主流話語的理性取向統攝整個課程領域的思想范式與實踐模式,課程便由此被規約為線性、封閉、穩定的實體存在或工藝學程序,并由此面臨著諸多合法性、合理性危機。而莫蘭(E.Morin)的“復雜性方法”、普利高津(I.Prigogine)的“復雜性科學”、美國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等以反思、超越西方近代以來科學研究中的靜態封閉、線性還原以及機械決定論等簡單性思維為主要學術旨趣的復雜理論研究,則為課程研究擺脫、解決簡單性思維規約束縛下當前課程領域中所出現的理論盲點及實踐困頓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法論。
一、復雜理論及其方法論旨趣
莫蘭將分離、還原和抽象原則統一稱為“簡單性范式”,[1]所謂“分離”是指經由笛卡爾總結的二元論哲學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諸如中心與邊緣、現象與本質、有序與無序、確定性與隨機性等產物;“還原”是指將所分離出的二元產物進行靜態的切割與肢解,從而摒棄現象、無序,并將事物還原為本質、有序等;“抽象”是指運用抽象概念化、形式化的公理、規律對所還原出的品質進行提取、描述。這三大支柱的相互連續、彼此遞進成就了一個完美的簡單性思維范式,并貫徹在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例如,牛頓演繹力學的三大規律時指出:“自然界不做無用之事,只要少做一點就成了,多做了卻是無用;因為自然界喜歡簡單化,而不愛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來夸耀自己。”[2]愛因斯坦在構想出一切自然規律必然奉承簡單性原理時也指出:“一切科學的偉大目標,即要從盡可能少的假設或公理出發,通過邏輯的演繹,概括盡可能多的經驗事實。”[3]然而,隨著簡單性思維因其無法根治和袪除的內在痼疾與癥結而引發種種思想認識上的悖謬、沖突以及實踐領域中的迷惘、混亂,以及自20世紀以降,自然科學領域所取得的一系列諸如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超循環論、混沌理論、分形理論等革命性突破,根深蒂固的簡單性思維由此遭遇了自其確立以來最為猛烈的質疑和深刻的批判。
1973年法國哲學家莫蘭出版《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書,較早提出復雜性思想,他指出:“對人類的一個封閉的、片段的和簡化的理論的喪鐘敲響了,而一個開放的、多方面的和復雜的理論時代開始了。”[4]并于1977年開始系統建構復雜性方法的多卷本巨著《方法》,由此系統論述了以兩重性邏輯、組織循環邏輯以及全息邏輯為核心的復雜性方法。1979年比利時物理學家普利高津出版《新的聯盟》(該書1984年的英文版,改名為《從混沌到有序》)一書中提出了“復雜性科學”的概念,這一概念來源于貝納德流體實驗、激光和化學震蕩反應等典型實驗,這些實驗現象共同的特征即是有序結構的形成和維持需要耗散能量和物質,普利高津將這類結構稱為耗散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尖銳批評了“把復雜性約化為某個隱藏著的世界的簡單性。”[5]1984年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州府圣塔菲成立一個專門從事復雜性科學研究的機構——圣塔菲研究所,匯集了諾貝爾獎得主蓋爾曼、安德森、阿羅等為了探索生物、物理、經濟、語言、大腦和計算機等跨學科復雜性問題的物理學家、經濟學家,成了世界復雜性科學研究的專門機構和前沿陣地。該所復雜性科學綱領指出:復雜性實質上就是一門關于涌現的科學。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發現涌現的基本規律,涌現的發生并非源于靜態有序,也并非源于動態無序,而是誕生于秩序與混沌的邊緣。[6]
這三家的復雜理論彼此差異卻又相互補充,莫蘭提出統一性與多樣性、有序與無序相統一的復雜認識方法理論;普利高津則認為復雜性科學意味著不可逆性、隨機性與不確定性;而圣塔菲研究所又提出復雜性產生于“混沌的邊緣”,即在有序和無序適中地相互混合的區域。整體來講,這三種復雜理論的共識便在于超越簡單性思維的框架,而強調事物自身本體論復雜性的復歸并倡導非還原性、混沌、非線性、涌現、協同、自組織、生成、非對稱性、突現、不確定性等復雜性的思維方式。
二、復雜理論對課程研究的意蘊
思考復雜理論對課程研究的意蘊,可以根據美國復雜學者雷舍爾(N.Rescher)從本體論、認識論[7]兩個范疇思考復雜性的分析框架,從課程實踐與課程理論兩個范疇來進行。
(一)理解課程實踐的復雜性
課程實踐是課程研究的對象,如何理解課程實踐必然影響課程研究的價值判斷與理論視野。現代課程研究興起于對控制和效率的追捧,無論是工作分析、活動分析還是泰勒原理,其根本旨趣在于預先確定課程目標,隨后選取課程經驗,再次進行課程實施,最后組織課程評價。沿用這種線性還原、機械決定論的簡單思維,課程實踐便被簡化為有序、靜態、穩定、固態的實體存在或計劃程序。然而,“并沒有簡單的事物,只有被簡化的事物。”[8]從本體論層面,課程實踐的復雜性邏輯在于人自身的復雜性,科學研究發現:“我們大腦就表現為復雜網絡的非線性動力學,”[9]這體現為學生認知、情感與心理以及教師的教學認識、教學行為等都具有內在的非線性、差異性等復雜性表征。而且,由于“復雜性其實是存在于組織之中:即一個系統的組成因素用無數可能的方式在相互作用。”[10]這種課程實踐的復雜性表現為課程實踐中學生、教師、學科知識、課堂情境等之間的互動、組織,進而產生了課程實踐無窮的豐富性、動態性、開放性等復雜性。由此,課程實踐的復雜性便意味著擱置對課程實踐的簡單線性判斷與預成定論,課程是在活生生、變化多端的實踐場域不斷生成、延綿的有機體,這一過程必然承擔著多面的偶然、隨機、突發事件等因素的影響從而使課程實踐呈現為復雜性、多變性、非線性、不確定性、非平衡性等表征。
(二)審視課程理論的局限性
課程理論是課程研究的成果,如何審視課程研究的成果形態,勢必影響到課程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合法性。傳統課程理論無論從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還是桑代克的學習定律、泰勒的課程目標模式、斯金納的程序教學等,均以一種機械還原論、線性決定論等工具理性和技術操作主義的方式來從事課程理論研究,以此為課程實踐提供與設定先驗的、普遍的和必然性的標準、確定性的方法以及嚴格性的操作程序。對此,莫蘭指出,這是一種虛假的完美理性,“即在大量的客觀事物表現出來的現象中從差異性中抓取統一性,從變動性中抓取穩定性,從而獲得關于客觀事物存在和運動的規律,便于實踐主體‘以簡奴繁’地加以掌握和運用。”[11]然而,從認識論層面來看,課程理論的復雜性主要來源于計算復雜性,即通過主體認識和經驗視閾進行測量、推論課程實踐所耗費的成本與所付出的代價,并由此產生課程理論的復雜性。于此同時,認識論范疇的復雜性“一方面是對非分裂的、非隔絕的、非還原性的知識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對任何認識的非完成性和非完備性的承認。”[12]那么,基于完美理性的“處方式”的傳統課程研究由于受到課程實踐復雜性的內在約束以及研究主體有限理性的鉗制,都使得課程理論并非全智全能,難免存在理性不及或是理性約束的維度。復雜理論的意義在于促使我們重新審視課程理論的有限性,為課程理論的限度、有效性以及局限性進行劃界,并由此秉承著一種有限決定論與有限預測觀交融的思維品性。
三、復雜理論對課程研究的啟示
基于復雜理論視域的課程研究,無疑將消解課程研究簡單性所誘發的困境以及難為,同時也意味著一場課程研究的范式轉變,其具體啟示至少體現在課程的本體論、課程的認識論以及課程方法論三個層面。
(一)從存在到演化:課程本體的當代定位
課程本質的問題隸屬于課程本體論的范疇。歸納起來,傳統課程本質大體有三種取向,課程即有組織的教學內容、書面的學習計劃以及預期的學習結果,三種取向分別指向了課程內容、計劃以及結果。其主要特征都在于強調課程是一個孤立固定、封閉單一、絕對靜止的實體性存在,這種實體性消解與隔離了課程的生成性邏輯以及對課程實踐時間之矢的否定。實體性的課程本質也使得課程只是作為一種固定、機械、僵化、恒久不變的學習材料而獨立于教師、學生的自主認知與經驗建構之外,演化出了一個防教師、防學生的課程觀。然而,自熱力學第二定律對“時間之矢”的發現打破了絕對時間的對稱性,將世界的本質定位于實體性、靜態的、線性的實體存在的定位顯然早已不符事宜,實際上“復雜性并不僅僅包含向我們的計算能力挑戰的組成單元的數量和相互作用的數量,它還包含著不確定性、非決定性、隨機現象,復雜性在某種意義上,總是與偶然性打交道。”[13]這便意味著作為封閉實體的課程本質已經過時,從復雜理論視角看,課程呈現出混沌、無序、分岔甚至突變的非連續性、非線性的表征,其確定性不斷降低并難以預測,課程的本質也由此呈現出開放動態、非線性、復雜性的演化過程。這種課程本質的定位意味著學校課堂情境中,教師、學生、課程始終處于一種復雜的際遇與互動之中,課程成為學生與教師共同經歷個人體驗以及履歷邂逅的延綿性演化,從而課程的本質體現為“正在創造著的一條跑道,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14]
(二)從對立到互動:課程知識的范式置換
課程的知識問題隸屬于課程認識論的范疇。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深陷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學,例如:笛卡爾提出“心靈與物質”,休謨提出“觀念的關系與實際的事實”的兩種知識以及康德提出“物自體與現象”,這種知識二元論哲學在于強調知與行、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理論與實踐等的二者分離、彼此對立、互不依賴。之所以產生二者的分裂,在于為人性本身逃脫不確定的風險,而強調確定性的追尋。這是因為“通過思維人們似乎可以逃避不確定性的危險,”“實踐活動所涉及的乃是一些個別的和獨特的情境,而這些情境永不確切重復,因而對他們也不可能完全加以確定,”[15]所以實踐、經驗以及行動等必然會引起不確定的危險,而必須加以祛除、摒棄。伴隨著這兩者的分離,二者出現了對立的局面,知識研究與真理的追尋開始摒棄行動的參與、經驗的內化以及實踐的價值。正如杜威(J.Dewey)指出:“只有確定的事物才內在地屬于知識與科學所固有的對象。如果產生一種事物時我們也參與在內,那么我們就不能真正認知這種事物,因為它是跟隨在我們的動作之后的而不是存在于我們的動作之前的。所涉及行動的東西乃屬于一種單純猜測與蓋然的范圍,不同于具有理性保證的實證。”[16]沿襲這個知識論譜系的課程知識研究,所建立的共同的基礎便是傳統哲學意義下的二元對立,課程領域中課程知識理性至上以及普遍主義無涉,這種課程知識觀摒棄任何時間任何場域中教師與學生的個人知識、實踐體驗、經驗互動等,教師的課程身份與權責由此成為了機械性地執行課程方案、忠實性地搬運課程知識以便原原本本的傳遞、灌輸于學生。伴隨哲學研究對二元論知識研究的剖析以及復雜性理論的探索,杜威指出:“心靈是一個參與者,與其他事物交互發生作用。”[17]普里戈金則主張“人與自然的新對話”,嘗試性地討論了這種“既作為參與者又作為旁觀者的知識概念。”莫蘭也指出:“在我們以客體眼光考察復雜性外,還應以‘復雜性的第四眼’考察正在考察世界的我們自己,也就是把我們包含在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中。”[18]這一系列范式的轉變呼喚著課程知識的范式重建,這種新的課程知識范式體現為教師、學生的個體知識與代表著公共知識的課程內容的相互互動、對話,一種平等交互、意義對話的課程知識觀。教師與學生個體知識統整于學科知識之中,并伴隨著教師、學生以及學科知識的相互對話,合作建構思想與意義,不斷體認知識的意義與價值,而在這一相互轉化、動態生成中,共同構成了課程發生與演化的知識基礎。
(三)從構成到生成:課程方法的內在轉變
課程的思維問題隸屬于課程方法論的范疇。傳統課程思維深陷構成思維,即“把對事物的認識劃歸為對這些事物固有的有序性即規律、不變性、穩定性等的認識。”[19]這種簡單性課程思維深受還原論的鉗制,將整體性的課程進行肢解、拆分,直到找到構成課程的穩定性、規則性、必然性、確定性、統一性的結構序列,以此演繹出普適性原理、科學性模式、客觀性標準、統一性方法、程序性操作方式等指導課程實踐。這種濃烈的“技術理性”,強調“控制”、“效率”旨趣的同時,奉行著“一旦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可以推算出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演出先前的狀態。”[20]由此,課程實施中的教師和學生被外在的課程計劃所牢牢控制,毫無疑問,這種課程思維嚴重遺漏了課程實踐過程中的復雜性、情境性、偶然性因素。然而,復雜理論看來,“復雜性不屬于現實的現象的泡沫,而是屬于它的本質本身。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非決定性、隨機性不能作為認識、實踐的殘渣和屏障,而應該成為我們面對改革現實領會和認識的一個重要方面。”[17]這就意味著事物的變動性、不規則性、偶然性、不確定性以及離散性等擁有了合法性的承認與賦權。課程實踐中各種不確定性、隨機現象或是非連續性偶然事件誘發整個實施過程處于有序與無序間的不平衡的混沌狀態。由此,便呼應著一種生成性思維,即“重視事物規律、結構等有序性的過程性,強調事物的生成性,許多自組織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19]那么,生成性的課程思維便意味著課程實施的真正品質不僅是對預設的課程改革方案、計劃、藍圖的忠實執行,而更是在鮮活的實施場景中,師生共同對課程進行不斷的創造性反饋、補充以及調整的生成性、開放性、創造性實踐。并且,鮮活的課程場景中的隨機、偶然性事件的侵襲,本身也具有著無限、潛在的課程資源,由此有必要巧妙動用教學機智、實踐性智慧等不斷挖掘與綻放這些隨機偶然性事件的課程意蘊。
[1][11][12][法]E·莫蘭.陳一壯.復雜性思想導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8,5、8、3.
[2][美]H·塞耶.王福山.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3.
[3]許良英等.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262.
[4][法]E·莫蘭.陳一壯.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73.
[5][比]I·普里戈金等.曾慶宏等.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41.
[6][美]M.沃爾德羅普.陳玲.復雜——誕生于秩序與混沌邊緣的科學[M].北京:三聯書店,1997,115.
[7]N·Rescher.Complexity:A Philosophical Overview[M].News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9-11.
[8][18][法]E·莫蘭.陳一壯.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1、153-155.
[9][德]K·邁因策爾.曾國屏.復雜性中的思維[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1.
[10]張良.論課程改革之復雜性邏輯:聲辯及其構想[J].全球教育展望,2012,(4).
[13]轉引自:張良.新課程改革中簡單性思維的困頓及其超越[J].教育發展研究,2010,(24).
[14][加]B·Davis.崔長運.復雜理論與教育[J].全球教育展望,2008,(1).
[15][16][17][美]J.杜威.傅統先.確定性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154.
[19]黃欣榮.復雜性科學與哲學[M].北京:中央翻譯出版社,2007,63.
[20][比]I·普里戈金.湛敏.確定性的終結:時間、混沌與新自然法則[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9.
(責任編輯:孫寬寧)
2012年貴州省教育改革發展研究十大招標課題——“特崗教師”政策對貴州農村教育發展的影響及政策優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李舒波/畢節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教育心理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