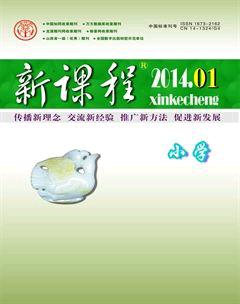溫柔“陷阱”
王千紅
在賞識備受推崇的今天,許多人認(rèn)為懲罰沒有了意義。但中國青少年研究會主任孫曉云卻認(rèn)為:教育本就是十八般武藝,表揚(yáng)批評獎(jiǎng)勵(lì)懲罰,各有其責(zé)。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一種虛弱的教育、脆弱的教育、不負(fù)責(zé)任的教育。巧妙而藝術(shù)地運(yùn)用懲罰,能與賞識教育一樣,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懲罰教育絕不是體罰。懲罰教育是在孩子犯了錯(cuò)誤的時(shí)候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孩子心服口服地改正自己的錯(cuò)誤。那么,怎樣才能在對孩子不施加任何壓力的情況下,讓他們主動、積極地去接受批評呢?我在幾年的教學(xué)生涯中摸索出一套懲罰的方法。我把它戲稱為溫柔“陷阱”法。溫柔,即對每一個(gè)犯了錯(cuò)誤的學(xué)生都要有愛,愛心應(yīng)成為懲罰的前提;“陷阱”,即懲罰要講究藝術(shù),“陷阱”是懲罰的手段。懲罰的藝術(shù)是用愛心挖掘一個(gè)陷阱,讓學(xué)生在這個(gè)陷阱中不知不覺地接受懲罰并健康地成長起來。
溫柔“陷阱”的設(shè)置有幾種方式。
一、“自投羅網(wǎng)”式
有的家長一聽說孩子犯了點(diǎn)錯(cuò)誤,就火冒三丈,不分青紅皂白就是一頓猛批狠打,結(jié)果不僅收不到教育的效果,還會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有的家長和教師雖然不打孩子,但是采取諷刺挖苦等方式,讓孩子在心靈上受到傷害。這種“心罰”對孩子的傷害在某種意義上并不亞于體罰。以情動人、以理服人才是最好的方法。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擔(dān)任小學(xué)校長時(shí),看到一位學(xué)生用泥塊砸另外的同學(xué),就制止了他,并要他放學(xué)后到辦公室去。放學(xué)后,陶先生來到辦公室時(shí),那位學(xué)生早已等在那里。先生沒有批評他,反而掏出一顆糖給他,說:“你按時(shí)到,我遲到了,獎(jiǎng)給你。”學(xué)生驚疑不定地接過糖。接著,先生又掏出一顆糖,說:“我制止你用泥塊打人,你立即住手,我應(yīng)該獎(jiǎng)勵(lì)你。”學(xué)生疑惑萬分地接過糖。先生又掏出第三顆糖,說:“根據(jù)我的了解,你用泥塊砸那些男生,是因?yàn)樗麄兤圬?fù)女生,這說明你有正義感,這顆糖也是獎(jiǎng)給你的。”這時(shí),學(xué)生激動得流下眼淚,說:“校長,我錯(cuò)了,我砸的不是壞人,是自己的同學(xué)……”陶先生笑了,又掏出第四顆糖:“這顆糖獎(jiǎng)給你,是因?yàn)槟阏J(rèn)識了自己的錯(cuò)誤。好啦,我的糖給完了,我們的談話也完了。”
這種“懲罰”教育,是在濃濃的情感中實(shí)施的,是對孩子心靈深處的觸動,孩子不但沒有任何的抵觸情緒,還受到了很大的感動。但就是在這種溫情的“懲罰”中,孩子真正認(rèn)識到了自己的錯(cuò)誤,并心悅誠服地改正了自己的錯(cuò)誤。
二、“投其所好”式
著名的諾貝爾醫(yī)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麥克勞德每次談及他的成功因素時(shí)總是對自己小時(shí)候的一次“懲罰”念念不忘。
有一次,小麥克勞德萌發(fā)了看看狗內(nèi)臟的念頭。于是他和伙伴們偷殺了校長家的寵物。校長得知此事后,決定重重懲罰麥克勞德。可誰也沒有想到懲罰的內(nèi)容竟是叫他畫一張狗的結(jié)構(gòu)圖和一張血液循環(huán)圖。
校長的懲罰藝術(shù)之高明,在于他透過“殺狗事件”看到了麥克勞德的興趣愛好,并且投其所好,用一種意味深長的方式激勵(lì)了麥克勞德的情感因素,使他落入了校長設(shè)下的溫柔“陷阱”。使他在受罰中不僅反省了自己的行為,而且保護(hù)了他的積極性。
我在工作中也經(jīng)常利用“投其所好”法“懲罰”犯了錯(cuò)的學(xué)生,如罰犯錯(cuò)的學(xué)生畫畫、罰寫作、罰做好事等。這類彰顯學(xué)生特長的罰,與其說是罰,不如說是一種激勵(lì)。這么富有人情味的“懲罰”,哪個(gè)學(xué)生不樂意接受呢?
三、“責(zé)人先責(zé)己”式
批評學(xué)生,貌似簡單,實(shí)則復(fù)雜,切忌“急功近利”。“以退為進(jìn)”的批評表面上是給學(xué)生留一些余地,實(shí)際上是在無形中給學(xué)生一面鏡子,照出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責(zé)人先責(zé)己,教師先自我批評一番,讓學(xué)生在教師的批評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知不足方能求上進(jìn)。
我班有個(gè)學(xué)生叫潘孝雄(化名)作業(yè)常常是“缺斤少兩”,我巧用“陷阱”,在他的作業(yè)后面寫上:“真是對不起,老師少給你兩個(gè)勾,我找不到地方打,怎么辦?”第二天,他把作業(yè)如數(shù)奉還,還帶上了紙條:“是我不好,您能再補(bǔ)我兩個(gè)勾嗎?”
每學(xué)期期末那天,我總是很真誠地在學(xué)生面前做一次深刻的“檢查”。找出自己一學(xué)期來的不足,發(fā)自內(nèi)心地向?qū)W生說一聲“對不起”,并真誠地希望學(xué)生向家長轉(zhuǎn)達(dá)我深深的歉意。
責(zé)人先責(zé)己,側(cè)面點(diǎn)撥,引發(fā)自信,良藥不必苦口。措辭誠懇的自責(zé),往往勝過耳提面命的說教。
四、“底下私了”式
一天早上,我班一位學(xué)生報(bào)告,她的午飯錢不見了。我經(jīng)過調(diào)查,基本上確定了錢是阿峰拿的。于是,我找來阿峰,告訴他:“偷竊是一種違法行為,如果繼續(xù)下去將會走向犯罪。”可他始終不敢承認(rèn)。我又告訴他:“如果是你拿的,你就悄悄放回去,我們可以把這件事私了。我保證不在同學(xué)面前說出來,絕對保密。”后來就聽到了那位丟錢的學(xué)生報(bào)告,錢找到了。同學(xué)們自今也不知道錢是誰拿的。
蘇霍姆林斯基說:“一個(gè)好老師意味著什么,首先意味著熱愛學(xué)生。”學(xué)生在成長過程中犯點(diǎn)錯(cuò)誤是在所難免的,每個(gè)教師都應(yīng)該深知,犯了錯(cuò)的學(xué)生也有尊嚴(yán),也有人格。如果教師不顧及這些,把學(xué)生臉皮撕破,很有可能會造成在這些學(xué)生破罐子破摔,甚至?xí)l(fā)生意外。
社會在飛速地發(fā)展,學(xué)生的變化也是多種多樣,新時(shí)代的學(xué)生渴望新時(shí)代的教師,德育追求新型的藝術(shù)。“懲罰”有法,但無定法。“懲罰”是一服苦口的良藥。只要我們從尊重學(xué)生、愛護(hù)學(xué)生出發(fā),掌握“懲罰”的藝術(shù),并將之嫻熟地應(yīng)用于日常的德育之中,讓“懲罰”溫柔起來,便可一舉多得。善用“懲罰”這一教育藝術(shù),會與賞識有異曲同工之效。
(作者單位 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qū)長干小學(xué))
編輯 韓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