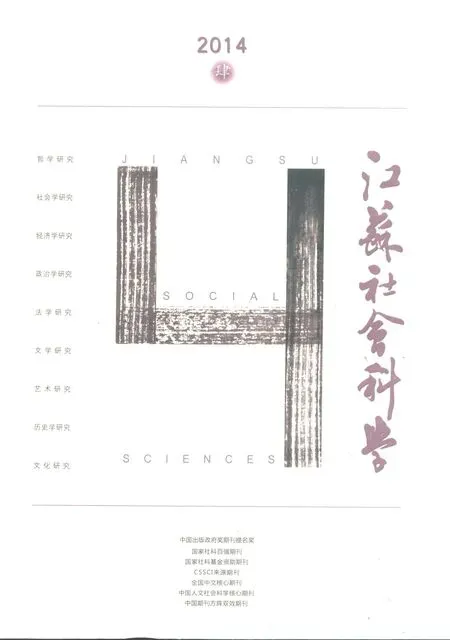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路徑創新
周曉虹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 210023
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路徑創新
周曉虹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 210023
現有社會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屆三中全會用“社會治理”代替了原先的“社會管理”,而且直接將社會治理與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結合在一起,申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盡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卻不僅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指明了方向,也從根本上對國家與社會關系有了新的確認。
具體說來,在新的社會治理體制下,國家或政府不再是單一的社會管理主體,其他社會組織、私營機構也可以作為權力主體參與其間,這體現了“還權于民”的傾向;同原先社會管理體制強調國家(政府)對社會的強制性管理不同,新型社會治理體制強調在“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之間建立“良性互動”式的合作。
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的兩大重任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述及這一任務時,將“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視為改革之目標,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一復雜的改革重任歸納為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社會組織兩大方面。
轉變政府職能:首先涉及到政府究竟應該管什么,不管什么;其次涉及到怎樣管,以及怎樣不管。就第一個問題而言,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政府有五項核心使命:即“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投資于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保護承受力差的階層以及保護環境”。
這都涉及到政府應該管的事情,具體說來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國家或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事情,包括與國家和社會安全、社會穩定相關的事宜,如立法和司法保障、社會治安、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網絡安全、社會秩序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等。第二類涉及社會公平正義、民生實踐、社會服務,主要包括教育、就業、養老、醫療衛生、文化生活、社會保障、社會救濟以及基本的公共物品供給和政府提供的行政類別的服務。這一類可以在政府主導或者“引導”下,通過市場機制或道德激勵激發社會參與合作,既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需求,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
培育社會組織:從政府身上“卸”下來的擔子或事務,不但不能棄之不顧,反而需要更好、更有效地承擔起來,而承擔市場和政府都有可能“失靈”區域的治理任務的最好對象就是社會本身,包括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非營利組織、社團、人民團體或公民個人,其中大多數可以稱之為廣義的社會組織。培育社會組織,首先要尊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切實加強對社會組織及公眾的社會參與權力的法律保護。事實上,培育社會組織,并非需要全部從頭再來、白手起家,我們原有的工青婦系統、工商聯合會以及各類協會、學會都可以通過創新變為有活力的社會組織。關鍵是“加快實施政社分開”,讓這些組織機構都能夠真正與行政機關脫鉤,而此次事業單位改革是一個絕佳時機。在激發現有社會團體組織的同時,應該賦予其他社會組織如各類基金會、非營利組織、民營社團和中介機構與現有的人民團體以同等權利,這樣才能“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其次是能夠為社會組織的治理運作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必須通過政府的“分權”,一方面將無限政府自身轉變為有限政府,另一方面與獲得政府“分權”的社會組織“合作治理”。
再次是能夠為社會組織的成長提供資源供給。包括設立公益創投基金,為初創期和中小型的公益組織提供“種子資金”,以及管理或技術支持;實行政府外包與購買公共服務;還可以由公益組織自己爭取獲得政府、基金會或其他公益捐贈的支持。
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的若干突破口
1.改革信訪制度,通過司法中介對接法治軌道。嘗試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專項招標、服務外包等方式,逐漸將部分乃至全部信訪事件交由律師事務所、律師協會、司法工作室等各類專業法律機構、社會組織代理,或提供專業咨詢,或提供民事與行政調解,再或提供司法幫助。一方面真正實現“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的設想,另一方面有效增加法律事務所等機構的咨詢和非訴業務。
2.在實行網格化管理的同時,大力推進基層社會自治。基層社會的網格化管理是一項有益嘗試,但其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進一步的實踐應該由網格化管理向社區自治、居民自治過渡。
3.建立第三方輿情調查中心與政府回應中心,不僅要及時處理突發的公共性事件,更要對社會組織和公民的意見進行常規性的及時、負責的回應。可以嘗試將輿情調查交由高校或民營研究機構等第三方來完成,基層政府的辦公室、信訪局等相關部門成立輿情民情回應會辦中心,定期或不定期處理、回應比較重大或頻繁出現的輿情信息或民眾訴求。
4.加強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文明進步。比如,在廢除勞教制度之后,近期亟需大批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協助國家機關從事社區矯正。提高專業社工的能力和相關待遇,通過支付轉移、服務外包、公益創投基金等多種方式,支持社工機構大膽介入社區矯正事業。
〔責任編輯:天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