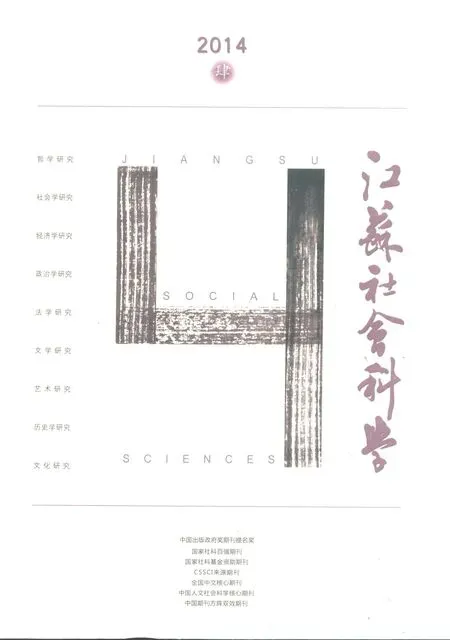主動改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理想選擇
——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路徑辨析
李昌庚
主動改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理想選擇
——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路徑辨析
李昌庚
雖然主動改革是痛苦、艱難的,但任何被動改革及其后可能出現(xiàn)的變革都更容易帶來災難性后果,尤其基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因此,主動改革是中國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理想選擇,但需以更為審慎和清醒的態(tài)度把握主動改革。在主動改革進程中,要避免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創(chuàng)造相對穩(wěn)定和默契的國際環(huán)境,形成改革合力,減少或避免改革誤判。
社會轉型 特殊國情 以史為鑒 主動改革 平穩(wěn)轉型
我國近現(xiàn)代以來經(jīng)歷了三次社會轉型:第一次是清末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是1949年建國以后,第三次是1978年開始的全面改革開放。由于前兩次社會轉型未能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三次社會轉型仍是前兩次社會轉型的延續(xù)。關于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轉型路徑選擇,筆者曾有多篇論文提及,基于現(xiàn)實國情,黨和政府要有相應的主動改革路線圖,從而避免被動改革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1]參見李昌庚:《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穩(wěn)定的博弈與平衡》,〔武漢〕《學習與實踐》2009年第4期;李昌庚:《維穩(wěn)與改革的博弈與平衡——我國社會轉型期群體性事件的定性困惑及其解決路徑》,〔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jīng)明確提出了主動改革目標,并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筆者就此再略陳管見。
一、為何要主動改革
人類社會從古至今,任何政權如果缺乏將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不斷調整、諧調、消解的內在機制,則執(zhí)政到一定時期,當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面臨改革或變革的現(xiàn)實壓力。但如果執(zhí)政者回避或怠于改革或錯失改革良機等,人類社會的歷代政權更替往往更多經(jīng)歷了因被動改革而帶來的革命性劇變,其結果往往出現(xiàn)一定時期的局勢動蕩及其社會停滯期,引發(fā)人權災難,從而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諸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晚清的中國等均是如此。
對于當今中國而言,同樣面臨著改革的現(xiàn)實壓力。雖然我國經(jīng)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滯后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而致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也不徹底,故社會轉型的改革壓力依然存在并更為艱巨。在這種背景下,基于我國民族問題、臺灣問題、東中西部地區(qū)差距、城鄉(xiāng)差距以及13億人口等現(xiàn)實國情語境下,加以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以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乃至今日體制性缺陷所留下的歷史欠賬非一時所能解決[1]李昌庚:《官員財產(chǎn)申報制度是否可以起航?》,〔北京〕《團結》2013年第3期。,如若處理不慎,均有可能出現(xiàn)民族沖突、國家分裂、地方諸侯、社會撕裂及其民粹暴政等問題,進而引發(fā)一定時期的社會動蕩及其人權災難,甚至即便付出一定代價也難以獲得預期效果。清末辛亥革命其后所發(fā)生的軍閥割據(jù)、地方諸侯、民粹暴政等便是深刻的歷史教訓[2]這并非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性貢獻,但我們可以從中反思:如果大清帝國由恭親王開始的主動改革甚至其后的“戊戌變法”成功,是否可以避免其后的辛亥革命及其后一系列問題,進而使中國少走歷史彎路而步入現(xiàn)代化國家行列?雖然這種歷史假設不可與當今社會主義中國面臨的問題相提并論,但這個假設又足以引以為鑒。。
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任何一個政權積累到一定階段能否實現(xiàn)或完成主動改革,從而跳出政治周期律?因為執(zhí)政者主動改革意味著“自己拿起手術刀給自己開刀”,必將面臨著利益固化藩籬和既得利益集團障礙的怠于改革,以及改革不當、錯失改革良機或外來干擾等若干或然因素,而致改革受挫或失敗。由此決定了任何主動改革往往是痛苦而艱難的,甚至會夭折。歷史亦以證明,古今中外歷代政權更替多以滯后性的被動改革而致革命性劇變引發(fā),從而付出沉重的社會轉型代價。這也是某些人對執(zhí)政者主動改革不抱希望,而是追求激進變革的理由所在。當然,人類歷史也不乏有主動改革從而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成功先例。諸如韓國、印尼、緬甸、尼泊爾、我國臺灣地區(qū)甚至不丹等。然而,中國的現(xiàn)實國情要遠比上述國家和地區(qū)復雜的多,由此也決定了不要對中國的主動改革報以盲目樂觀或想當然態(tài)度。
因此,基于中國現(xiàn)實國情,筆者的結論在于,為了吸取原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等國家的經(jīng)驗教訓,主動改革應當是黨和政府懷抱民族和國家使命所應當作出的最優(yōu)戰(zhàn)略選擇,這也是降低執(zhí)政黨、民族和國家社會轉型代價繼而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理想選擇。同時,必須以更為審慎和清醒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的主動改革,力求避免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這也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任何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中國公民訖需考慮的問題。為了避免歷史重演,避免延緩甚至再次錯失中國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良機,任何思考或實踐中國改革的人都應當以理性的思維優(yōu)先考慮到:基于中國現(xiàn)實國情,如何以盡可能小的成本與代價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主動改革路線圖?
二、如何準確把握主動改革
中國的主動改革應當是在黨和政府掌握改革主動權的情況下,基于現(xiàn)實國情,有計劃有步驟并有改革最終目標地推動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全方位改革。進而言之,中國主動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在確保國家統(tǒng)一和主權完整基礎上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以構建符合國情和人性基礎上的民主法治社會。
1.“相應保障”條件成就基礎上的全方位改革
基于現(xiàn)實國情,中國的主動改革應當實行“相應保障”條件成就基礎上的經(jīng)濟、社會、政治等體制領域的全方位改革。一方面,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實施;另一方面,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適應深化改革中可能出現(xiàn)的社會穩(wěn)定及其國家安全問題,以避免改革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兩者相互配合與協(xié)調,以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這要取決于執(zhí)政黨的政治勇氣與智慧。
這種“相應保障”條件成就基礎上的全方位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健全和完善市場經(jīng)濟體制。其中,按照先易后難,并以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為目標,推動國企、土地(尤其農(nóng)村土地)、金融、財稅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沒有上述領域的徹底改革,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2)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快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3)大力推行社會建設。一是加強教育體制改革,實行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目標,尤其加強少數(shù)民族和落后地區(qū)的教育投入;二是推動醫(yī)療衛(wèi)生、養(yǎng)老保險、住房等領域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三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合理縮小個人、民族和地區(qū)差距,形成“橄欖型社會”等。(4)改革與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尤其要深化維、藏、蒙等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改革,適當借鑒特別行政區(qū)和聯(lián)邦制的某些經(jīng)驗,正視并妥善解決民族問題,并為解決臺灣問題預留空間。(5)加強軍隊和公安武警改革。一是軍隊和公安武警反腐要法治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包括法律人才在內的高素質人才充實到軍隊和公安武警系統(tǒng),加快軍隊和公安武警的現(xiàn)代化進程[1]李昌庚:《維穩(wěn)與改革的博弈與平衡——我國社會轉型期群體性事件的定性困惑及其解決路徑》,〔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從而為改革提供軍事保障。(6)在上述改革基礎上,實現(xiàn)寬容歧見和包容共生,逐漸形成社會共識的主流核心價值觀。這是政黨政治的基石,也是避免社會轉型期社會撕裂和族群對立的重要條件。(7)在上述改革基礎上,隨時把握時機和條件成熟度,適時同步推進人大、司法和政黨等領域的政治體制改革。
2.正確認識主動改革可能產(chǎn)生的問題
(1)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可能影響并阻礙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基于現(xiàn)實國情,政治體制改革超前,容易出現(xiàn)前已述及的災難性后果。但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到一定時期又常常阻礙國企、土地、金融、財稅、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養(yǎng)老保險等經(jīng)濟體制及其他領域的進一步改革。這在我國過去長期以來所謂漸進式改革中已經(jīng)凸顯此問題。同樣,在“相應保障”條件成就基礎上的主動改革進程中也不排除此類問題的重復出現(xiàn)。這是我國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一直難以健全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國改革的困境所在。這既是我國尋求主動改革的理由所在,也是主動改革需要減少或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
對此,筆者認為,主動改革與過去長期以來所謂漸進式改革最大的區(qū)別在于,主動改革應當有著明確的改革路線圖及其最終改革目標,有著可掌控的改革期待[2]這種“改革期待”又不能拖得太久,否則臺灣問題、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國內外因素都有可能增大改革的風險系數(shù)。。而這種可掌控的改革期待,可以力求探索出在可掌控的政治體制改革范圍內,能夠深化超出政治體制層面的經(jīng)濟體制及其他領域改革的路徑,從而降低或緩解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所帶來的改革阻力,盡可能使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取得相對成效,從而為政治體制改革奠定基礎。即便如此,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的嘗試與實踐,都有利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而這些要取決于黨和政府的主動改革目標及其改革路線圖的制定和實施。
(2)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可能因此而惰化或延緩政治體制改革。無論過去長期以來所謂漸進式改革還是當下提出的主動改革,均要優(yōu)先考慮到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雖然經(jīng)濟體制等相關領域改革尤其社會保障改革是社會平穩(wěn)轉型的重要條件,但如果把握不當,有時可能因此而惰化或延緩政治體制改革。這在我國過去長期以來所謂漸進式改革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此問題。這也是我國當下主動改革進程中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雖然主動改革有著可掌控的改革期待,從而能夠消解這一問題,但如果把握不當,尤其時間拖延、既得利益障礙、不確定外因等因素的干擾,都有可能使這一問題重復出現(xiàn),可能因此延續(xù)所謂漸進式改革而錯失社會轉型良機。而這同樣要取決于黨和政府的主動改革目標及其改革路線圖的制定和實施。
(3)尋求社會平穩(wěn)轉型是否成為一種阻礙改革的理由或借口?這是某些尋求激進變革的人試圖提出的質疑,也是我國主動改革路徑選擇所必須澄清的問題。
有人或許提出印度、南非甚至柬埔塞、緬甸、尼泊爾等若干發(fā)展中國家社會轉型進程并沒有我國所一直強調的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建設等主張,筆者認為,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認識:
①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很多國家國情與中國差異很大,即使同樣擁有眾多人口、民族和地域廣闊的印度也與中國國情差異很大,比如印度是一個從英國殖民地獨立的國家等。中國的特殊國情不在于人口眾多、農(nóng)業(yè)人口多、人口素質低、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和儒家文化等,而在于民族問題、臺灣問題以及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慣性和威權政治所形成的國民特性、文化錯位、價值模糊與沖突等。有人常以前者作為回避、阻礙或延緩改革的理由或借口,這實際上是濫用國情。就如同陳獨秀早就說過,不要以所謂的國粹或國情的鬼話來搗亂革新[1]參見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轉引自公丕祥:《中國的法制現(xiàn)代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頁。。而后者才是中國社會轉型及其改革路徑選擇需要考量的真正特殊國情。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往往又使中國問題更為復雜。
②歷史慣性延續(xù)下的當今中國有時間和條件以史為鑒。凡事不能簡單地以歷史結果來考量后來者,還要考量其過程有哪些經(jīng)驗教訓可以吸取。因此,不能以原蘇聯(lián)東歐國家以及許多亞非拉國家的現(xiàn)狀簡單地要求中國也必須立即如此。歷史慣性已將中國推向今天,從而使當今中國有時間和條件以史為鑒,中國改革哪些成本與代價必須付出,哪些成本與代價可以避免或減輕。比如西方國家盡管政黨林立,但其主流價值觀是一致的,從而使其政黨政治很成熟。相比較而言,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尤其威權政治國家在民主化歷史進程中曾經(jīng)歷過乃至現(xiàn)在依然存在社會撕裂、族群對立等街頭政治和民粹暴政。比如韓國、印尼、伊拉克、埃及、敘利亞、泰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等[2]我國臺灣地區(qū)社會轉型進程中的政治對立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等政黨之間的“統(tǒng)獨”歷史遺留問題,還不單純是社會轉型主流價值觀爭議。當然,這種政治對立問題目前已經(jīng)相對緩解。。我國清末民國初期也是如此。那么,我國是否可以盡可能創(chuàng)造條件逐漸形成主流核心價值觀以及其他有效措施,從而避免或減輕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街頭政治和民粹暴政?又如原蘇聯(lián)東歐國家社會轉型中出現(xiàn)了民族沖突、國家分裂等社會動蕩及其人權災難。那么,我國在確保民族自治權及其公民權利的基礎上,可否創(chuàng)造條件避免這種問題發(fā)生?等等。
但如同筆者早就申明,以上情形均不是回避、阻礙或延緩改革的理由和借口,而是基于特殊國情如何改革的問題。這也是筆者為何一直主張主動改革的理由所在。雖然時至今日的歷史慣性下中國以史為鑒的改革可能因此在一定時期內延緩甚至限制公民的權利訴求和利益表達,雖然筆者一直同意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權利更為重要的觀點[3]See Roscoe Pound,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William S.Hein&Co.,Inc.,1995,p.53.,但基于特殊國情的中國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也是國際社會的要求,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最終使私人權利最大程度的彰顯。
三、主動改革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避免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
改革實踐中存在一個誤區(qū),認為權力分散有助于遏制權力、遏制腐敗,這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此話本身并不錯,但要看權力來源及其性質的特定語境。語境使用不當,貽害無窮,并因制度缺陷而將人性“惡”的一面充分凸顯。
自古以來,無論專制社會還是民主社會,一旦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必犯人性大忌,也必然容易產(chǎn)生問題。比如我國清末的光緒和慈禧關系等。民主政治的關鍵在于,權力民選以及國家或政權意義上的權力分工和制衡,如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等。但無論立法權、行政權還是司法權,每一種權力本身只能有一個中心,不能出現(xiàn)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實行同一種權力中心下的職能分工,尤其是行政權的核心地位得到保障,這是世界各國摸索出的共同規(guī)律。無論總統(tǒng)制國家還是議會制國家等。如果說國家或政權意義上的權力分工和制衡是基于人性的制度安排,那么每一種權力本身只能有一個中心也是基于人性的制度安排。
從我國目前來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有識之士已經(jīng)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令人費解的是,在社會轉型改革過程中,迫于權力制約和反腐壓力,基于威權政治的基本制度背景下,有時采取同一種權力內部的不當拆分和制衡,或采取臨時性應付改革舉措,比如有些省市目前試行黨政一把手不直接管理“人財物”等做法,都有可能違背權力運行規(guī)律,形成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其結果必然制造內耗和沖突,容易導致政令不暢、改革措施難以到位等缺陷,尤其不符合社會轉型期權力相對集中的改革要求。
從中央層面來看,已經(jīng)初步解決這個問題,即國家主席集軍委主席和黨的總書記一身,是行政權核心,國務院是其行政內閣。當然,這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從地方、部門和單位層面來看,我國各地方、部門、單位還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即黨委書記和省長、市長、廳長、局長、院長、校長等行政負責人還存在分設問題,其結果必然容易造成權力中心二元化。比如黨委領導下的省長負責制、市長負責制、院長負責制等,理論上都很好說,立法和規(guī)章制度上也規(guī)定的很清楚,但實踐中很容易產(chǎn)生問題。即黨委與行政以及黨委書記與行政負責人之間可能出現(xiàn)的職能沖突與相互內耗。
歷史上為了解決黨政不分問題,又要考慮加強黨的領導,曾有部分省份采取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做法,但這不僅不能解決黨委和政府的權力二元中心問題,而且還導致人大立法權和行政權的職能錯位問題。實際上,要解決的不是黨政分開問題,而是如何使中國共產(chǎn)黨從革命政黨向執(zhí)政黨轉型問題,這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能否平穩(wěn)轉型。
考慮到社會轉型期國情,筆者認為,至少目前可以考慮,凡是條件具體的,即將黨委書記和地方、部門和單位行政負責人集于一身,再另設一個副書記專職負責黨務;對于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擔任行政負責人時,要另設書記一職;由行政負責人統(tǒng)一組閣,人大審批;組織人事權和財權等統(tǒng)一歸口于行政負責人等。除非黨務活動外,對外活動應統(tǒng)一以行政負責人的行政職務出現(xiàn)。同樣,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也是如此。這樣做至少有如下幾點好處:一是避免權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二是有助于中國共產(chǎn)黨向執(zhí)政黨轉型的基礎鋪墊,因為提名執(zhí)政黨負責人擔任行政負責人符合政黨政治的國際慣例;三是有助于精簡國家機構及其公務人員,實現(xiàn)政府職能轉型,減少或避免黨委與政府之間職能交叉與沖突,降低內耗和公務成本;四是有利于社會轉型改革行政權集中的更為迫切要求,以便更好地推動改革等。
至于行政權內部,有些情形下可以采取決策、執(zhí)行和監(jiān)督職能分離的制度設計,比如行政處罰中的罰沒分離制度等。這并不違背行政權集中的基本要求。理由在于:一是這僅是行政權內部的職能分工,無論決策、執(zhí)行還是監(jiān)督職能都在其上一層級行政負責人統(tǒng)領下;二是決策、執(zhí)行和監(jiān)督職能是分別機構設置,每一機構的行政權本身又是集中的。
2.創(chuàng)造相對穩(wěn)定和默契的國際環(huán)境
“獨立自主”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原則僅具有相對意義,尤其愈益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國家的科技創(chuàng)新、經(jīng)濟發(fā)展、環(huán)境污染、人權保障等都或多或少地牽涉到世界或受到國際社會影響。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涉及到民族問題、臺灣問題、領土紛爭等特殊國情。
對于中國而言,即便清末民國時期,在自身存在問題時,不確定的外因,加上國內的不滿偏激情緒,也存在既有改革或操之過急的革新失敗的現(xiàn)象[1]比如清末時期,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等不確定外因,從而導致其后倉促的“戊戌變法”失敗,也打亂了恭親王等人原先就已推行的主動改革等。。如果當時政府在確保國家主權前提下,能夠妥善處理好國內外關系,主動穩(wěn)步推進改革,或許都有可能改變歷史。這對于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今中國,基于封建專制社會和威權政治的歷史慣性,以及民族問題、臺灣問題、領土紛爭等特殊國情,尤其要以史為鑒。不確定的外因,加上國內的不滿情緒,都有可能使改革增加危險變數(shù)。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雖然有些國家或組織或許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但國際社會總體而言不愿意看到像中國這樣龐大國家出現(xiàn)一場類似于原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及中東地區(qū)等諸如此類的人權災難[1]李昌庚:《官員財產(chǎn)申報制度是否可以起航?》,〔北京〕《團結》2013年第3期。。因為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動蕩以及13億人口的社會轉型無不牽涉到世界各國利益及其人類文明。而這也正是我國在主動改革過程中需要清醒把握、妥善處理和充分利用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基于特殊國情,在黨和政府掌握改革主動權的情況下,在確保國家統(tǒng)一、主權完整等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需要充分對國際因素加以趨利避害,與美國、俄羅斯、周邊國家以及其他世界主要國家盡可能就民族問題、臺灣問題、領土紛爭等達成默契,管控分歧,妥善處理好國際關系,以便為我國改革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從而贏得足夠的改革時間和空間,以確保社會平穩(wěn)轉型。
3.準確把握“三個理性看待”
(1)理性看待普通百姓尤其農(nóng)民
在我國改革進程中,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存在這么一種不良傾向,即認為普通百姓尤其農(nóng)民文化素質低下,因而很多改革條件還不具備。這種濫用所謂“國情”的不良傾向往往或多或少影響到改革決策,從而延誤改革良機。這應當是我國當下主動改革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否則又將重蹈過去所謂漸進式改革陷阱。
其實,文化素質高低只是專業(yè)知識及其職業(yè)分工的差異,但絕不可認為文化層次高的人就一定比那些普通百姓聰明多少。農(nóng)民首創(chuàng)的農(nóng)村生產(chǎn)承包責任制即是例證。這并非是政治家、經(jīng)濟學家或法學家等所創(chuàng)造,而恰是那幫源于生活實踐的農(nóng)民本能追求,他們才不會想到“公有制”、“私有制”等諸如此類的無謂爭論和偽命題干擾,想到的就是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也正是許多普通百姓嘲笑某些文人“迂腐”的原因所在。
不同的職業(yè)及其生活圈體現(xiàn)了不同的游戲規(guī)則及其話語體系。只不過我們當中有些源于生活實踐而深諳世道的文化人利用文字表述從而掌握特定話語權而已,但這僅是專業(yè)知識及其職業(yè)分工的差異,并不意味著比普通百姓聰明多少。
因此,每一個人都應當懷揣一顆謙卑之心、敬畏之情去尊重周圍的每一個人,去遵守共同的游戲規(guī)則,并以此心態(tài)學習、工作和生活。如果我國改革始終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或許諸如農(nóng)村土地改革、國企改革、教育改革等也就少了許多無謂爭論和偽命題干擾。雖然我國尚有許多普通百姓尤其農(nóng)民存在文化素質較低的現(xiàn)象,但這只是如何改革的考量因素,而絕非回避、阻礙或延緩改革的理由和借口。就如同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不能借口民眾的智識低下,就拒絕給予他主人的地位[2]《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13頁。。因此,任何政黨或派系,其政治游戲規(guī)則的最終落腳點都要回到普通百姓的期盼上。這也是黨和政府必須始終堅持的改革落腳點。
(2)理性看待少數(shù)民族及其民族問題
前已述及的“理性看待普通百姓尤其農(nóng)民”也同樣適用于少數(shù)民族。然而,針對我國民族問題,許多人對某些少數(shù)民族存在認識誤區(qū),尤其我國當前改革進程中,則有特別需要闡述的必要。
雖然有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還相對貧窮,發(fā)展進程還較為緩慢,這不僅因為自然條件、國家政策、歷史因素等,而且還因為有些少數(shù)民族在特定語言文化環(huán)境中相對缺乏競爭力等因素。但這并非意味著民族間的智慧差異。甚至有些少數(shù)民族在其自身特定語言文化環(huán)境下有著更為特別的生存法則,而非其他民族以其自身邏輯思維所能充分理解。
因此,如果說人與人之間要懷揣一顆謙卑之心、敬畏之情相處,并遵守共同的游戲規(guī)則,那么民族間也是如此。這應當成為塑造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理念。如果說人類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民族間的強盜邏輯,那么對于社會主義中國尤其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更要力求避免這樣的錯誤發(fā)生。如果始終清醒地把握這一點,或許有助于反思民族政策及其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包括所謂“援疆”、“援藏”政策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或許在尊重民族自治的基礎上更多地通過平等“交流”和“合作”往往更能獲得相互理解、支持、尊重和自然融合。我國應當以此理念更多地讓維、藏、蒙等少數(shù)民族尤其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精英主動融入社會轉型改革主流中。比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可以考慮讓維、藏、蒙等主要少數(shù)民族甚至海外華人華僑各推選一個代表參加。等等。這不僅有利于解決民族問題,也有利于凝聚更多的改革正能量,進而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基礎上的社會平穩(wěn)轉型。
(3)理性看待政府官員
自古以來,在缺乏民主程序政權更替的環(huán)境下,都存在著來自民間及其知識分子對政府官員不滿的偏激情緒,這種情緒一旦膨脹,加之不確定內外因而致改革失敗,將使社會付出沉重代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有人要么“假大空話”,認識不到問題或回避問題;要么一味地抱怨問題,而未回答“如何解決問題”。前者粉飾太平,但無助于解決問題;后者雖能起到一定監(jiān)督和促進作用,但也難以根本解決問題,甚至在特定時期基于某種不確定的內外因而致已有改革失敗。歷史已有教訓。其實,黨和政府中許多有識之士源于社會實踐已經(jīng)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問題癥結所在。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以盡可能小的改革成本與代價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一味地“粉飾太平”或“牢騷滿腹”都可能給改革添亂。
在黨和政府主動改革的前提下,基于特殊國情,立足于當今中國現(xiàn)狀,以史為鑒,如何以盡可能小的改革成本與代價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轉型及其國家現(xiàn)代化,是國人尤其是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亟需考量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就不能簡單地以某些民主法治標準衡量中國已經(jīng)主動改革的社會轉型特殊時期的某些現(xiàn)象,而應當以民主法治為基礎,準確理解歷史慣性下當今中國推動改革的諸多游戲規(guī)則,否則有可能給改革添亂。而這關鍵取決于我國主動改革路線圖的制定、實施及其改革方向。如果始終清醒地把握這一點,就能避免許多資源浪費和時間消耗,就能凝聚更多的改革正能量,形成改革共識。
〔責任編輯:錢繼秋〕
Initiative Reform:the Ideal Choice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Changgeng
Although initiative reform is painful,difficult and even premature death,any passive reform and subsequent changes may easily bring about disastrous consequences,especially on Chinese special conditions.Although we do not regard China's initiative reform with the attitude of blind optimism or taking it for granted,China has been pushed to today by the historical inertia,so China has time and conditions to learn from history,initiative reform is the ideal choice for China to achieve social smooth transformation!But we need to be more cautious and sober attitude towards China's initiative reform.During the process of initiative reform,China should avoid the dual power center or ev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ower center,create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nd rationally treat the common people,especially farmers,ethnic minoriti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which can thus form a reform force,and reduce or avoid reform misjudg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special conditions;learning from history;initiative reform;smooth transformation.
李昌庚,南京曉莊學院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 210029
本文得到江蘇省高校優(yōu)秀中青年教師和校長境外研修計劃和江蘇省“333”工程項目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