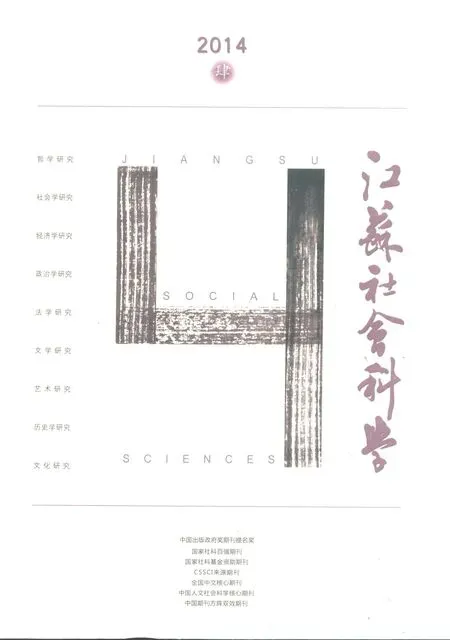合作的政治
——憲政的形而下解讀
趙娟
合作的政治
——憲政的形而下解讀
趙娟
在形而下層面,憲政可以被解讀為合作的政治,合作的意愿、規(guī)則和能力成就了憲政這一人類(lèi)社會(huì)的政治形態(tài)。我們關(guān)注憲政,并非因?yàn)槠鋬r(jià)值的終極正確,而是因?yàn)樗蔷S系生存安全的有用的工具,是迄今為止人類(lèi)找到的有效的政治組織和運(yùn)作方式。
憲政 合作 憲法 政治 實(shí)踐
一、問(wèn)題的提出
近一年來(lái),有關(guān)憲政的“性質(zhì)”之爭(zhēng)成為知識(shí)界的“公共事件”[1]一般認(rèn)為,此次爭(zhēng)論緣起一篇否定憲政的文章,參見(jiàn)楊曉青:《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http://www. aisixiang.com/toplist/view.php?pid=74604,2013年5月30日訪問(wèn)。。總體看來(lái),此番爭(zhēng)論主要集中在意識(shí)形態(tài)問(wèn)題上。那么,憲政就一定是一個(gè)與意識(shí)形態(tài)相關(guān)聯(lián)的命題?一提及憲政,則必定與某些價(jià)值相關(guān)聯(lián)?除此之外,憲政還有其他存在的理由嗎?
本文的問(wèn)題意識(shí)正在于此。毫無(wú)疑問(wèn),憲政是一個(gè)充滿價(jià)值色彩的存在,但在價(jià)值之外,憲政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我們把憲政的價(jià)值研究看作是“道、本”層面的“形而上”研究,那么,去價(jià)值化或者去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研究即可歸為“器、術(shù)”層面的“形而下”研究[2]《易經(jīng)·系辭》云:“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yè)。”。在筆者看來(lái),在非此即彼的價(jià)值選擇中,實(shí)際上是很難有確定的“一致性”或者“正確性”的,尤其在一個(gè)價(jià)值多元的異質(zhì)化社會(huì),更是如此;形而下研究的一個(gè)顯而易見(jiàn)的好處是,可以讓我們遠(yuǎn)離感性的和情緒化的判斷——因?yàn)閼{借感性和情緒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將憲政“妖魔化”抑或“神圣化”。本文即是一種形而下研究的努力,試圖討論的一個(gè)基本觀點(diǎn)是:在形而下層面,憲政可以被解讀為合作政治,正是合作的意愿、規(guī)則和能力成就了憲政。
二、愿意合作:憲政的起點(diǎn)
如果說(shuō)憲政啟始于人類(lèi)的合作意愿,大抵是不會(huì)錯(cuò)的。憲政之前的人類(lèi)政治狀態(tài)的形成,多依賴于武力和偶然的機(jī)遇,“政府的建立出于機(jī)遇和強(qiáng)力是大多數(shù)人類(lèi)社會(huì)普遍的現(xiàn)象。”[1]〔美〕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fù)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毛壽龍譯,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1999年版,第3頁(yè),第13頁(yè)。合作,確立了憲政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新型政治模式。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yàn)閼椃ㄔ诤艽蟪潭壬鲜且环N契約,而契約來(lái)自于合作。
這樣的合作可以是被動(dòng)的。最有說(shuō)服力的例子是英國(guó)。1215年的《大憲章》——人類(lèi)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就是一個(gè)契約,是國(guó)王和貴族之間的契約,這是國(guó)王——約翰王在貴族的逼迫之下被迫接受的,他的合作顯然是非自愿的。盡管如此,他的合作仍然構(gòu)成了憲政的起點(diǎn)。1688年“光榮革命”延續(xù)了合作的傳統(tǒng),這回是議會(huì)中的占主導(dǎo)勢(shì)力黨派與國(guó)王之間的斗爭(zhēng):趕跑了一個(gè)不愿合作的國(guó)王——詹姆斯二世,迎回了愿意合作的國(guó)王和女王——威廉和瑪麗。有意思的是,威廉和瑪麗因?yàn)橥夂献鳎庞袡C(jī)會(huì)成了英國(guó)的國(guó)王和女王,而在成為統(tǒng)治者后,他們繼續(xù)保持了合作的傳統(tǒng),從而有可能保持和延續(xù)了其地位。在威廉和瑪麗的合作下,議會(huì)1689年通過(guò)了《權(quán)利法案》,正式確立了國(guó)王必須服從法律和議會(huì)至上原則,英國(guó)由此結(jié)束了幾百年來(lái)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政治紛爭(zhēng),走上了穩(wěn)定的憲政之路。
這樣的合作也可以是主動(dòng)的。1787年美國(guó)聯(lián)邦憲法就是一個(gè)合作的產(chǎn)物。美國(guó)立憲的直接目的或者出發(fā)點(diǎn)是為了解決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所面臨的政治問(wèn)題:避免歐洲各國(guó)的混戰(zhàn)局面,避免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的弊害,補(bǔ)救邦聯(lián)制度的失敗,從而建設(shè)和平而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2]〔美〕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fù)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毛壽龍譯,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1999年版,第3頁(yè),第13頁(yè)。。然而,立憲過(guò)程并不順利。在費(fèi)城的制憲會(huì)議上,各州代表為了各自代表的利益而對(duì)新憲法進(jìn)行爭(zhēng)論,一時(shí)間很難形成一致意見(jiàn)。比如,在政府權(quán)力的結(jié)構(gòu)安排上,就存在“弗吉尼亞方案”與“新澤西方案”之爭(zhēng),制憲會(huì)議曾一度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分歧巨大。但最終在辯論中達(dá)成了共識(shí),以相互的讓步、妥協(xié)代替了對(duì)立、沖突,聯(lián)邦憲法得以產(chǎn)生。從歷史上看,美國(guó)的立憲政治是人類(lèi)社會(huì)第一次嘗試靠“思考和選擇”,靠自由建議、公開(kāi)討論以及非強(qiáng)迫的人民贊許和同意來(lái)實(shí)行統(tǒng)治。憲法真正成了基于社會(huì)共識(shí)而產(chǎn)生的一種對(duì)政府和人民都具有約束力的全民政治契約。主動(dòng)的合作立憲是美國(guó)憲政留給世界的一大遺產(chǎn),它證明:人類(lèi)能夠通過(guò)理智的思考和公開(kāi)的選擇來(lái)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
在此,有必要討論與憲法密切關(guān)聯(lián)、對(duì)憲政的發(fā)展起到過(guò)顯著作用的社會(huì)契約論。學(xué)者們對(duì)于契約論思想的認(rèn)識(shí)往往將其與國(guó)家、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合法性聯(lián)系在一起。一個(gè)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契約論的目的是為國(guó)家權(quán)力的產(chǎn)生和維持提供合法性依據(jù),或者說(shuō)是為界定什么是合法國(guó)家權(quán)力提供標(biāo)準(zhǔn)。”[3]張千帆:《憲法學(xué)導(dǎo)論:原理與應(yīng)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頁(yè)。這樣的解說(shuō)是合理的,也是深刻的,但其僅僅涉及到了契約論的本質(zhì)——形而上的價(jià)值,而忽視了契約本身對(duì)于國(guó)家的功能——形而下的意義:國(guó)家、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存在也可以是合作的產(chǎn)物,是一種合意的表達(dá)過(guò)程和結(jié)果。不論是霍布斯的“專制契約論”,還是洛克的“自由契約論”、盧梭的“民主契約論”,都在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共同點(diǎn):國(guó)家、國(guó)家權(quán)力應(yīng)該是基于同意的合作的存在。相比較而言,霍布斯的貢獻(xiàn)是劃時(shí)代的。在近代思想史上,霍布斯承繼亞里士多德的知識(shí)傳統(tǒng),第一次把政治理解為或者構(gòu)想為合作的結(jié)果:人作為政治動(dòng)物的自主選擇。在霍布斯看來(lái),與某些能群處相安地生活的動(dòng)物如蜜蜂、螞蟻等不同,盡管它們也被亞里斯多德列為政治動(dòng)物[4]〔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30頁(yè),第131頁(yè)。,人類(lèi)的協(xié)議是根據(jù)信約而來(lái),信約是人為的[5]〔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30頁(yè),第131頁(yè)。。“如果要建立這樣一種能抵御外來(lái)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權(quán)力,……那就只有一條路:把大家所有的權(quán)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gè)人或一個(gè)能通過(guò)多數(shù)的意見(jiàn)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gè)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就不僅是同意或協(xié)調(diào),而是全體真正統(tǒng)一于唯一人格之中;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訂立信約而形成的,其方式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個(gè)其他的人說(shuō):我承認(rèn)這個(gè)人或這個(gè)集體,并放棄我管理自己的權(quán)利,把它授予這人或這個(gè)集體,但條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權(quán)利拿出來(lái)授予他,并以同樣的方式承認(rèn)他的一切行為。這一點(diǎn)辦到之后,像這樣統(tǒng)一在一個(gè)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稱為國(guó)家,在拉丁文中稱為城邦。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Leviathan)的誕生。”[1]〔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31-132頁(yè),第132頁(yè),第575頁(yè)。霍布斯這一開(kāi)創(chuàng)性思想無(wú)疑具有宗教根源,他把利維坦的誕生比喻為“活的上帝的誕生;我們?cè)谟郎恍嗟纳系壑滤@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從它那里得來(lái)的。”[2]〔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31-132頁(yè),第132頁(yè),第575頁(yè)。他特別區(qū)分了“以立約而形成”的“政治的國(guó)家”和非以立約而“以力取得的國(guó)家”,聯(lián)系到對(duì)《圣經(jīng)》的理解,他認(rèn)為,“在猶太國(guó)中,上帝本身由于與百姓立約而成了主權(quán)者。這些百姓于是便被稱為特屬的民,以示區(qū)別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對(duì)于其余的民族,上帝不是根據(jù)他們的同意,而是根據(jù)他本身的權(quán)力進(jìn)行統(tǒng)治的。”[3]〔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31-132頁(yè),第132頁(yè),第575頁(yè)。霍布斯所設(shè)想或者設(shè)計(jì)的按約建立的國(guó)家即政治的國(guó)家在他之前不是歷史的事實(shí),但是,按約來(lái)確定國(guó)王的權(quán)力和臣民的權(quán)利卻是《大憲章》的功能;同時(shí),《大憲章》的契約形式也是霍布斯展開(kāi)政治國(guó)家討論的起點(diǎn)——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正是通過(guò)契約而組成的[4]“利維坦”即Leviathan,來(lái)自圣經(jīng),是一種力大無(wú)窮的巨獸的名字,“利維坦”作為書(shū)名,意在比喻一個(gè)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參見(jiàn)〔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出版說(shuō)明,第4頁(yè)。,或者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只有通過(guò)契約組成的國(guó)家才可能是強(qiáng)大的。這樣看來(lái),霍布斯對(duì)于政治的國(guó)家的構(gòu)想并非“憑空臆念”。合作意味著人類(lèi)的政治可以成為“爭(zhēng)論與妥協(xié)”的存在,而不再是“刀劍乒乓作響”的結(jié)果。
三、合作規(guī)則:憲政的基準(zhǔn)
憲法是政治規(guī)則的載體。幾乎所有現(xiàn)代國(guó)家都以憲法文本的形式為本國(guó)政治設(shè)定最基本的規(guī)則和要求。同時(shí),與法律一樣,憲法具有規(guī)范性特質(zhì),規(guī)范性在于其確定性和強(qiáng)制性的品格,這樣的特質(zhì)使得憲政區(qū)別于任意、反復(fù)無(wú)常、隨心所欲的政治,從而防止統(tǒng)治者的恣意和放縱,“朕即國(guó)家”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即是恣意政治的典型表達(dá)。憲政狀態(tài)下的統(tǒng)治者不可以“根據(jù)其自由的無(wú)限制的意志及其偶然興致或一時(shí)的情緒頒布命令和禁令”[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xué)法律哲學(xué)與法律方法》,鄧正來(lái)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yè)。,因而作為規(guī)則之治的憲政是可預(yù)見(jiàn)的政治。依據(jù)規(guī)則而展開(kāi)的憲政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不確定性,也將政治的不確定性風(fēng)險(xiǎn)降到了最低點(diǎn)。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盡管在總體的法律傳統(tǒng)上,美國(guó)承繼了英國(guó),但在憲法問(wèn)題上,美國(guó)卻選擇了不同于英國(guó)的另外的形式——制定成文憲法。一位學(xué)者曾經(jīng)這樣論述:“英國(guó)自由主義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認(rèn)為,英國(guó)不需要一部憲法,因?yàn)橛?guó)的歷史以在政治理想和倫理價(jià)值上一種普通合意的形式,提供了對(duì)自由的唯一真實(shí)的保障。他認(rèn)為如果沒(méi)有這種合意,任何一紙條文都根本無(wú)法為自由提供保障。……沒(méi)有傳統(tǒng)的支持,一部成文憲法不過(guò)是一紙空文;而有了那種傳統(tǒng),一種成文憲法就沒(méi)有必要。但是美國(guó)人畢竟看到了全部的英國(guó)歷史。美國(guó)人采用了法律書(shū)面形式,與法國(guó)人一樣,它是成文的,與法國(guó)人不同,它更多地建立在英國(guó)政治法律史的制度和習(xí)慣做法的基礎(chǔ)之上,而非建立在理想主義和革命言詞的基礎(chǔ)之上。”[6]〔美〕肯尼思·W·湯普森編:《憲法的政治理論》,張志銘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97年版,第87頁(yè)。美國(guó)選擇成文憲法就是為了避免英國(guó)曾經(jīng)的“過(guò)往”,是對(duì)“反反復(fù)復(fù)之政治”的警惕,合作的意愿和傳統(tǒng)是重要的,以白紙黑字寫(xiě)下來(lái)合作的規(guī)則形式可能是更重要的。
人類(lèi)需要權(quán)力,因?yàn)樾枰J聦?shí)上,政府權(quán)力是合作政治不可或缺的,沒(méi)有政府權(quán)力,政治合作無(wú)從談起。對(duì)于政府權(quán)力的服從是普通民眾的合作方式,文明社會(huì)中人的生存和安全須以受治于國(guó)家的強(qiáng)制力為前提。這也是為什么霍布斯一再?gòu)?qiáng)調(diào)主權(quán)的無(wú)限即至上性[1]〔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5年版,第161-162頁(yè)。,他的意思并不是說(shuō)主權(quán)絕對(duì)或毫無(wú)邊界,而是說(shuō)主權(quán)必須具有強(qiáng)制力,這是文明社會(huì)存在的基礎(chǔ)和保障,民眾對(duì)于權(quán)力的服從也是信約的內(nèi)容。對(duì)于政府而言,權(quán)力是其合作的條件,而對(duì)于權(quán)力的控制,則是迫使政府按照合作方式行使權(quán)力的機(jī)制。道理并不復(fù)雜:合作意味著利益的共享,意味著每個(gè)人(每個(gè)群體)的利益都需要得到承認(rèn)和保護(hù),在強(qiáng)者與弱者構(gòu)成的社會(huì),不情愿合作的大多是強(qiáng)者,因?yàn)樵谌跞鈴?qiáng)食的規(guī)則下,強(qiáng)者是利益的獲得者,他可以依靠其強(qiáng)勢(shì)地位,占取和壟斷利益,合作與否意義不大。相對(duì)于普通民眾而言,擁有權(quán)力的政府也是強(qiáng)者,自然也不會(huì)自覺(jué)自愿的合作,控制權(quán)力實(shí)際上是強(qiáng)迫政府進(jìn)行合作,迫使其不再回歸到叢林法則的狀態(tài)中去。
憲政從其誕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限權(quán)的胎記。這一點(diǎn)在憲政發(fā)軔國(guó)——英國(guó)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如果說(shuō)世界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1215年的大憲章在形式上確立了限制王權(quán)的規(guī)則,那么,英國(guó)法治所體現(xiàn)的則是實(shí)質(zhì)意義上的限權(quán)政治。柯克的名言“國(guó)王在萬(wàn)萬(wàn)人之上,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就是英國(guó)憲政的經(jīng)典表白。根據(jù)學(xué)者的研究,英國(guó)十五世紀(jì)即形成了良好的政制:英格蘭“政治且王室的”統(tǒng)治即英格蘭“政治且王室的”政體構(gòu)造。“政治的”意味著政治體的政治權(quán)威的終極根源來(lái)自于作為一個(gè)團(tuán)體的政治體本身,“法律對(duì)于政治體能夠作為一個(gè)團(tuán)體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并代表政治體自身對(duì)王權(quán)不逾越其在政治體中的本份發(fā)揮制約功能”;“王室的”意味著“政治體必須通過(guò)王權(quán)才能從一個(gè)單純團(tuán)體發(fā)展為一個(gè)賦有明確政府形式的政治體”,而且通過(guò)集中化和體系化的王權(quán),“保證王國(guó)的良好秩序、實(shí)現(xiàn)政治體的內(nèi)部整合”。兩者結(jié)合的意義是:“王權(quán)所代表的地域集中化權(quán)力及其所支持的領(lǐng)土性統(tǒng)一秩序,是在政體中受到政治體自身的限定的。”[2]參見(jiàn)楊利敏:《探尋英格蘭良好政制的“道理”——〈論英格蘭的法律與政制〉導(dǎo)讀》,http://www.calaw.cn/article/ default.asp?id=7179,2012年6月8日訪問(wèn)。正是這種“政治且王室”的統(tǒng)治將英國(guó)導(dǎo)向了現(xiàn)代憲政國(guó)家。英國(guó)這種政制的形成具有“憲政發(fā)生學(xué)”意義[3]楊利敏博士文章中用到的“憲政發(fā)生學(xué)”這個(gè)詞,極為形象、恰當(dāng)?shù)卣f(shuō)明了英國(guó)憲政可能發(fā)生、可以發(fā)生的內(nèi)在緣由和外在條件。參見(jiàn)楊利敏:《探尋英格蘭良好政制的“道理”——〈論英格蘭的法律與政制〉導(dǎo)讀》,http://www.calaw. cn/article/default.asp?id=7179,2012年6月8日訪問(wèn)。,它可以解釋,為什么同時(shí)代的歐洲大陸國(guó)家比如法國(guó)沒(méi)有走上憲政的方向。法國(guó)同樣是王室的統(tǒng)治,但因?yàn)樗鼉H僅是“王室的”,而非“政治的”,換言之,王室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規(guī)制,缺乏這樣的掣肘,權(quán)力是無(wú)所顧忌的,王室的統(tǒng)治就是恣意的,所以這樣的統(tǒng)治與憲政的方向是相背的[4]參見(jiàn)楊利敏:《探尋英格蘭良好政制的“道理”——〈論英格蘭的法律與政制〉導(dǎo)讀》,http://www.calaw.cn/article/ default.asp?id=7179,2012年6月8日訪問(wèn)。。
在限權(quán)問(wèn)題上,美國(guó)制憲者走得更遠(yuǎn)。美國(guó)聯(lián)邦憲法被設(shè)計(jì)成為便于實(shí)施的限權(quán)規(guī)則,憲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序性的”,是可操作的,以有利于其限權(quán)功能的發(fā)揮。政府權(quán)力既是必需的、也是必須受到限制的,不受限制的政府如同沒(méi)有政府一樣,都是危險(xiǎn)的,如何平衡這樣的糾結(jié)關(guān)系,分權(quán)是唯一出路,美國(guó)憲法通過(guò)分權(quán)原則而為政府提供了一套有效制衡的體制:以三權(quán)分立、聯(lián)邦制為標(biāo)志的雙重分權(quán)的復(fù)合共和政體,迫使政府負(fù)責(zé)。制憲者甚至“偏執(zhí)地”認(rèn)為,憲法只需要對(duì)政府權(quán)力進(jìn)行規(guī)定,而不需要多涉及人民的權(quán)利。換言之,憲法就應(yīng)該是因應(yīng)政府權(quán)力而存在的。對(duì)于一個(gè)有限權(quán)力的政府而言,憲法根本沒(méi)有必要再專門(mén)規(guī)定人民的權(quán)利。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反對(duì)批準(zhǔn)新憲法的一個(gè)意見(jiàn)——憲法草案內(nèi)容未列入人權(quán)法案,聯(lián)邦黨人進(jìn)行了這樣的回應(yīng):“人權(quán)法案,從目前爭(zhēng)論的意義與范圍而論,列入擬議中的憲法,不僅無(wú)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人權(quán)法案條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與政府的權(quán)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將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權(quán)力的借口。既然此事政府無(wú)權(quán)處理,則何必宣布不得如此處理?例如,既然并未授權(quán)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則何必聲明不得限制之?筆者并非謂這類(lèi)規(guī)定將形成處理權(quán)的授予;但它將為擅權(quán)提供爭(zhēng)奪此項(xiàng)權(quán)利的借口則甚為明顯。”[5]〔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0年版,第427-429頁(yè)。簡(jiǎn)言之,在他們看來(lái),政府的行為必須有憲法的根據(jù),把政府的權(quán)力控制在確定的范圍之內(nèi),即在實(shí)際上劃出了政府行為的邊界,也就確立了人民的權(quán)利:政府能做的就是權(quán)力所允許的,此外,政府不能做、無(wú)權(quán)做,政府不能做的即是人民能做的、有權(quán)做的。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解,聯(lián)邦黨人認(rèn)為:“實(shí)際上憲法本身在一切合理的意義上以及一切實(shí)際的目的上,即為一種人權(quán)法案。”[1]〔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0年版,第430頁(yè)。盡管在以后的多次修憲中,憲法不同程度地加上了權(quán)利的內(nèi)容,但是,思路是一以貫之的,沒(méi)有改變,出發(fā)點(diǎn)仍然在權(quán)力,在限制權(quán)力,而不是權(quán)利。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憲法修正案對(duì)于權(quán)利的規(guī)定,多半是以“政府不得……”的規(guī)范形式來(lái)“反向”明確。在這個(gè)意義上,所謂自由,不是意識(shí)形態(tài),也不是精美言辭,而是“一國(guó)的人民相對(duì)于政府而享有的權(quán)利”,而在憲政實(shí)踐中,“自由的問(wèn)題就是最優(yōu)政府范圍的問(wèn)題。”[2]〔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實(shí)用主義與民主》,凌斌,李國(guó)慶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頁(yè)。
上述英美憲政代表了憲政的兩種形態(tài),卻反映了同一個(gè)主題:限權(quán)政治。英國(guó)是從限制國(guó)王的權(quán)力開(kāi)始的,美國(guó)則不僅限制聯(lián)邦政府、州政府的權(quán)力,也限制作為不同政府分支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權(quán)力,尤其是立法機(jī)構(gòu)的權(quán)力,這意味著,即使“以人民名義”行使的權(quán)力也在限制的范圍之內(nèi)。由無(wú)限權(quán)力走向有限權(quán)力,是人類(lèi)歷史上政治制度的飛躍。有意思的是,英國(guó)憲政并非發(fā)端于某種先在的價(jià)值或者思想的假定、推演與論證,而是緣自英國(guó)政治實(shí)踐的逐步演進(jìn)、變革與進(jìn)步。在經(jīng)歷了無(wú)數(shù)次的紛爭(zhēng)、動(dòng)蕩之后,英國(guó)人最終選擇了協(xié)商、妥協(xié)、退讓,限權(quán)政治的實(shí)現(xiàn)——以國(guó)王服從于法律為標(biāo)志,結(jié)束了無(wú)序、失衡、血腥的歷史。相對(duì)而言,美國(guó)或許更“理性”些,制憲者不僅反對(duì)王權(quán),而且對(duì)歷史上出現(xiàn)過(guò)的非王權(quán)形式的專權(quán)——雅典城邦的公民大會(huì)——也十分警惕,選擇了兩院制的立法機(jī)構(gòu)模式,宣布了對(duì)任何機(jī)構(gòu)擁有絕對(duì)權(quán)力的否定。這樣的理性與其說(shuō)是憲法設(shè)計(jì)的認(rèn)識(shí)論前提或者說(shuō)是理論認(rèn)知,毋寧是對(duì)既往人類(lèi)政治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的反思、總結(jié)與超越。
四、能夠合作:憲政的展開(kāi)
憲法是合作所達(dá)成的共識(shí),是最低限度或者說(shuō)是最低層面的共識(shí),是避免由于利益、立場(chǎng)等等方面的種種差異而相互傾軋帶來(lái)的動(dòng)蕩。可以說(shuō),以合作作為標(biāo)志性狀態(tài)的憲政是人類(lèi)這個(gè)族類(lèi)找到的解決沖突的有效途徑,合作也在實(shí)際上成為利益沖突社會(huì)中的存在法則。合作的能力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責(zé)任的落實(shí)和秩序的形成。由合作所形成的秩序體現(xiàn)了憲政作為規(guī)則之治的特質(zhì),同時(shí),秩序也是每個(gè)人都信守和履行自己的責(zé)任的結(jié)果。基于對(duì)契約的信守,在憲政的規(guī)則下,每個(gè)人——事實(shí)上可以簡(jiǎn)單地界分為政府和人民明確自己的行為范圍所在,并且各安其分。尊重他人(包括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相互尊重)和服從規(guī)則(首先是憲法)是基本要素。對(duì)于政府而言,知道權(quán)力的底線在哪里,尊重和敬畏規(guī)則,遵循權(quán)力規(guī)則,才能在權(quán)力的行使上有所收斂,才不至于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作為權(quán)力支點(diǎn),才不至于無(wú)法無(wú)天,為所欲為。作為普通的民眾,知道自己是在一個(gè)政治共同體中生活的人,是一個(gè)必須遵循法律的人,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安全和保護(hù)。遵守法律是憲法規(guī)則為普通人事實(shí)上也是所有人設(shè)定的責(zé)任,這意味著所有人都在約束中。沒(méi)有誰(shuí)的利益可以得到?jīng)]有邊界的保護(hù),每個(gè)人都必須對(duì)各自的利益進(jìn)行讓步,自己利益的存在必須以他人利益也存在作為前提,尤其是政府,更是在控制之下,所以,沒(méi)有權(quán)力是可以恣意的,權(quán)利也是如此。這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合作的結(jié)果。
從宏觀上看,所有人都需要以合作態(tài)度、立場(chǎng)去對(duì)待憲法、對(duì)待社會(huì),每個(gè)人都對(duì)國(guó)家的秩序負(fù)有責(zé)任,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與一般人相比,政府應(yīng)該負(fù)有更大的責(zé)任。可以說(shuō),憲法的責(zé)任是需要政府來(lái)落實(shí)的,憲法的責(zé)任也需要政府來(lái)承擔(dān)。換言之,政府應(yīng)該比普通人更應(yīng)該做到守則(守約)。在任何時(shí)候、任何場(chǎng)合,政府都是人民最有說(shuō)服力的教員。事實(shí)上,幾乎所有國(guó)家都把憲法責(zé)任施加給了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在不同的角色活動(dòng)中,讓?xiě)椃ㄔ诓煌瑢哟魏筒煌瑐?cè)面發(fā)揮作用,影響人們的生活。在政府內(nèi)部,相對(duì)于立法與行政權(quán)力分支,司法承擔(dān)的責(zé)任更重。在美國(guó),其他的權(quán)力分支一般是拿憲法的文本說(shuō)事,比如立法和行政,尤其是行政,它幾乎不能夠?qū)椃ǖ奈谋咀魅魏我饬x上的擴(kuò)展性解讀,權(quán)力就是權(quán)力,立法可能好一些,特別是基于憲法第一條的彈性條款,國(guó)會(huì)可以決定在什么時(shí)候制定自己認(rèn)為“必要與合適”的立法。而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職責(zé)顯然不止于此。在具體的憲法案件中,它的解釋?xiě)?yīng)該更加細(xì)致和清晰,而且必須要證明自己判決的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對(duì)憲法作出解釋的進(jìn)一步說(shuō)理和論證,也是引導(dǎo)人們展開(kāi)憲政思考、推進(jìn)司法決定與社會(huì)認(rèn)知良性互動(dòng)的過(guò)程。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過(guò)程并不是一個(gè)尋求絕對(duì)真理或者說(shuō)是作出唯一正確決斷的過(guò)程,毋寧“是要把事辦妥(而不是好)。”[1]〔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實(shí)用主義與民主》,凌斌,李國(guó)慶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波斯納文叢》總譯序”(蘇力),第5頁(yè)。把事辦妥,而不是好,這可以看作是實(shí)用主義法學(xué)的最典型表達(dá),也是憲法合作方式的體現(xiàn)。“妥”與“好”是不同的,后者充滿了價(jià)值判斷,而價(jià)值判斷往往是有差異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每個(gè)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憲法不是去分辨誰(shuí)的看法是正確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而去保護(hù)、去發(fā)揚(yáng)光大,而是忽略這樣的問(wèn)題,或者說(shuō)根本就不去考慮這個(gè)問(wèn)題,而是留待一定的程序性規(guī)則去確定,作為憲法,只是要?jiǎng)?chuàng)造、維持一個(gè)秩序,一個(gè)安全的秩序,這是最基本的,價(jià)值讓人們自己去選擇和判斷。至于“妥”,可以理解為合適的,是在憲法框架下解決爭(zhēng)議和沖突,不是去做“正確的決斷”。這樣的“妥”體現(xiàn)的就是合作的態(tài)度和方式,即在最大程度上維護(hù)憲法規(guī)則,合作正是司法作出判斷的出發(fā)點(diǎn)。這也是為什么有學(xué)者認(rèn)為:“實(shí)現(xiàn)正義,哪怕天塌下來(lái),在波斯納看來(lái),這是一種不負(fù)責(zé)任的司法態(tài)度。”[2]〔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實(shí)用主義與民主》,凌斌,李國(guó)慶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民主與法治的張力(代譯序)”(蘇力),第8頁(yè)。這說(shuō)明,負(fù)責(zé)任的司法應(yīng)該在最大程度上履行合作之責(zé),盡最大可能的合作,維系整個(gè)憲政秩序。
就憲政國(guó)家的歷史而言,不僅僅是憲法規(guī)則本身的形成要在合作的方式下進(jìn)行,比如美國(guó)聯(lián)邦憲法就是如此,而且,憲法規(guī)則的發(fā)展也需要合作。作為書(shū)面文件的憲法,面臨著文本固定規(guī)則與社會(huì)發(fā)展變遷之間的內(nèi)在緊張關(guān)系,由于人類(lèi)智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的局限性,大家都不是神,制憲者也無(wú)力預(yù)計(jì)未來(lái)。但是,作為憲政方式的合作(合意)卻是不變的,而且,只要固守這樣的方式,文本與社會(huì)之間的張力就可以獲得有效的化解。在一個(gè)多元社會(huì)中,在最低限度上的共識(shí)的形成只能是基于合作的出發(fā)點(diǎn)。憲法正是這樣的底線,只不過(guò)憲法僅僅提供了一個(gè)基本的合作框架,初步確立了一種合作模式。政府機(jī)構(gòu)特別是法官還需要發(fā)展這樣的憲法秩序,在面對(duì)新的問(wèn)題的時(shí)候,以憲法來(lái)確定。事實(shí)上,基于憲法規(guī)則的合作也是美國(guó)憲法司法實(shí)踐中法官們作出決定的出發(fā)點(diǎn)。特別是面對(duì)新的問(wèn)題尤其是憲法規(guī)則面臨挑戰(zhàn)的情形下,司法的決定更是如此。根據(jù)學(xué)者的研究,在經(jīng)典的第一修正案領(lǐng)域,很難說(shuō)存在著什么普遍的“言論自由原則”,換言之,探求表達(dá)自由的基本原理是徒勞的,因?yàn)閷?duì)于言論的保護(hù)程度取決于法院將其歸入的社會(huì)領(lǐng)域(即共同體、管理、民主)的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法院需要確定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界限。正是通過(guò)確定不同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界限,言論被辨識(shí)[3]參見(jiàn)〔美〕羅伯特·C·波斯特:《憲法的領(lǐng)域:民主、共同體與管理》,畢洪海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頁(yè)。。而通過(guò)在具體案件中將第一修正案運(yùn)用于不同社會(huì)領(lǐng)域,法院不斷地重新解釋第一修正案,從而賦予這一條款應(yīng)對(duì)言論世界的各種層出不窮的問(wèn)題的功能,也是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憲法調(diào)整(也是調(diào)和)既存在矛盾甚至沖突但又相互依賴的社會(huì)秩序形式的工具價(jià)值得以顯現(xiàn),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法官將憲法的“兼容性”的合作特質(zhì)落實(shí)在了司法實(shí)踐中。有學(xué)者認(rèn)為,憲法的意義幾乎會(huì)在每一代被重新確立,憲法的代際變遷是憲法生活的一個(gè)客觀事實(shí)[1]See Cass R.Sunstein,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Why the Founding Document Doesn't Mean What It Meant Befo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210,preface p.ix.。不同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duì)于憲法解釋的不同立場(chǎng),恰恰表明了自由派與保守派路徑選擇的不同,也正因?yàn)檫@樣的不同,才可能在爭(zhēng)論與平衡中,尋求重新確立憲法的意義,解決新的社會(huì)難題。這也是合作的體現(xiàn)。在這個(gè)意義上,與其說(shuō)憲法規(guī)則是底線,不如說(shuō)合作是底線,或者說(shuō),在所有憲法規(guī)則中,合作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規(guī)則。
五、結(jié)語(yǔ)
作為制度,憲政從一開(kāi)始就不是理論的演繹,而是實(shí)踐的展開(kāi)。作為手段,它是實(shí)驗(yàn)、試驗(yàn)甚至是不斷“試錯(cuò)”的產(chǎn)物,而非理性思維的寵兒。歷史的事實(shí)是,憲政最初發(fā)生在以實(shí)踐哲學(xué)見(jiàn)長(zhǎng)的英國(guó)而非以理性思辯見(jiàn)長(zhǎng)的歐洲大陸,說(shuō)到底,憲政就是一種經(jīng)驗(yàn)。正如戴雪所指出的那樣,英國(guó)憲政的生成“并不是根據(jù)抽象理論而得到的結(jié)果,這種結(jié)果實(shí)產(chǎn)生于英吉利人們所有一種政治天性。”[2]〔英〕戴雪:《英憲精義》,雷賓南譯,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頁(yè)。照筆者的理解,這樣的天性無(wú)疑是一種“最善于調(diào)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jīng)驗(yàn),就是合作,也就是伯克所總結(jié)的構(gòu)成英國(guó)政治理想和倫理價(jià)值層面上的“普遍合意”。這提示我們,對(duì)于一種制度來(lái)說(shuō),理性、假定、理念是重要的,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唯一重要的,也未必是“牢靠的”,關(guān)鍵在于實(shí)踐。不僅如此,一國(guó)憲政的實(shí)現(xiàn)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便是在所謂“原發(fā)性的”憲政國(guó)家也不例外。英國(guó)憲政幾百年來(lái)的演進(jìn)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憲政需要在實(shí)踐中進(jìn)步,所以也是一個(gè)過(guò)程。另外,人們選擇憲政,并非因?yàn)槠溥壿嫛白郧ⅰ保且驗(yàn)樗怯杏玫模Y(jié)束了人類(lèi)社會(huì)千百年來(lái)?yè)u擺于暴政和無(wú)政府狀態(tài)兩個(gè)極端之間的歷史,為人的安全提供了最為確實(shí)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對(duì)于憲政的有用性認(rèn)識(shí),早在一個(gè)世紀(jì)前的中國(guó)就存在。清末變法立憲過(guò)程中,贊同與反對(duì)之聲并存,但兩種主張的共同點(diǎn)在于:都是從工具理性上考慮的,與所謂的“價(jià)值選擇”或“意識(shí)形態(tài)”并無(wú)多少關(guān)聯(lián)。比如,贊同者認(rèn)為,僅就治理國(guó)家的人的數(shù)量而言,憲政就優(yōu)于專制。“臣竊聞東西各國(guó)之強(qiáng),皆以立憲法開(kāi)國(guó)會(huì)之故,國(guó)會(huì)者,君與國(guó)民共議一國(guó)之政法也。……故人君與千百萬(wàn)之國(guó)民,合為一體,國(guó)安得不強(qiáng)?吾國(guó)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shù)人共治其國(guó),國(guó)安得不弱?蓋千百萬(wàn)之人,勝于數(shù)人者,自然之?dāng)?shù)矣。”[3]康有為:《請(qǐng)定立憲開(kāi)國(guó)折》,載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guó)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yè)。在憲政的控制規(guī)則和功能方面,贊同者認(rèn)為,其實(shí)傳統(tǒng)的皇權(quán)也是有限制的,但并不明確,現(xiàn)在的立憲不過(guò)是以憲法的書(shū)面形式即規(guī)則化的形式將這樣的控制確定下來(lái)而已[4]參見(jiàn)梁?jiǎn)⒊骸读椃ㄗh》,載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guó)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yè)。。反對(duì)者認(rèn)為,立憲這個(gè)藥方只適合處理西方之疾,不能祛除中國(guó)之病,我們不應(yīng)該病急亂投醫(yī)[5]參見(jiàn)《御史劉汝驥奏請(qǐng)張君權(quán)折》,載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guó)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頁(yè),第78頁(yè)。。更有反對(duì)者認(rèn)為,“君子而充議員,黨孤力怯,將屏息不敢出聲。小人而充議員,上藉抵抗官長(zhǎng)之力,即下可魚(yú)肉鄉(xiāng)愚。”[6]參見(jiàn)《御史劉汝驥奏請(qǐng)張君權(quán)折》,載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guó)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頁(yè),第78頁(yè)。關(guān)于選擇憲政的理由,梁?jiǎn)⒊恼J(rèn)識(shí)是頗為深刻的,他將憲政與專制相比較,認(rèn)為“專制政體者,實(shí)數(shù)千年來(lái)破家亡國(guó)之總根源也。”[7]梁?jiǎn)⒊骸讹嫳液霞罚段募拧罚?0頁(yè)。轉(zhuǎn)引自張晉藩:《中國(guó)憲法史》,〔長(zhǎng)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yè)。要擺脫中國(guó)千年來(lái)周而復(fù)始的專制王朝更迭的命運(yùn),就必須選擇憲政。在這里,憲政的好處是顯而易見(jiàn)的,因而選擇憲政是一種需要。
由此可見(jiàn),相較于前人的“求實(shí)”,今天的我們似乎過(guò)多地糾纏于“求是”。當(dāng)代學(xué)者多將清末立憲的失敗原因之一歸結(jié)于那個(gè)時(shí)代的學(xué)人和制憲者采用“憲政-富強(qiáng)”思維的工具性價(jià)值,而不是采用憲政本來(lái)的價(jià)值理性[1]參見(jiàn)張晉藩:《中國(guó)憲法史》,〔長(zhǎng)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緒論,第11頁(yè)。。曾有學(xué)者指出,“西方人追求的是憲政自身的價(jià)值,而在中國(guó),憲政則變成了人們?cè)谧非髧?guó)家富強(qiáng)時(shí)的一個(gè)工具。這種語(yǔ)境的置換消解了憲政本身的價(jià)值。”[2]王人博:《憲政的中國(guó)語(yǔ)境》,〔北京〕《法學(xué)研究》2001年第2期。這一見(jiàn)解的合理性和深刻性是顯著的,但不可忽視的問(wèn)題是:對(duì)于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guó)家來(lái)說(shuō),基于“挑戰(zhàn)-回應(yīng)”模式的路徑依賴,工具理性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很少是因?yàn)閼椪氨旧砗谩辈乓浦驳模喟胧且驗(yàn)閼椪昂苡杏谩辈沤邮埽@幾乎是所有所謂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guó)家對(duì)于外來(lái)制度的認(rèn)知和接納方式,中國(guó)也不可能例外。
另外,我們對(duì)于憲政的價(jià)值分析和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人所追求的憲政價(jià)值本身?自由、民主、平等,這些由學(xué)者總結(jié)出來(lái)的價(jià)值,可能都不是憲政發(fā)生的理由,而是憲政運(yùn)作的結(jié)果,如果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憲政發(fā)生的價(jià)值的,那可能就是和平或者說(shuō)是安全[3]比如,美國(guó)立憲的最突出目標(biāo)就是克服邦聯(lián)的松散無(wú)力狀態(tài),建立強(qiáng)大的聯(lián)邦政治形式;在英國(guó),自1215年《大憲章》始,幾百年來(lái)一系列憲法性法律文件(舊譯“文書(shū)”)的出臺(tái),“無(wú)一道文書(shū)不是專為應(yīng)付當(dāng)時(shí)所有急需而設(shè)立。”(參見(jiàn)〔英〕戴雪:《英憲精義》,雷賓南譯,〔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譯者導(dǎo)言,第4頁(yè)。)可能比較例外的是法國(guó),大革命之后的《人權(quán)宣言》把自由、平等寫(xiě)在了紙上,結(jié)果是在此后的近兩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里,法國(guó)人既沒(méi)有得到自由,也沒(méi)有得到平等。。至于其他,或許只是“副產(chǎn)品”。當(dāng)然,只求“實(shí)用”或許會(huì)有失偏頗,落入“結(jié)果論”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是非”的判斷并不是僅僅依靠所謂的推理和演繹就能夠成立的,也是需要“實(shí)用”來(lái)檢驗(yàn)的,就像“實(shí)踐是檢驗(yàn)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憲政是被人類(lèi)社會(huì)幾百年來(lái)反復(fù)實(shí)踐所證明的“有用”的東西,我們沒(méi)有拒絕的理由。事實(shí)上,如果我們更進(jìn)一步地思考,就不難發(fā)現(xiàn),被我們認(rèn)為是某種“價(jià)值”、“意識(shí)形態(tài)”的理論,在其根本意義上,不過(guò)是對(duì)實(shí)踐的描述或者提煉。比如“自由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憲政”,不過(guò)是對(duì)于憲政實(shí)踐的理論解說(shuō),換言之,是憲政實(shí)踐在前,憲政理論在后。英國(guó)實(shí)踐為自由主義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來(lái)源和養(yǎng)料,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可以認(rèn)為,自由主義到憲政、憲政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實(shí)踐的因果而非邏輯的因果。
“任何具體制度的本身都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合法性,都必須服務(wù)人類(lèi)的、特別是當(dāng)代人的需要,這才是任何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根據(jù)。它反對(duì)用一種自我中心的、上帝式的、歷史在我這里或在我們這一代終結(jié)的眼光來(lái)考察和評(píng)價(jià)任何制度。”[4]蘇力:《語(yǔ)境論——一種法律制度研究的進(jìn)路和方法》,〔北京〕《中外法學(xué)》2000年第1期。我們不需要為憲政附加太多不必要的色彩,也不需要將憲政看作包治百病的“普世良方”,說(shuō)到底,憲政不過(guò)是迄今為止人類(lèi)找到的一種合理和有效的管理制度,這也是我們關(guān)注這個(gè)制度的理由。
〔責(zé)任編輯:錢(qián)繼秋〕
The Politics of Corporation:a Physical Study of Constitutionalism
Zhao Juan
Constitutionalis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olitics of corpor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physics. The wishes,rules and abilities of corporation accomplished constitutionalism as a political formation in human society.We chose constitutionalism,because it is a useful tool of maintaining living safety and an effective wa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which is hitherto a human find,not because of its final correct value.
constitutionalism;corporation;constitution;politics;practice
趙娟,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 210008
本文系南京大學(xué)985三期項(xiàng)目資助,特此致謝。
- 江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江蘇農(nóng)村工業(yè)化中環(huán)境污染的規(guī)模效應(yīng)、污染排放強(qiáng)度效應(yīng)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效應(yīng)研究
- 商業(yè)的目的和更大的善:私人財(cái)富和公共財(cái)富的結(jié)合
- 試論劉師培家學(xué)傳統(tǒng)與揚(yáng)州學(xué)派的關(guān)系
——由《江南鄉(xiāng)試墨卷》說(shuō)起 - 從“以身發(fā)財(cái)”到“以財(cái)發(fā)身”
——張謇創(chuàng)業(yè)的人力資本與社會(huì)效應(yīng) - 元治理視域下政府治道邏輯與治理能力提升
- 全息:傳統(tǒng)糾紛解決機(jī)制的現(xiàn)代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