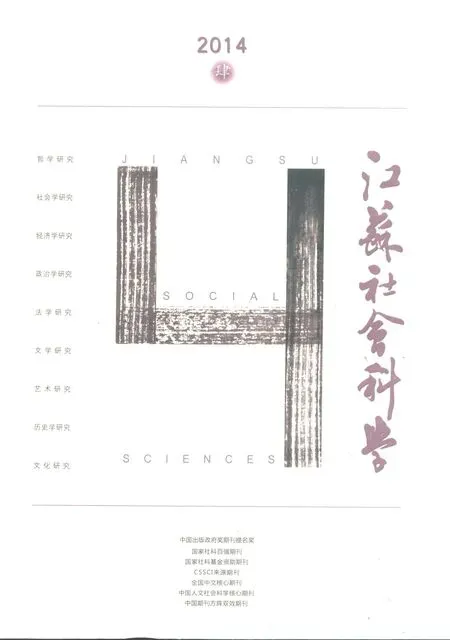論193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
張立群
論193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
張立群
“國家主題”主要涉及文學主題、題材、意象等多方面內容,并可以以類型化、個性化、動態的視野把握文學與歷史、文化、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從文學史的角度上說,193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由于特定時代而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在充分聯系時代語境的前提下,本文從“捉住現實”的立場及其主題呈現、“為祖國而歌”的集中表達、“主題”的制約與形式的“選擇”、“土地”等意象的意圖外化、寫作的轉向與心靈的真實五個主要方面研討“國家主題”在這一時期新詩中的表現及內涵,努力在重繪1930年代新詩圖譜的過程中,為中國新詩的國家主題研究提供參考個案。
1930年代 新詩 國家主題
歷史地看,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經歷草創期的實踐,已積累了大量的藝術經驗并呈現出深入發展的趨勢,而在另一方面,30年代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又使新詩必須做出回應。30年代新詩的發展態勢使其和“國家主題”具有某種天然的聯系。得益于主題學研究的啟示,“國家主題”主要是研究“國家”這一“主題”“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處理,據以了解時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圖’(intention)”[1]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年版,第26頁。。具體至創作層面,“國家主題”不但包括與“國家”相關的題材、主題(此時主題的含義指單個作品)、母題、意象、情節、人物等,還包括與此相關的隱喻、象征以及理想、價值及其相互關系。國家主題的提出,可以以動態的視野重繪30年代新詩的圖譜,而此時的30年代與現代文學史意義上的第二個十年(1927至1937年)并不一致,又為其獲得了新的闡釋空間。
一、“捉住現實”的立場及其主題呈現
無論“1930年代”的定位會最終為我們呈現怎樣的研究視野,順應20年代革命文學的發展,立足社會現實、捍衛革命文藝正確的發展方向,都是從歷史演進角度談及30年代詩歌國家主題首要面對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3批面上資助課題“現代新詩的國家主題研究”(編號2013M530328)的階段成果。
的問題。這一問題結合具體的詩歌實踐,可以通過“左聯”時期的詩歌活動加以證明。1930 年3 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標志著左翼文藝運動成為有組織的革命活動,以“左聯”詩歌為代表的“捉住現實”的實踐活動也隨即開展起來。
從《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及其理論綱領》中的“詩人如果是預言者,藝術家如果是人類的導師,他們不能不站在歷史的前線,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清除愚昧頑固的保守勢力,負起解放斗爭的使命”[1]《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及其理論綱領》,見《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不難看出,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左聯”對包括詩人在內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提出了要求。歷史地看,“左聯”雖成立于1930年,但作為前期籌備工作卻從1929年10月就開始了;而就國內形勢來看,“左聯”的“大事記”可以上溯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其后涉及文藝界的又有1928年后期創造社成員在《文化批判》(1928年1月上海創刊)上旗幟鮮明地提出建設“革命文學”的主張,進而展開了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茅盾等關于“革命文學”的論戰等等[2]關于“左聯”成立的經過及“大事記”,本文主要參考了夏衍的《“左聯”成立前后》,陽翰笙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經過》等文章,以及由張大明、王保生整理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大事記》,均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這一時期詩歌與國家主題相關的可以舉蔣光慈寫于東京的《我應當歸去》[3]蔣光慈:《我應當歸去》,發表于1929年12月15日《新流月報》第4期。,殷夫的《我們的詩》(包括《前燈》、《Romantic的時代》、《Pionier》、《靜默的煙囪》、《該死的死去吧!》、《議決》6首)、《詩三首》(包括《我們》、《時代的代謝》、《May Day的柏林》)、《血字》(外六首)(包括《血字》、《意識的旋律》、《一個紅的笑》、《上海禮贊》、《春天的街頭》、《別了,哥哥》、《都市的黃昏》),以及寫于1930年的《前進吧,中國!》、《五一歌》、《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4]殷夫的詩,具體出處如下:《我們的詩》6首,發表于1930年1月10日《拓荒者》1期(即《新流月報》第五期);《詩三首》,發表于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第2期;《血字》(外六首),發表于1930年5月《拓荒者》第4、5期合刊;《前進吧,中國!》寫于1930年1月19日,《五一歌》寫于1930年4月25日,《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表明時間為1930年五卅紀念,后收入《殷夫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4-70頁。等。在這些詩作中,詩人的愛國意識、理想意識以及具體寫作過程中“我們”人稱的使用等特點,不但生動地呈現了作者的革命者身份,而且還呈現了他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定立場和斗爭精神。
“左聯”的成立,使革命詩歌有了更為明確的發展方向。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而當時盤踞于詩壇的新月派、現代派被“左聯”的詩人認為是“逃避現實,粉飾現實,甚至是歪曲現實的”[5]任鈞:《關于中國詩歌會》,王訓昭選編《一代詩風——中國詩歌會作品及評論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頁。,因此,如何繼承五四以來新詩的革命傳統,更好地配合反帝、抗日、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就成為了一項迫切的任務。1932年9月,經“左聯”詩人任鈞(筆名盧森堡)倡議,左聯批準,由任鈞、穆木天、蒲風、楊騷等為發起人,在上海召開“中國詩歌會”成立大會,這樣,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個有組織、有綱領的革命詩歌團體就誕生了[6]關于“中國詩歌會”誕生的背景及經過,本文主要參考了王訓昭選編《一代詩風——中國詩歌會作品及評論選》的“前言”和任鈞的《關于中國詩歌會》、柳倩的《左聯與中國詩歌會》、任鈞的《略談一個詩歌流派——中國詩歌會》等。。
中國詩歌會在其成立階段,便確立了“以推進新詩歌運動,致力中國民族解放”和“介紹和努力于詩歌的大眾化”[7]王訓昭選編:《一代詩風——中國詩歌會作品及評論選》“前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的宗旨和任務。1933年2月,中國詩歌會創辦了其機關刊物《新詩歌》旬刊。在第一期《發刊詩》(后收入詩集《流亡者之歌》,名為《我們要唱新的詩歌》)中,穆木天寫道——
我們要唱新的詩歌,
歌頌這新的世紀。
朋友們!偉大的新世紀,
現在已經開始。
我們不憑吊歷史的殘骸,
因為那已成為過去。我們要捉住現實,
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
壓迫,剝削,帝國主義的屠殺,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眾的高漲的情緒,
我們要歌唱這種矛盾和他的意義,
從這種矛盾中去創造偉大的世紀。
“捉住現實”、“歌唱新世紀的意識”闡明了中國詩歌會同仁在創作上的基本主張。這種在具體創作過程中關注現實社會,反抗壓迫、剝削,反帝抗日的主張,就歷史而言,是繼承和發揚了“五四”以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革命傳統;而從“主題”的角度上看,由“捉住現實”具體至國家題材、意象的書寫,則充分反映了30年代的時代特點和詩人的創作意圖。
結合穆木天、蒲風、任鈞等人這一時期的創作,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詩歌會時代詩歌的“國家主題”:第一,是緊密關注時代社會現實。以蒲風的《一九三二年交響曲》為例,該詩結合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的“一·二八事變”,直接觸及社會大事,聯系世界形勢,揭示國民政府消極抵抗、內部相互傾軋等,構成了這一類詩作的共同特點。嚴峻的社會現實造成了流亡者的悲歌,同時也造就了直面時代的“主旋”。從穆木天寫于30年代前期、中期的《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別鄉曲》(一)、《別鄉曲》(二)和《我們的詩》、《歌唱呀,我們那里有血淋淋的現實!》等作品中,人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位東北詩人在故土被日寇侵占、不得不告別故土的心路歷程。這種充分體現由社會、時代影響而形成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創作,在當時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第二,是民族危亡時期的“怒吼”與抗爭之歌。在任鈞的《中國喲,你還不怒吼嗎?》、《據說這兒還是中國的領土》、《祖國,我要永遠為你歌唱!》,蒲風的《中國,我要做個炮手喲》,馬畡夫的《祖國》等直接以“中國”、“祖國”為題的作品中,其題目本身就表達了詩人的意圖:作為民族危亡時期的“聲音”,“中國喲,你還不怒吼嗎?”“祖國,我要永遠為你歌唱!”“中國,我要做個炮手喲”直抒胸臆,既唱出了“全國民眾的覺醒”,又唱出了“抗敵怒潮的高漲”;而在將“堅強的意志做鋼骨,/憤怒當做大石,/團結當做最好的粘土,/借失地的悲哀當做炮基”之后,“等候著一聲信號的轟響,/怒吼吧,中國!/我要做個炮手喲!”更是喊出了抗爭之歌。第三,革命年代中國農村動亂現實的書寫。蒲風的長詩《六月流火》、王亞平的《十二月的風》、田間的《中國,農村的故事》、楊騷的《鄉曲》等,揭示了革命年代中國農村的現實。其中,既有封建地主殘酷剝削下,農村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又有國民黨反動派對外不抵抗、對內加緊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強迫農民割禾、挖墳、修公路,進而激起農民抗爭的情景。這種“捉住現實”重大題材的書寫,充分反映了30年代中國農村真實的生活場景,具有波瀾壯闊的氣魄和史詩的格調。總之,中國詩歌會諸詩人的詩歌創作,以現實的筆法,直涉當時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以實際創作和親身經歷自覺地為民族救亡運動和階級斗爭服務,集中呈現了“左聯”時代詩歌的國家主題,并在相當程度上和30年代社會形勢產生契合。
二、“為祖國而歌”的集中表達
為了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建立文藝界更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于1936年初自行解散。“左聯”的結束,就歷史進程來看,新詩已逐步進入到“抗戰詩歌”階段,這一階段“國家主題”的主要特點即為“為祖國而歌”的集中表達。“為祖國而歌”是胡風在4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本詩集的名字,曾作為“七月詩叢”之一種,主要收錄了詩人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創作的詩五首,其創作時間皆為1937年,系“最早的抗戰頌歌之一”[1]關于胡風的《為祖國而歌》,本文主要參考了牛漢、綠原編《胡風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胡風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詩五首依次為《為祖國而歌》、《血誓》、《給怯懦者們》、《同志》、《敬禮》。“最早的抗戰頌歌之一”的提法,可參見《胡風詩全編》52頁。。在同題詩《為祖國而歌》中,詩人寫道——
在黑暗里在重壓下在侮辱中
苦痛著呻吟著掙扎著
是我的祖國
是我的受難的祖國!
……
在敵人的鐵蹄所到的一切地方,
迎著槍聲炮聲炸彈的呼嘯聲——
祖國呵
為了你
為了你的勇敢的兒女們
為了明天
我要盡情地歌唱:
用我的感激
我的悲憤
我的熱淚
我的也許迸濺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正如詩人在詩集“題記”中說的:“戰爭一爆發,我就被卷進了一種非常激動的情緒里面。在血火的大潮中間,祖國兒女們底悲壯的行為,使我流感激的淚水,但也是祖國兒女們底卑污的行為,使我流悲憤的淚水。于是,我底喑啞了多年的咽喉突然地叫了出來。”[2]胡風:《為祖國而歌》“題記”,最初發表于1940年5月《七月》5集3期,后收入詩集《為祖國而歌》。《為祖國而歌》既寫“受難的祖國”,又寫“我要盡情地歌唱”;與一般的使用第一人稱、抒發自我情感之作不同的是,它是通過自我的感知與發自內心的歌唱,和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等公共主題建立了緊密的有機聯系,進而在聯系的過程中實現了一種從個體到群體的話語講述方式;其感情真摯而深沉,唱出了抗日戰爭爆發后眾多中國詩人的心聲。至1942年,青年詩人陳輝再次以“為祖國而歌”為題,抒發對祖國的愛與頌歌,這不能不說明“祖國”特別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祖國”形象所能激發的詩情,和“為祖國而歌”可以承載的復雜的詩人心態。顯然,在國家、民族處于生死存亡之際,“國家”這個具有多重含義的詞更容易成為詩人從多個角度加以書寫的重大主題。“她”自發而真實,鮮明而集中,并在不斷歌詠中成為“想象的共同體”[3]“想象的共同體”,可參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安德森認為:“民族被想象為一個共同體,因為盡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系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愿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這種說法顯然也適合于本文抗戰詩歌的國家主題,見該書第7頁。。
應當說,抗戰爆發后直接書寫“國家主題”的詩歌是舉不勝舉的。而且,在具體書寫的過程中比“左聯”時代的“國家主題”更加突出、明確。從“左聯詩歌”到“抗戰詩歌”,“國家主題”的變化表明其書寫既有業已本質化、歷史化的內容,又有隨時代變化而凸顯的特質。具體比較而言,30年代“抗戰詩歌”在“國家主題”層面上有兩個突出的表現:其一,是“國防”與救亡。郭沫若的《詩歌國防》、《們》,穆木天的《全民族總動員》,柳倩的《救亡歌》,任鈞的《中國已經開始怒吼了》等,都在總體上表達了這一主題。其二,是抗戰的戰歌與頌歌。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的喜炮》、《抗戰頌》、《戰聲》、《血肉的長城》,穆木天的《全民族的生命展開了——黃浦江空軍抗戰禮贊》、《東方的壁壘》、《民族敘事詩時代》,艾青的《我們要戰爭——直到我們自由了》、《這是我們的——給空軍戰士》,田間的《進行曲——我們行軍生活素描》,胡風的《血誓——獻給祖國的年青歌手們》,楊騷的《莫說筆桿不如槍桿》以及大量刊載于《抗戰》(一度更名為《抵抗》)、《抗戰文藝》、《光明》、《七月》、《文藝戰線》等雜志上的詩,均凸顯了上述主題內容。
按照穆木天在《詩歌創作上的題材與主題的問題》中的說法,“一個真實的詩歌工作者,要作他的時代的喇叭手,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他要把他的時代的聲音,反應出來。他要作他的時代的代言人。他要把他的時代的感情集中在他的身上,以一種極緊縮的形相,把他的時代的感情,反映出來。他要用時代的典型的形相反映出來時代的典型的感情。這樣,在我們抗戰建國的民族革命斗爭中間,一個真實的詩歌工作者,就是,必須用他的詩歌,歌唱出我們的時代的抗戰建國的要求,以之,在政治上,和在藝術上,完成了他的民族革命的任務。”[1]穆木天:《詩歌創作上的題材與主題的問題》,《怎樣學習詩歌·六》,生活書店1938年版,第121頁。抗戰爆發之后,詩人自發的關注社會、書寫“國家”,做“時代的代言人”:“我們應是全民族的回聲,/洪亮的歌聲要震動禹域,/全民族的危亡的形象,/要——在我們心中喚起”(《我們的詩》);“民族的戰斗的行動,/是一部偉大的詩篇,/我們是要作一個/真實的詩歌記錄者!”(《我們要作真實的詩歌記錄者》)穆木天寫于這階段的兩首詩,十分典型地呈現了抗戰時期詩人持有的主客觀認識。“抗戰”特定的歷史背景對詩人、詩歌寫作本身都提出相應的要求,它使那些關注現實的詩人介入到更為廣闊的社會洪流之中,進而使國家、民族的主題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與集中。當然,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如何在關注國家命運和書寫內心真實的同時,使詩歌以藝術的方式表現國家的主題。事實上,在寫于這一時期的孫毓棠的《談抗戰詩》、戴望舒的《談國防詩歌》、胡風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等文章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詩歌在急劇適應時代過程中呈現的“思路不習慣、表現的技術不習慣”[2]孫毓棠:《談抗戰詩》,《大公報·文藝副刊》1936年6月14、15日。和出于文學是“工具”、“宣傳”的“功利主義之目的”而造成的“淺薄而庸俗”[3]戴望舒:《談國防詩歌》,《新中華》1937年4月10日第5卷第7期。后收于《戴望舒全集》,名為《關于國防詩歌》,〔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7頁。的現象,“公式化是作家廉價地發泄感情或傳達政治任務的結果,這個新文藝運動里面的根深蒂固的障礙,戰爭以來,由于政治任務的過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過于興奮,不但延續,而且更加滋長了。”[4]胡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對于文藝發展動態的一個考察提綱》,1939年7月《七月》4集1期。而在穆木天的《關于抗戰詩歌運動——對于抗戰詩歌否定論者的常識的解答》、任鈞的《談戴望舒的〈談國防詩歌〉》以及艾青的《詩與時代》、《詩與宣傳》等文章中,人們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針對上述孫毓棠、戴望舒文章的回應,還可以看到當時詩人對于“詩與時代”、“詩與宣傳”等現實命題的認識。這樣,在強調創作真實性、戰斗性,情緒慷慨激昂的同時,如何處理具體詩歌寫作過程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類型化、模式化的傾向以及有效地認識“藝術工具論”,便成為30年代抗戰詩歌發展中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這個留給40年代新詩的問題不僅涉及新詩的內容與形式,而且,也涉及新詩主題與藝術之間的辯證關系。
三、“主題”的制約與形式的“選擇”
談及“左聯詩歌”、“抗戰詩歌”的主題呈現及其特點,很容易聯系到30年代新詩的形式問題。盡管,從主題學的角度來看,形式并不是其主要的研究對象,但由于受到特定的“主題”的制約,形式的“選擇”則顯然成為“據以了解時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圖’”的一個重要方面。
為了能夠更為清晰地闡述30年代新詩的形式“選擇”,筆者選擇從“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這一延續自“革命文學”的論爭并貫穿30年代文學史的話題入手。“左聯”成立前后,為了在文學實踐中貫徹創作與民眾結合的問題,曾集中討論過大眾化的形式問題。這場大討論在1930年進行了第一次,在1931年冬至1932年進行了第二次,后在1934年進行了第三次。其中,1930年由《大眾文藝》推出的“新興文學專號”[1]《大眾文藝》,1928年9月20日創刊,郁達夫等為主編,上海現代書局發行,后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之一,至1930年5月出版最后一期,共計十一冊十二期。其第二卷第三期、第四期曾推出“新興文學專號”上下兩冊,具體出版時間為1930年3月1日、1930年5月1日。其中,上冊共收入“文藝大眾化的諸問題”討論文章七篇,座談會紀要一篇;下冊有“我希望于大眾文藝的”26位作家、理論家的筆談以及批評文章、第二次座談會紀要各一篇。曾十分集中地討論了“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并對此進行了有效的推動。“文藝大眾化”問題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受到了更為廣泛的重視,“左聯”執委會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關于“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等文件中都強調了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性。“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反映在當時的詩歌戰線上即為“詩歌大眾化”的理論探討和藝術實踐[2]具體可參見蒲風的《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1934)、王亞平的《新詩歌的內容與形式》(1934)、任鈞的《關于中國詩歌會》(1946)、柳倩的《左聯與中國詩歌會》(1979)等文章,后均收于王訓昭選編:《一代詩風——中國詩歌會作品及評論選》。。從《新詩歌》旬刊《發刊詩》中的“我們要用俗言俚語,/把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人們可以看到,中國詩歌會諸詩人適應形勢“用俗言俚語”、民謠、小調、鼓詞、兒歌等,使詩歌成為“大眾歌調”的形式追求。而在《關于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中,人們更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詩歌會同人關于“中國新詩歌的時代任務”、“新詩歌的題材(內容)”和“新詩歌采用什么樣形式去表現”等的意見、看法:
中國新詩歌的時代任務是應該:站在被壓迫的立場,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不合理的壓迫,同時引導大眾以正確的出路;
明白了新詩歌的時代任務,我們才能講到“怎樣寫作新詩歌”的問題。新詩歌的題材(內容)是什么?在這里,為著新詩歌是負有偉大的時代任務,我們必須理解新詩歌的內容,最少應該包含的三種要件:(一)理解現制度下各階級的人生,著重大眾生活的描寫;(二)有刺激性的,能夠推動大眾的;(三)有積極性的,表現斗爭或組織群眾的。
……
新詩歌采用什么形式去表現呢?關于新詩歌的形式,我們有如下的意見:(一)創造新格式——有什么就寫什么,要怎么寫就怎么寫,卻不要忘記應以能夠適當地表現內容為主。要應用各種形式,要創造新形式。但要緊的是要使人聽得懂,最好能夠歌唱。(二)采用大眾化的形式——事實上舊形式的詩歌在支配著大眾,為著教養、訓導大眾,我們有利用時調歌曲的必要,只要大眾熟悉的調子,就可以利用當作我們的暫時的形式。所以,不妨是:“泗洲調”、“五更嘆”、“孟姜女尋夫”……(三)采用歌謠的形式——歌謠在大眾方面的勢力,和時調歌曲一樣厲害,所以我們也可以采用這些形式。(四)要創造新的形式,如大眾合唱詩等。[3]同人等:《關于寫作新詩歌的一點意見》,《新詩歌》旬刊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11日。后收于王訓昭選編:《一代詩風——中國詩歌會作品及評論選》。
在上述的闡述中,中國新詩歌的時代任務、題材和形式以有機、辯證的方式得到了統一。而在此過程中,“詩歌大眾化”不僅是“達到革命大眾詩歌的橋梁”[4]穆木天:《關于詩歌大眾化》,《戰歌》1卷6期,1939年。后收于《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而且,還是一種“政治的革命的手段”,一種“文藝的革命的手段”[5]穆木天:《文藝大眾化與通俗文藝》,《文藝陣地》第2卷第8期,1939年2月1日。,它要在啟蒙、引導、教育、團結大眾的過程中,改變其心理意識,徹底地完成其心理革命,進而實現詩歌的國家主題書寫和政治文化功能。
詩人林木瓜的《新蓮花》采用了俗曲“蓮花落”調,書寫國難背景下中國農村的貧富階級對立;“流”(指詩人葉流)的《國難五更調》采用了舊俗曲中的“五更嘆”調,從一更唱到五更天明的形式,擯棄了其原有的悲憫的基調,注入抗日救亡的新主題;《新編十二個月花名》、《新十嘆》采用民歌調,或通過“報花名”寫國家時事、呼吁人民上戰場,或通過“十嘆調”寫正泰橡膠廠慘案,“奉告同胞快想清,/勞苦群眾齊攜手,若要享福快斗爭!”;任鈞的《婦女進行曲》曾被作曲家任光譜曲、《中國喲,你還不怒吼嗎?》曾由作曲家鐘川譜曲;蒲風的《搖籃歌》曾由孫慎譜曲;柳倩的《五月進行曲》曾由音樂家張曙譜曲以及蒲風的《六月流火》、穆木天的《江村之夜》運用大眾合唱詩,努力創造新的形式……。這些都證明中國詩歌會詩人重視詩歌與音樂的結合,進而使民眾“在歌著新的歌曲之際,不知不覺地得到了新的情感的薰陶”,“完成它的教育的意義”[1]穆木天:《關于歌謠之創作》,《新詩歌》第2卷第1期,1934年6月1日。后收于《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這也說明,以中國詩歌會為代表的“左聯詩歌”不僅認識到新詩的內容要同人民大眾生活的現實緊密地聯系起來,而且新詩的形式也必須同人民大眾的接受水準、藝術欣賞力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樣,在努力運用俗言、俚語和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的過程中,30年代新詩的大眾化形式“選擇”便在主題、觀念的制約下確立了其實踐的路向。
“詩歌大眾化”問題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曾一度表現為朗誦詩和解放區街頭詩的繁榮。朗誦詩,這種以詩人高蘭為代表的詩歌形式,曾由于“文字通俗化”、“有韻律”和“熱烈與現實的情感”[2]高蘭:《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5頁。而體現了抗戰背景下詩歌大眾化的傾向。街頭詩,順應詩歌大眾化的形勢,其不僅源自“在今天,因為抗戰的需要,同時因為大城市已失去好幾個,印刷、紙張更困難了,我們展開這一大眾街頭詩歌(包括墻頭詩)的運動,不用說,目的不但在利用詩歌作戰斗的武器,同時也就是要使詩歌走到真正的大眾化的道路上去;不但有知識的人參加抗戰的大眾詩歌運動,更要引起大眾中的‘無名氏’也多多起來參加這運動”,更在于“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我們要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這一大時代中,從全國各地展開偉大的抗戰詩歌運動——而街頭詩歌運動,我們認為就是使詩歌服務抗戰,創造新大眾詩歌的一條大道”[3]《街頭詩運動宣言》(1938年8月7日),《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392頁。的主觀意愿。至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提出“民族形式”的口號,要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4]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一場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又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相繼拉開。“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就歷史而言,是和大眾化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就這一時期詩人柯仲平的《談中國氣派》、《論文藝上的中國民族形式》,蕭三的《論詩歌的民族形式》等文章來看,“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仍然延續文藝大眾化(詩歌大眾化)的道路,而其對于詩人、詩歌的影響,還會在40年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凸顯。
由“文藝大眾化”衍生出的“詩歌大眾化”,是30年代新詩發展中形式化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新詩主題、觀念制約和價值追求的必然結果。“大眾化”問題的出場,雖表面上呈現出對20年代“五四”新文學精英立場、文化啟蒙主張的“反動”,但其適應社會形勢發展、注重解決現實問題的實踐性,卻使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在上述關于“詩歌大眾化”所涉及的形式之外,能夠和“國家主題”發生關聯的,還可以列舉敘事長詩和諷刺詩等。其中,前者可以以蒲風的《六月流火》、王亞平的《十二月的風》、田間的《中國,農村的故事》、《給戰斗者》以及楊騷的《鄉曲》為代表,主要是可以更為充分地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產生更為顯著的功用意識;后者可以以中國詩歌會的任鈞為代表,他1936年出版的《冷熱集》是中國現代詩壇上第一本諷刺詩集。其辛辣尖銳的筆法,嫉惡如仇的情感,形象通俗的諷刺,對侵略者、反動派以及賣國投敵者給予了無情的揭露。這些創作形式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詩歌的創作方法、意象使用等問題,但顯然,其具體探討應當屬于另一范疇的內容了。
四、以“土地”為核心之意象叢的生成
意象,既是詩歌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概念,同時也是主題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概念。按照《比較文學術語匯釋》中的說法,意象“是具有某種特殊文化意蘊、文學意味的物象。它存在多種層次,可以是一種自然現象和客觀存在,也可以是一種動植物,還可以是一種想象中的事物,等等”[1]尹建民主編:《比較文學術語匯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頁。。通過詩人內心體驗與客觀物象的融合,主、客觀意、象內外相合,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歷來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突出特點。進入現代之后,意象研究受到西方文藝理論各學科交叉、互見和意象派詩歌的影響,得到了深入的發展。“提到意象,吾人立刻會想到龐德(Ezra Pound)的定義‘意象就是在一剎那間同時呈現的一個知性及感性的復合體’;這復合體能使人在欣賞藝術品獲得一種從時空的限制中掙開來到自在感、一種‘突然成長的意識’。意象能在外面面對藝術品的剎那間給我們的感覺是自足的,然后我們才會想到它們所可能給出的意義。(筆者注:后一句在陳鵬翔的文章中被注明語出弗萊)。”[2]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年版,第32頁。從多年來致力于主題學研究、成績卓著的臺灣學者陳鵬翔談論“意象”時熟悉援引龐德、弗萊的理論,我們不難看出現代視野中意象的認知邏輯及其理論溯源。當然,從主題學研究的角度上看,意象研究也需做如下的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意象都具有主題性的意義。只有當意象作為一種中心象征,與作品的主題發生緊密關系時,才可以成為主題學研究的對象。”[3]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第2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頁。
1930年代,新詩由于特定的時代語境,在書寫國家主題時往往選擇某些特定的意象,如祖國(包括中國、國家)、土地、太陽、長城等等,從而在貫穿詩歌作品的過程中形成特殊的意象叢,而其中,又以原本是自然意象的“土地”為核心。以艾青寫于這一時期有關土地意象的詩為例。《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表于1938年1月16日《七月》第二集第七期),以“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開頭并在詩中前后重復出現四次,足可以作為全詩的主旨句。在這句詩中,“雪”、“中國的土地”由動詞“落”前后相連,初看儼然是一句寫實;然而,“寒冷”、“封鎖”的介入卻使“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變得不再簡單。“中國的苦痛與災難/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又漫長呀!……”“中國的土地”因“雪落”而遭遇“寒冷的封鎖”,但在寒冷的象征背后,卻是“饑饉的大地”、“苦難與災難”的中國,由(苦難的)“土地”而隱喻出的(苦難的)“中國”。這是寒意遍布的“土地”,同樣也是遭受外敵入侵的“中國”。詩的結尾句“中國/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所寫的無力的詩句/能給你些許的溫暖么?”使詩人內心的“意”和“土地”之具象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而國家主題所包含的諸多層面也正在詩人“土地”意象的使用中得以藝術的呈現。
同樣地,在《手推車》(作于1938年初,后收入詩集《北方》)中,“唯一的輪子”的手推車,發著“尖音”,穿過無數枯干了的“河底”,穿過一個個“山腳”、貧窮的“小村”,“以單獨的輪子/刻畫著灰黃土層上的深深的轍痕/穿過廣闊與荒漠”,“徹響著”同樣也是“交織著”“北國人民的悲哀”。聯系詩作的時代背景,可以明顯感受到“手推車”其實走過的是一次有關“土地”的遷徙之旅:孤獨、簡單、在寒冷中穿行的“手推車”在灰黃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而“北國人民的悲哀”正是在土地上遷徙體驗和感受到的(既有主觀、也有客觀看到的),至于在此背景上思索“手推車”、“北國人民的悲哀”,人們不難聯想到戰爭造成的災難、貧困甚至流亡。
《北方》(發表于1938年3月1日《七月》第二卷第十期),以穿越歷史和現實的筆法,寫出“北方是悲哀的”。被“沙漠風”卷去“生命的綠色與時日的光輝”的“北方”,惟余“一片暗淡的灰黃”。冬日的土地、孤單的行人、修長而又寂寞的道路……北方的土地披上了“土色的憂郁”:災難、不幸、貧窮與饑餓,使“我”這來自“南方的旅客”,深愛著“悲哀的北國”,這里不但有我“祖先的骸骨”,還有不屈的靈魂,因而,“我相信這言語與姿態,/堅強地生活在大地上/永遠不會滅亡;/我愛這悲哀的國土,/古老的國土/——這國土/養育了為我所愛的/世界上最艱苦/與最古老的種族。”
從艾青三首關于“土地”意象的詩,我們可以讀解出詩人賦予“土地”意象的隱喻義和象征義。“土地”意象當然可以借助相關的意象(如“手推車”)及地域空間(如“北方”)加以多方呈現,但在冬日、雪、灰黃、憂郁等這些虛實相間的詞語修飾下,“土地”的苦難意識使其成為時代中國的生動而真實的象征物。而從“國家主題”的層面上說,或以具象、或以觀念(審美)面目出現的“土地”意象,正是由于其是包含象征性的表意之象,才與一般的文學形象相區別,進而在反復出現、蘊含作者濃厚的思想感情的過程中,與作品主題發生了緊密的關聯,成為主題學研究的對象。
除上述列舉的艾青詩中的“土地”意象之外,雷石榆的《被強奸了的土地上》(《夜鶯》,1936年6月15日第一卷第四期)、臧克家的《要國旗插上東北的土地》(《光明》,1936年11月15日第一卷第十一號)、王亞平的《失地上的故事》(《文藝陣地》,1938年6月1日第一卷第四號)等等,都以書寫土地意象的方式折射出災難深重背景下的國家主題。值得指出的是,“土地”作為一種自然意象,一直具有擴展、再生或曰存有內涵多義的“意象叢”之現象。溫流的《青紗帳》(《文學界》,1936年8月10日第一卷第三號)借“青紗帳,/咱們的城墻!”表達守住“咱們的田地家鄉”,“不賣國,不投降”,直至把“敵人趕個精光!”的決心;關露的《風波亭》(《光明》,1936年8月25日第一卷第六號),借助“風波亭”具體地點,重溫“精忠報國”的歷史故事,其現實的愛國指向是不言而喻的……通過以上列舉,我們可以看到:“土地”意象不僅包括廣袤的土地,也可以指“手推車”、“青紗帳”式的與土地的相關之物,還可以指“北方”這樣的區域空間以及“風波亭”式的具體地點……然而,它們惟有在以象征、隱喻義指涉國家時才具有國家主題的性質,這種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主題與意象之間制約與表達的辯證關系。
按照中國最常見的三種意象母題是“傷春與悲秋、離情與別緒、思鄉與懷遠”的說法,“失地上的故事”很容易衍生出流浪者和思鄉者的形象。穆木天的《別鄉曲(一)、(二)》(《北斗》,1931年12月20日第一卷第四期)、《流亡者的悲哀》(1936年,后收于《流亡者之歌》)、《七年的流亡》(1938年9月,《戰歌》2期);舒群的《在故鄉——紀念我們的“九一八”》(《光明》,1936年9月10日第一卷第七號)等大量出現在30年代的“流亡歌”、“別鄉曲”、“懷鄉詩”,都是“土地”意象與“國家主題”相互糾結之后升華的結果:由于土地的喪失、背井離鄉,所以“別鄉曲”、“流亡者之歌”以及懷念故土之歌才如此真摯、深沉、動人,而由此生發的“流浪主題”無疑是“土地”意象延伸的另一結果。
如果說“土地”意象由于30年代特定的歷史背景,很容易染上悲涼、憂郁的色調,進而和流亡者、懷鄉者聯系在一起,那么,作為“土地”意象的“對應物”,“太陽”意象往往會成為追求光明、理想的現實寫照。在1938年4月艾青寫于武昌的長詩《向太陽》中,“太陽”意象及其在詩中可以聯想到的場景,自然可以作為30年代國家主題與詩歌意象研究之間的又一話題。顯然,“太陽”意象的出現,揭示了30年代新詩國家主題的另一表現方式,它使詩歌在鍍上“光明”和“灼熱”的同時,負載了詩人的理想與渴求,因而,其指向也必將面向時代的未來。
五、寫作的“轉向”與心靈的真實
如果將社會現實作為國家主題的物質層面,將詩歌表現國家主題作為一種精神吁求,那么,詩人在以詩歌形式呈現國家主題時必然會涉及心靈的真實,且包含此刻書寫國家主題的渴望。由此縱觀30年代中國新詩,關心國家時事、關注社會現實應當是這一階段詩歌寫作的重要方面。除那些習慣寫實的詩人會與國家主題發生共鳴之外,何其芳、卞之琳在1938年赴延安之后創作的轉向,現代派詩人徐遲于1939年寫出《最強音》等,都表明國家主題擁有的感召力和向心力。當然,從主題學自身所包含的比較視野來看,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語境下發生重大轉變的詩人往往更具代表性。為此,本文選擇東北詩人穆木天作為代表個案展開論述。
在《關于抗戰詩歌運動》一文中,穆木天曾結合國外作家的創作,認為“藝術的真實性,是由于作者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所決定的;藝術心理只是作者的政治心理的反映罷了。一個詩人的詩感,是他的政治感情所決定的”[1]穆木天:《關于抗戰詩歌運動》,《文藝陣地》第四卷第三期,1939年12月1日。。從藝術心理是政治心理的反映之角度論及一個詩人的“詩感”,在抗日戰爭背景下,自然可以作為一種鮮明而有力的主張。無論從現代派詩人,還是從現實生活經歷的角度來看,穆木天都堪稱30年代新詩中“寫作的轉向和心靈的真實”的典型個案。穆木天,原名穆敬熙,1900年出生于吉林。1918年考取官費留學日本。1919年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轉向了文學。1921年7月參加創造社。1923年開始從事新詩創作。日本留學的生活處境、情感的焦慮特別是“去國懷鄉者”的情緒,使穆木天很容易沉浸于象征主義的世界之中。結合他在這一時期的詩學論文《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我們可以看到出于對“中國人現在作詩,非常粗糙”的不滿,穆木天提出要求“純粹的詩歌”以及“詩的統一性”、“詩的持續性”、詩的“暗示能”[2]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創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16日。,他的名篇《落花》、《蒼白的鐘聲》也確然實踐了其理論主張。基于此,文學史歷來將20年代的穆木天作為初期象征派的重要詩人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1929年夏天回到故鄉之后,穆木天通過訪親問友和實地考察,對東北的社會情況有了具體、深入的了解,便迅速轉向了革命。1931年1月,因向學生宣傳革命思想而遭到解聘的穆木天從東北抵達上海不久,便直接投身于“左聯”,負責“左聯”創作委員會詩歌組的工作;隨即,其創作風格和寫作主題也發生了強烈的反差——從其發起中國詩歌會,為其機關刊物《新詩歌》旬刊創作《發刊詩》(具體見前),人們可以感受到其熱烈的號召與吁求,是希望將詩歌和生活捆綁到“政治”的戰車之上。他在《心境主義文學》一文中指出“這種心境文學,是回避現實的,是同‘社會的表現’相背馳的”,“這是反映著文人生活之空虛”,帶有“八股化的傾向”[3]穆木天:《心境主義的文學》,《現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在《我與文學》中檢討自己:“在象征主義的空氣中住著,越發與現實相隔絕了,我確是相當地讀了些法國象征詩人的作品。貴族的浪漫詩人,世紀末的象征詩人,是我的先生。雖然我在主觀上是忠實的,可是在拋棄了我的Moraliste的任務之點,我是對不起民眾的。”[4]穆木天:《我與文學》,原文收入鄭振鐸、傅東華主編的《我與文學》,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版。本文依據陳惇、劉象愚編《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第428頁。從中人們可以讀出他正在向“過去”告別、向“現實”懺悔。從其大量詩歌創作的情況(主要收入詩集《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以及詩論集《怎樣學習詩歌》(1938)可知,30年代的穆木天正在經歷從“現代”到“現實”的轉變。
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驅常常來自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地區(比如:江、浙、皖)不同的是,穆木天“東北大野詩人”的身份,使其創作和理論只有在“東北情結”的潛在精神力量的影響下,才能完成“審美與功用”、“國家與民族”的現實轉變。一面是身負國仇家恨、體驗流亡者的痛苦,一面是擺脫源于地域邊緣文化的地位,渴望得到時代與現實的“身份確證”,在這一告別過去、消解象征主義世界的過程中,同樣被消解的還有文學藝術上并不純粹的“現代成分”。“真實的詩人,是須在其詩中,表現出他的獨特的崇高的情緒。那種獨特的情緒,代表著在該時代為本質的情緒”;“詩人,為了對于自己忠實起見,是必須對于客觀的現實忠實的。真正地認識客觀的現實的人,真正地認識社會的動向的人,是才能獲得崇高的真實的感情的。”[5]穆木天:《詩歌與現實》,《現代》第5卷第2期,1934年6月1日。顯然,此時的穆木天首先是以現實決定論的標準衡量“當代詩人”并為其進行歷史定位的,而后,才是從現實中滋生出來的情感以及作家可以存留的意識能動性。從30年代詩人的創作不斷為現實所同化,加入“中國詩歌會”后的思想進步、創作轉向,已構成了穆木天詩歌創作及理論思考的基本出發點。然而,火熱的現實不能匱乏火熱的情感,使得穆木天在賦予詩人政治義務的同時,最終要以“偉大的情感”,將詩人作為“傳達全民族的感情的一個洪亮的喇叭”[1]穆木天:《目前新詩運動的展開問題》,1937年8月《開拓者》。本文依據陳惇、劉象愚編《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第158頁。:
一切的帝國主義,退去吧!
一切的民族叛徒,退去吧!
我們的詩,要是一支降妖劍,
有他的強烈的光芒和聲息。
一切都形式的束縛,退去吧!
我們的詩,要是浪漫的,自由的!要是民族的樂府,大眾的歌謠;
奔放的民族熱情,自由的民族史詩。——《我們的詩》(1936)盡管,由于個人以及故鄉的緣故,穆木天的“寫作的轉向與心靈的真實”在30年代詩人群中有自己獨特之處,但這并不影響他作為從“現代”到“現實”、從遠離“政治”到回歸“政治”的典型。事實上,隨著“九一八”之后,國家民族危亡的態勢日趨明顯,任何一位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詩人都因時代的感召,而在創作上發生一定的變化或者是主題意義上的集中。象征派詩人李金發的《亡國是可怕的》(1938)、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的《元日祝福》(1939),都相對于以往各自的創作呈現出變化的態勢,只不過,由于其熟悉現代派的藝術手法,其詩作并不呈現直白、呼喊式的狀態,且更重視詩歌的藝術表達而已。藝術地看,現代派詩人在30年代的“轉向”既折射出深遠的時代背景,又對于詩歌藝術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從戴望舒的《談國防詩歌》,胡風、艾青等參與的《宣傳·文學·舊形式的利用》的討論等文章可以看到,詩歌的公式化、簡單化以及不加區分的舊形式的利用,雖出于現實、大眾化的目的,但這些過于注重宣傳、功用的做法,往往是在弱化詩質及其藝術性的同時并未完全面向多層次且為數眾多的“大眾”,而如何更為切實平衡詩歌審美和功用之間的辯證關系,恰恰可以作為這種“轉變”留給其后詩歌寫作的課題之一。
從以上分析可知,3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與30年代社會的變化息息相關。“國家主題”作為30年代新詩與時代、現實、生活多元對話的結果,不僅由于現實的緊迫感生成了新詩的特定主題,而且還影響到了新詩在具體創作過程中的藝術選擇。作為獨立的年代史個案,3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延續、深化了20年代新詩的同類書寫,并呈現出開放的態勢,而4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了新的路向。
〔責任編輯:平嘯〕
On the Theme of Nation in New Poetry in the 1930s
Zhang Liqun
“The theme of nation”involves literary theme,subject matter,image and so 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the theme of nation in new poetry in the 1930s is unique owing to the particular times.Taking the tempor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sent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theme of nation in new poetry in five aspects,trying to draw a picture of new poetry in the 1930s to provide cases for the study of the theme of nation in new poetry.
the 1930s;new poetry;the theme of nation
張立群,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 110036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流動人員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