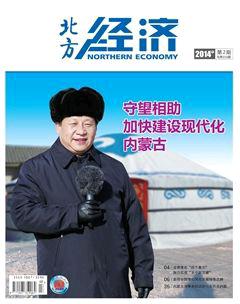中國城市女性環境意識研究
張斐男



目前,人們對環境意識的概念界定并沒有達成共識,比較主流的觀點是:環境意識包括環境知識、環境價值觀、環境保護態度和環境保護行為四個環節。環境行為作為環境意識的一個方面,其研究也比較廣泛。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對環境友好行為與性別關系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表明,中國城市居民的環境關心確實存在著性別差異,這與國外一些已有研究的發現是一致的。”(洪大用、肖晨陽,2007)還有學者進一步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居民中,男性所作出的環境友好行為比例低于女性,而女性的環境友好行為更傾向于一些私人領域內的日常生活環境行為。”(龔文娟,2008)
一項關于環境關心的性別差異研究表明:“如果剔除環境知識的作用,所有自變量對環境關心的解釋力度(R平方)將不到10%。”(洪大用、肖晨陽,2007)這10%的內容中環境意識占多大的比例呢?根據已有的研究,認為女性的環境友好行為多于男性,那么中國城市女性的環境意識處于什么層次呢?這就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理論假設與數據變量
本文的基本假設是:女性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顯著相關;女性的環境意識與受教育、年齡、婚姻、收入、單位性質等情況有關。
基于社會化和勞動分工的性別差異這兩種理論假設,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被期待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較之男性承擔著更多的家務勞動,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機會進行環境友好行為。那么女性的環境意識就通過她們的環境友好行為有了展示的機會。同時,人們的環境意識大多是通過教育、媒體宣傳等方式建立起來的。女性的關注點與男性是不同的,男性更注重經濟、政治等宏觀問題,女性則傾向于消費、生活等微觀問題;婚姻對于女性的影響要大于男性;在現代社會中,女性的教育水平、收入狀況等也與男性有普遍差異。這些情況都對女性的環境意識產生影響。基于這種分析,本文的具體操作化假設為:
假設1a: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與環境意識成正相關;也就是說,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環境意識就越強;
假設1b:已婚女性較之未婚女性環境意識要更強;
假設1c:女性的年齡與環境意識成正相關;年紀越大的女性其環境意識越強;
假設1d:女性的收入與環境意識成正相關。
本文的數據采用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城市部分關于環境問題的數據。在全國實施問卷調查的抽樣城市中,最后完成樣本5078人,其中有效樣本5073人,有效回收率約為99%。本文著重對于城市女性居民的環境意識進行研究,所以選取了總樣本中性別為女性的樣本,共3059人。
女性的“環境意識得分”為本文的研究變量。另外,環境意識能夠對環境友好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本文也將對女性的環境友好行為做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預測變量包括教育程度,這是一個定類變量,分為文盲、小學及私塾、初中、高中(包括中專及技校)、大專以上。婚姻情況分為已婚和未婚,離婚后未婚、離婚后已婚、喪偶未再婚、喪偶后再婚,本研究把這幾種情況綜合為已婚和未婚兩種。年齡和收入是連續變量。
二、分析和發現
對問卷中10項環境友好行為進行描述性統計,發現“垃圾分類投放”、“與自己的親戚朋友討論環保問題”、“主動關注媒體中報道的環境問題和環保信息”這三項環境友好行為,女性居民回答“偶爾”、“經常”的比例明顯高出平均水平。“采購日常用品時自己帶購物袋”、“對塑料袋反復利用”這兩項環境友好行為也較之平均水平略高。而“為環保捐款”、“積極參加政府和單位組織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積極參加民間環保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這三項環境友好行為中女性回答“偶爾”、“經常”的比例與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自費養護樹林和綠地”、“參加要求解決環境問題的投訴和上訴”這兩項環境友好行為中回答“偶爾”、“經常”的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
這說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環境友好行為要高于在公共領域做出的環境友好行為。這主要與女性的生活經歷相關,因為女性采購、投放垃圾等活動要明顯多余男性,這使得女性有比男性多的機會做出此類環境友好行為;而在公共領域內,男性處于主導地位,在公共領域內的環保行為多與單位、收入相掛鉤,因而“為環保捐款”、“積極參加政府和單位組織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積極參加民間環保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這三項環境友好行為中女性回答“偶爾”、“經常”的比例與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女性的收入水平平均低于男性,因此,在涉及到金錢花費的環境友好行為上,女性的參與比例則要低于平均水平。
可見,女性的環境友好行為并非完全高于平均水平。通過對環境意識與環境友好行為的簡單交互分類分析,二者具有顯著性關系,并且其解釋力均高于0.5。下面,筆者嘗試以三個模型來解釋教育、年齡、婚姻、收入、單位類型對于女性環境意識的影響。
把環境意識得分與教育、年齡、月收入、單位性質、婚姻狀況分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獲得了五個模型:
對這五個模型進行F檢驗發現,教育、年齡、月收入對于環境意識的影響均具有顯著性,但單位類型及婚姻狀況對于環境意識沒有顯著影響,因此,剔除這兩個變量。在剔除單位類型和婚姻狀況這兩個變量后,剩余三個變量影響力由高到低排列為:教育、年齡、月收入。通過R2檢驗,發現納入教育程度這一變量能夠解釋3.9%的差異;納入年齡這一變量能夠多解釋4.7%的差異;納入月收入這一變量則能夠多解釋4.8%的差異;婚姻狀況本身對于環境意識不具有顯著性,但在與其他變量一起參與回歸時,婚姻狀況這一變量使其解釋力達到4.9%。所以,婚姻狀況可能與年齡等變量有相關性。通過F檢驗和t檢驗,在“剔除環境知識的作用,對環境關心影響不到10%的所有自變量”中有4.9%來自于環境意識。對于環境意識這4.9%的解釋力貢獻最大的是教育程度這一變量。婚姻狀況、教育、年齡和收入這四個變量間也具有相關性。
根據模型分析,假設1a得到部分驗證。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與環境意識成正相關;但是否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環境意識就越強”還需進一步檢驗。但總的來說,教育對于環境意識的影響是尤為重要的。美國著名環境社會學家漢尼根指出,成功地建構某種環境問題必須注意:(1)某種環境問題必須有科學權威的支持和證實;(2)擁有科學普及者是重要的,如果沒有他們的普及,某些問題只能是深奧難懂的研究專題;(3)某一潛在的環境必須以非常醒目的符號和形象詞匯加以修飾,以引起注意。(Hannigan 1995)在這里,教育擔當起普及科學知識的任務,起到了把科學知識普及化的作用,使得深奧的問題能夠為大眾所接受。所以,接受過教育的人獲取環境知識、了解環境問題的機會就較之未接受教育的人要多,其環境意識也就在這樣的教育中慢慢培養起來。在教育中,環境知識和環境問題多以簡單的名稱或者圖畫出現,更容易深入人心,容易被人們接受。人們一旦接觸過這些“符號”或“形象詞匯”,在以后的生活經歷中,再次使用它們的機會就會增加。另外,對于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來說,即使他的環境意識并不強,但仍然具備一定的關于環境問題的知識和信息,雖然并不是十分豐富、甚至不完全正確,但這類人潛在的環境意識更容易喚起。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某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詞匯或者事件時,他們會給予較之未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更高關注,也就更容易建立起環境意識,從而做出更多的環境友好行為。
假設1b被否定。假設1b為:已婚女性較之未婚女性環境意識要更強;但模型顯示:未婚女性要比已婚女性的環境意識強。這可能受到了年齡和教育等變量的相互作用的影響。在一般情況下,已婚女性較之未婚女性在生活領域具有更多機會做出環境行為,但在公共領域內,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是否工作、收入如何等方面。因此,按照模型未婚女性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才具有較強的環境意識。
假設1c:女性的年齡與環境意識成正相關;年紀越大的女性其環境意識越強。這一假設看似與假設b矛盾,而實際上這與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有關。一般情況下,女性年齡越大生活經驗越豐富,對于環境意識的培養時間就越長;另一方面,有工作的女性中年齡與收入是成正比的,收入又與教育相關,因此,當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環境意識越強時,年齡與環境意識也是成正比的。
假設1d得到驗證,即收入越高的女性其環保意識越強。結合與環境行為的相關分析,收入高低對于環境意識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公共領域。因為公共領域的環境意識主要體現在金錢的支出上,比如“為環保事業捐款”、“自費養護樹林和綠地”等,在這些方面,收入高的女性必然會比收入低的女性有更高的環境意識。
三、結 論
第一,教育程度是環境意識最重要的影響變量,同時,年齡、月收入、婚姻三個變量對環境意識也有顯著作用。四個變量間還具有相互作用。所以,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是提高環境意識的主要途徑。
第二,女性在生活領域的環境行為要多于在公共領域的環境行為,這不僅僅是由于女性的生活經歷,還說明女性的環境意識是不完備的。在生活領域中,諸如“垃圾分類投放”、“采購日常用品時自己帶購物袋”、“對塑料包裝袋進行重復利用”等環境行為往往與節約家庭開支聯系起來,女性的環境意識首先起于對節約家庭開支的重視;而在公共領域中的環境行為并不高于總體平均水平說明,女性對公共領域的環境意識較弱,這部分環境意識是應該給予重視的。所以,環境意識雖然與教育有較大相關性,但在女性居民中,能夠促進環境意識形成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經濟利益。因此,提高女性的環境意識除了在提高教育程度這一途徑外,還應該有其它如經濟利益等刺激因素,促使女性環境意識的提高。
由此,筆者推斷,不僅僅在女性居民中存在生活領域與公共領域環境意識水平有差異的想象,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和不同收入的人群,其環境意識在不同領域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其側重點是不同的。因此在培養環境意識的引導上要根據不同群體的環境意識側重點給予相應引導。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2C049)。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責任編輯:楊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