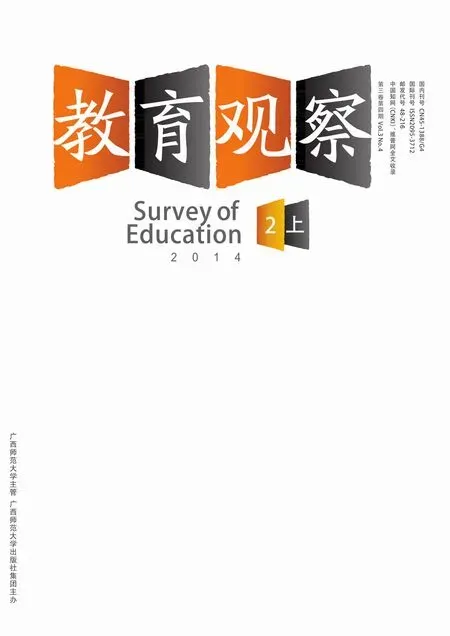淺談建構主義的學習觀與教學觀
宋春旗,陳燕燕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杜威在對教育的源流作了一番哲學歷史的考察后,指出正規教育自始便存在一種愈益擴大的內在緊張,即概念知識被剝離出其產生的具體經驗脈絡,而知識與經驗的隔離導致知識與實際生活的疏離。簡言之,學生所學的知識對其日常生活難以發揮指導和協助的作用。這種危險在現代學校教育中愈發明顯。杜威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就在于將分離的知識與生活重新合并歸一。
就我國而言,新課程改革的目的之一即是溝通學校與生活,養成學生能夠利用所學知識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乃至培養學生創新的思維習慣。教育的根本維系于教學的質量,而有效的教學需要根據學習的一般原理予以組織和安排,因為教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組織學生的學習。如今,在教育研究中,對于學習領域的探討已成一股熱潮,學習科學的出現與發展就是一個鮮明的標志。在各家學習理論中,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建構主義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我國新課程改革便以此為理論依據。
建構主義并不是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是由多種理論形成的一種思潮,而且各家理論的來源也并不一致。瑞士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和蘇聯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認知理論是建構主義的兩種主要理論源泉。雖然諸多建構理論之間分歧眾多,內容紛繁,然能統稱之為建構主義,即在于其共享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歐內斯特用“一與多”的傳統概念標志建構主義理論的這一特征。建構主義是一種哲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建構主義的經典文獻《教育中的建構主義》則以“一種新認識論”稱之。從認知的角度出發,這種新認識論所要回答的中心問題是:知識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知識的形成過程即個體學習的過程(當然,學習所涵蓋的范圍遠遠廣于知識的獲得)。換言之,學習如何可能的問題是建構主義的焦點。
一、建構主義的核心假設
在學習論的視野中,建構主義的核心假設可以表述為:學習是個體在自身已有經驗的基礎上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這也就是馮·格拉塞斯菲爾德所謂的建構主義第一原則:“知識并非被動地接受而是由認識主體主動構筑的。”[1]站在一種樸素的經驗主義立場,建構主義的這一假設近乎常識,在日常的教學實踐中,“學習是你(指學生)自己的事情”之類的話常被教師用作激勵學生的講辭。在一般意義上,學習顯然不是一種依靠外部模鑄就能實現的活動,而教師總是某種意義上現實的“建構主義者”。與此相關的一個現象是,死記硬背式的學習通常不會得到肯定的承認,即便需要純粹記憶以應付考試,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學生對于前后知識聯系的注意,以及不斷做題以掌握知識點的努力。記憶方式的區別從一個側面微弱地說明個體在學習甚至記憶過程中的差異性。
傳統的經驗主義構成了建構主義的出發點,在這個核心假設或第一原則中隱含著凝聚各種相互區別的建構主義理論的共享基礎,斯皮維稱作“木工或建筑的隱喻”[2]。“建構”(或“重構”)隱喻即是建構主義對于學習的一般或根本看法。學習是一種建構的活動,這個看似簡單的表述實際隱藏著很多含糊而重大的問題。事實上,核心假設中的每個概念都需要而且具有追問或質疑的空間,而正是這些看似明白的概念引起了研究與實踐中的誤解、混亂和失敗。
二、建構主義學習觀
(一)建構的主動性
在“建構”隱喻的視野中,學習者首先是一個主體。作為學習活動的發出者,主體(或稱學習者)擁有毋庸置疑的主動性,這也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首要之義。洛克曾于17世紀提出“白板論”,以論證教與學之可能以及教育之危險。其論證之目的固然不在于著重說明學習過程本身,但在其后來的繼承者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手上,學習被簡化為“刺激——反應”的外鑠機制。在建構主義者看來,白板論歪曲了學習的起點,個體總是以原有的經驗和認知結構來建構新的信息,而非簡單的被動接受。新信息在個體有選擇地加工和處理或編碼之后始獲得意義,因為外部信息本身乃是無意義的。因此,不僅學習無法為他人所代替,而且同一個事物對于不同的個體來講,亦標志著不同的意義。
建構主義的奠基者皮亞杰從結構主義的角度對兒童的認知發展作了原創性的研究,在他看來,認知發展的實質是個體內部的認知結構或圖式的形成、轉化和發展的過程。皮亞杰用同化和順應的概念表征認知結構發生變化的兩種機制,這樣,認知發展就是在個體頭腦中發生的智力運作過程。根據皮亞杰的研究,學習乃是一種雙向的建構過程。一方面個體憑借原有的經驗圖式不斷接受、吸收和轉化外來的刺激,使之成為自己固有圖式的有機成分,以此促使原有圖式愈益豐富,是為“同化”;另一方面,個體在遇到與其原有圖式發生沖突、分歧的刺激時,原有圖式被迫發生改造和重組,從而改變圖式本身,改變的程度隨沖突的水平而變化,從局部到整體之間形成一個連續體,是為“順應”。在這兩種不同方向的建構中,建構主義者往往更強調順應,即不斷變動的圖式,而不僅僅是在原有水平上不斷豐富的命題網絡。因為建構主義知識觀固有的實用主義性格講求應對靈活多變的問題情境之適應力,個體所遇到的諸問題情境并不能簡單地歸屬于相似的一類范疇。格拉塞斯菲爾德繼承并發展了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由此形成了激進建構主義學派。
既然認知的過程乃是個體內部認知結構的變化,而建構主義又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那么建構的含義就是學習者主動對外部的信息和刺激予以吸收、加工和賦予意義的過程。依建構主義知識觀的立場,盡管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知識乃是基于個體自身已有經驗與認知所主動建構而成的產物,而非獨立于個體之外的客觀存在物。據此,學習是一個連續不斷的主動建構的過程。
(二)建構的情境社會性
在學習即主動的意義建構過程中,個體固有的經驗與知識結構自是構成了學習的起點與推動力,同時交流與協作則構成了學習的另一個基本條件。在個體所處的情境中,社會性的因素對于個體知識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對此有頗為獨到且深刻的揭示。維果茨基區分了兩種心理機能,即低級心理機能和高級心理機能。低級心理機能是自然具有的,而高級心理機能只有在社會環境中才得以形成。由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轉化(心理結構的變化)的關鍵在于符號和活動的作用,即通過對各種工具的運用以及符號的中介,人才能夠獲得高級心理機能。對幼小個體而言,游戲活動所包含的協作與語言交流塑造著個體的經驗結構,這不僅給予個體以新的經驗與知識,而且制約著個體以后面臨新情境時的關系結構與解決路徑。所以,在個體的學習過程中,交流與協作成為個體完成主動建構的重要條件。
既然學習是個體在特定的情境中基于原有經驗與知識結構并借助交流與協作而完成意義建構的過程,則學習的實質即是個體原有經驗圖式或認知結構的改變。學習乃是主動性、情境性與社會性的,這些特點不僅契合于建構主義關于知識的看法,亦直接關系到建構主義關于教學的見解。
三、建構主義教學觀
(一)教學的起點
在建構主義者看來,教學不再是知識在師生之間的單向傳遞過程,因為學習的最終完成依賴于個體自身的主動建構。個體原有之經驗與知識結構作為學習或建構的最初基礎,構成了學習的起點,甚至規定了具體個體的特殊學習路徑。故此,教師教學之起始乃是對于個體已有經驗圖式之理解與把握,無此則教學亦失去了立身的根本。此種理解與把握亦是孔子所謂“因材施教”的前提,教師以之為學生學習的生長點,對之予以適當的引導與激發。由此可知,教學并非知識傳遞的過程,而在于個體自身對于外來信息或刺激之處理與轉換。這一主動建構的過程在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中有深刻的闡釋。所謂“最近發展區”,指的是個體在已有的知識水平基礎上所可能達到的新的高度,在此新的高度與已有水平之間的距離被稱作“最近發展區”。教師根據最近發展區規定教學之任務,選取引導與激發之方法,以避免過與不及之弊。
(二)教學的情境性
知識發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借助他人之力,如協作、交流、利用必要的工具等,并經由個體自身的意義建構而獲得。所以,理想的教學環境亦須包含三種要素,即情境、協作與交流。首先,教師應創設一種逼近于現實的學習情境,因為現實情境乃是復雜而多變的,設若學習情境迥異于抑或簡單于現實情境,則個體在其中所得之知識亦難以應對真正的現實問題。這樣的觀念直接來源于建構主義關于知識之生存性質的判斷。所以,教學內容以真實性任務為宜,目的在于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種種問題。其次,建構主義者提倡合作學習,建立學習共同體,其理由不僅僅在于社會交往之于學習的重要作用,亦有此一層的考慮:不同個體甚至對于同一事物或信息的理解都存在不同之處,不同個體亦只是把握了同一事物的若干方面,則個體之間的寫作與交流有助于個體對于事物的多樣而深刻的理解。這后一種理由即從主體間性發生。
(三)教學的整體性
現實問題多牽扯多種不同的概念與命題,全不顧所謂學科之間的界限,故建構主義者亦提倡沖破學科之間的界限,推崇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同時,又因為現實問題發生于具體而特定的情境之中,而解決問題之工具則隱含于此情境中,所以,建構主義者主張僅僅提供解決問題的原型,即科學家的研究、探索過程,以此為基礎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解決之工具與方法,同時亦為個體之探索留下充裕的建構空間,以應付多變的具體情境。此外,建構主義者亦倡議一種整體性的教學模式。圍繞某一具體問題,提出包含多層子問題的整體性任務體系,并建立起以關鍵概念為核心的概念網絡。進入此概念網絡的切點并無一定,既可從最抽象之原理入手,亦可從最具體之感受切入。此種教學模式迥異于傳統的按照概念層級逐級傳授的直線型教學模式,網絡式的概念結構顯然無法依據直線型模式予以教學。
(四)教師角色的轉變
在建構主義教學觀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教師角色的轉變。教師從傳統的知識呈現者、權威者脫離出來,而成為理解者、傾聽者和引導者。學習者成為教學過程中的中心,教師則作其學習過程中的高級伙伴,引導與幫助其克服建構過程中的諸種困難,卻不是方法與知識的提供者與灌輸者。由是,教學之目的在于幫助學生逐漸擺脫教師之幫助,完成自身學習之獨立。盡管如此,教師之地位與作用較之以往并無絲毫弱化。因為根據維果茨基的研究,學習者之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離不開其與成人的交往。教師的作用仍然巨大,只是不體現在提供知識層面,而表現在溝通交流以幫助學生建構知識的層面。
[1] 歐內斯特·保羅.一與多[M].斯特弗,蓋爾.教育中的建構主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 斯皮維·南西·納爾遜.書面話語:一種建構主義觀[M].斯特弗,蓋爾.教育中的建構主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 〔美〕申克.學習理論:教育的視角[M].韋小滿,等,譯.3版.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4] 高文,等.建構主義教育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
[5] 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劉儒德.建構主義學習要義觀評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8(1).
[7] 呂林海,高文.走出建構主義思想之惑[J].電化教育研究,2007(10).
[8] 張桂春.建構主義教學思想的再構[J].教育科學,2004(12).
[9] 劉儒德.知識觀、學習觀、教學觀[J].人民教育,2005(17).
[10] 張建偉,陳琦.從認知主義到建構主義[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6(4).
[10] 陳琦.認知結構主義與教育[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8(1).
[11] 高文.教育中的若干建構主義范型[J].全球教育展望,2001(10).
[12] 潘玉進.建構主義及其在教育上的啟示[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