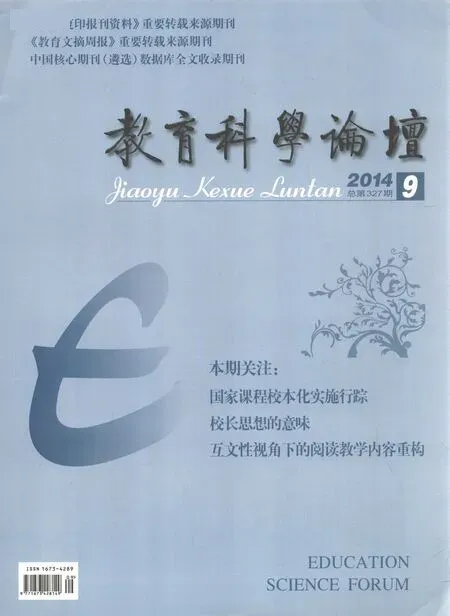互文性視角下的閱讀教學內容重構
●畢美娟
王榮生教授曾指出當前閱讀教學的主要問題,在于教師引導學生從事低層次、低水平的“掃讀”,而不是高層次、高水平的“理解”。他將廣西觀課的印象總結為教師閱讀教學的“三部曲”:指示性尋找——胡亂地談論——激情式號召[1]。這種“掃讀”“三部曲”使得閱讀教學呈現出視野封閉、 互動膚淺和意義虛無特征。這種閱讀教學內容被預設且固化為某幾點,簡單的線性思維封殺了學生基于文本內容的豐富思想感情, 閱讀教學創新以及教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相應淡失。
一、互文性及其對閱讀教學的重要規限
互文,在中國古代,多指一種修辭現象;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間的意義關涉,屬舶來品。有學者對二者的區分曾專門探討[2]。 文本也取其廣義,不僅指書面的文字文本,也包括口頭的話語文本。《論語》中孔子對弟子問“仁”、問“政”、問“孝”等同一問題的不同答語,就體現出一種極為鮮明的互文性。互文性即文本間性,“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3]。一篇課文不是孤立的作品, 而是和其他作品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關聯。 閱讀教學雖然不能也不必窮盡由這篇課文所延展開來的文本“森林”,但是總可以發現和這篇課文距離相近的幾棵“樹”,進而引導學生管窺到相對較大的問題視域與意義空間。 教師引導學生關注的,絕不僅僅是單篇課文這棵孤立的“樹”,而是由這棵“樹”所引起的書面文本和口頭文本的豐富關聯,進而領會到意義尋求的由此及彼與觸類旁通。我國古人強調的“神與物游”,便是建基于互文性文本的闊大視野與自由想象。
互文性對閱讀教學就因此具有了種種規限,上述“掃讀”式閱讀教學顯然是嚴重違規。 互文性閱讀教學的目的,在于提升師生的語用能力和自我心性,突破復制教學模式和記憶式學習牢籠。
(一)閱讀教學要從單篇視域走向多篇視域
關聯性文本選擇使得特定文本意義的視域擴大,給讀者帶來想象張力和思辨空間。思辨睿智和審美興味, 是互文性閱讀必然會帶給人的思想情感福利。
(二)閱讀教學要從還原再現走向創造生成
互文性理論注重多部作品的疊合與互滲, 彼此映襯與相互折射。 這種文本上的互文性正好印證了思維上的共通脈絡。 文本作為一種選擇性記憶和書寫,存在許多意義空白點。讀者自然會受到作者思維圖景和邏輯思路的某種指引和牽制,但是讀者的思想旁逸與思維變異也會存在。
(三)閱讀教學要從教控制學走向教解放學
新語文課改提倡“個性化閱讀”,個性化閱讀其實就是一種互文性閱讀。 閱讀教學不能引導學生追求同一性閱讀,而是追求和而不同的互文性,體現文本意義闡釋的“多聲部交響”。 此時的互文性主要是指課文文本與師生話語文本之間的意義關涉, 交織著課文文本與其他書面文本之間的意義關聯。
二、互文性視角下閱讀教學內容重構的三個層次
王榮生教授曾指出:語文教學內容既包括在教學中對現成教材內容的沿用,也包括教師對教材內容的“重構”——處理、加工、改編乃至增刪、更換;既包括對課程內容的執行, 也包括在課程實施中教師對課程內容的創生[4]。課程內容的創生既有教師視角的文本理解和教學處理,也有學生視角的文本思考。學生或對或錯或不足或困惑的文本理解, 是課程內容創生的重要基石。 于是,課程內容、教學內容和教材內容三者,就構成極為鮮明的互文性。從互文性視角看,閱讀教學內容重構包含以下三個層次:
(一)文本意義發現的知覺建構
此系師生對課文文本與關聯文本的對象性實踐。文本符號作為共享的集體記憶和文化通道,其意義能夠被群體中的個體所感知與發現。 作為受教育兒童,由于知識經驗的不足,必然會存在集體記憶上的缺損與文化通道上的障礙, 其關于文本意義的主動建構自然會出現某種不足, 師生的文本意義發現就會存在認知落差。認知落差的存在,正是新語文課程改革強調要“尊重學生獨特的感受、體驗與理解”的緣由,是教師實施教學的重要依據。
(二)思想認識交流的經驗互構
此系師生圍繞課文文本與關聯文本的意義建構而發生的溝通性實踐。閱讀教學要求學生課前預習,也就是要求學生帶著對課文文本意義的某種發現與困惑到課堂上來,與人分享或尋求支援。實施了這一環節,教師就是將學生主動建構出的或對或錯或不足或困惑的文本理解,轉變成重要教學資源,同伴之間的相互學習就成為閱讀教學內容重構的重要手段;缺失了這一環節,閱讀教學內容就是教師對學生思想認識的簡單外部強加,閱讀教學于是就成為教師的霸道施教。
(三)文本自我理解的反思重構
此系師生由認識分歧和認知困惑而誘逼出的倫理性實踐。 教師有義務與責任幫助學生意識到課文文本理解或對或錯或不足或困惑背后的邏輯推理,實現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思維遞進與認識攀升。學生的文本理解和學生自我之間,存在某種一致性關系,見證著學生的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過程。應試背景下的閱讀教學大多引導學生關注文本意義本身,所以才會推崇與復制名家的文本理解,卻讓學生自我淹沒與迷失。 其實,主體和文本的關系、主體和主體的關系都是中介, 最終都要回到主體與自己的關系上來。“理解他人就必須在自己身上設身處地地‘重構’他人的經驗。理解作為一種再體驗,意味著體驗他人之人生與體驗自己之人生的一致性, 其實也就是理解自我、發現自我。 ”[5]
三、互文性視角下閱讀教學內容重構的主要策略
由上述三個層次所決定, 閱讀教學內容因為不同主體基于自身經驗和語境、 時間上的變化和他人經驗和語境的刺激等而出現微妙變異。 閱讀教學要擺脫對文本理解現成結論的先在性控制, 教師要學會虛心傾聽學生的看法, 使得語文課堂教學成為一個“時機化的”、“境域發生式的”和“相互構成著的”[6]意義生成場域, 師生的課前準備都會因為課堂情境中的互動機變而出現調整和變化。 經歷上述三個層次,文本對象的自我認知,文本對象的他者認知,以及基于自我與他者文本對象認知辨析的自我認知三者,就內在地包含著因為時間變化,所帶來的學生思維轉變。這就是佐藤學教授提及的,學習即三種對話性實踐的有機統一體:學習不再是學生單純掌握知識的認知性、文化性實踐,還是協調人際關系的社會性、政治性實踐以及致力于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的倫理性、存在性實踐[7]。那么,互文性視角下閱讀教學內容重構該如何操作? 下面以陳鐘樑老師的 《合歡樹》課堂教學[8]為例加以解釋。
(一)多角度文本關聯策略
《合歡樹》是作者對母親的溫暖回憶與深切懷念,癱瘓對母子的創痛與母親對兒子的至愛,以及理解母愛的漸進心路歷程,是苦難中溢滿溫情的生命書寫。合歡樹本身就是一個隱喻,苦難生命歷程中的母愛所昭示的人格品質和所孕育的精神果實, 感人肺腑。陳老師的教學中出現三次橫聯,便顯示出三個角度的互文性:一是主題。教學起始階段引入史鐵生《我與地壇》中的一段文字:“母親生前沒給我留下過什么雋永的誓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誨,只是在她去世之后, 她那艱難的命運, 堅忍的意志和毫不張揚的愛,隨光陰流轉,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鮮明深刻……”后面又聯系王安憶對史鐵生散文的評價:“在敘述中流露原初面目的情感”,“情感經過歷練逐步趨向理性”,“理性最終孕育著哲學的果實”,并借“意蘊”一詞再次將《合歡樹》與《我與地壇》相聯系。 “地壇”與“合歡樹”具有某種對應關系,都是一種精神象征。二是寫作手法。教學過程中,陳老師為了引發學生思考作者寫母親為何還要寫一群老人,聯系《故鄉》中作者寫閏土還寫楊二嫂, 談人物寫作關涉到文章主題的深度與厚度, 一種極其重要的折射作用。 三是句義。陳老師在引導學生理解“悲傷也成享受”一句時,聯想到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即一個小孩走進森林深處的恐懼與走出困境的喜悅, 并引入茨威格的《世界最美的墳墓》,向學生傳達“時間距離產生心理美感”信息,母親對兒子傾心付出的溫情元素與作者對母親愈來愈深刻的理解,這種心靈的呼應與疊合,使得母親離去的悲傷中也和著許多感動和美好。
(二)高質量對話互動策略
從“灌輸”走向“對話”,對話教學是新課程改革以來極力提倡的重要策略。 對話教學的兩個要素在于問題設計的精準性與答案尋求的思辨性,它體現出教師“讓學生學”的教學策略。 對話式閱讀教學的關鍵在于尋求差異,催生學生的個性化閱讀,這與一些老師將教學導向一個預定答案不同。 陳老師注意用問題引發對話,如第一自然段中“母親什么性格”,學生依次道出“活潑”、“開朗”、“好強”、“愛美”;第二自然段的母親變老表現,學生指出“頭上開始有了白發”, 老師補充 “不斷地重復一句話”(“怎么會燙了呢? ”);如引導學生理解母親為什么挖含羞草(后來變成合歡樹)回家? 理解含羞草和母親的相似處,便有一個逐步深入的師生互動過程, 將學生從母親愛美、 含羞草生命力頑強過渡到對母親與含羞草的一體化認識:溫柔而堅強。 后來讓學生思考作者“為什么多次提到那個小孩兒和樹影兒?”學生提到“折射”與“生命的循環”,耐人尋味。整個教學過程存在一個對話互動的互文性格局。
(三)深層次語言咀嚼策略
作品語言的深層次意義是需要咀嚼的, 是需要結合具體語境來理解的, 作品閱讀和闡釋就會存在文本語境與讀者語境的復雜交互。 陳老師在引導學生理解老太太們和史鐵生在一起時從 “聊天喝茶從不提起母親”到“終于提起母親”,指出“終于”一詞包含三層意思: 時間的等待、 頭腦的醞釀和行動的努力,并先讓學生理解這個詞的具體語境:老太太們害怕提起母親會讓史鐵生傷心難過, 但更害怕史鐵生會忘了他的母親, 母親在老太太們心中是揮之不去的永遠惦念, 那棵茂盛的合歡樹便是一路風雨兼程母親的最好見證。顯然,“終于”是要和“提起母親”聯系起來理解,是“老太太們”、“母親”和“我”三者之間關系性復雜心理活動的結果。因此,“終于”和“最終”截然不同,不能隨意調換。還有像“時間”、“悲傷也成享受”、“那棵合歡樹的影子和那個小孩兒” 等,“母親”的那種頑強抗爭生命意識、“合歡樹”所沉淀的偉大母愛和“我”的生命覺醒,成為理解這些語言的具有感染力與引導力的渲染性文本語境, 構成參差多態的互文性。 文本內的人與物、人與人之間,以及基于文本理解的師生之間、生生之間,都存在某種共通和感應。
由上述三種策略所決定, 互文性視角下的閱讀教學內容重構是師生語文經驗參與文本意義建構,進而發生語文經驗互構, 并躍升到文本意義的反思重構,隱含著師生的語文思維和心性變化。文本意義建構、互構和重構本身,都是一種時間性和境域化理解。教師要超越課本知識傳遞的傳統做法,轉而通過關聯性的文字符號文本、 生活經驗文本和生命體驗文本,引發學生的趣味性溝通和創造性轉換,并大力關注和不斷完善學生的話語表達, 從而活化學生的語文思維。如有學者指出,“如果不通過表達展現,我們如何去確證,如何去驗證,又如何知道從哪里著手去修正、補充、完善他們?如果兒童僅僅是充當‘聽話者’的角色,作為被規訓者,作為教育者‘語言講述的對象’,而沒有表達自我感受和意愿的機會與意識,其自我意識、求知欲望如何培養,其進取、探索、開拓品質又如何形成? ”[9]這樣看來,互文性視角下的閱讀教學內容重構,教師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文本意義理解理所當然,但是學生在這一過程中的自我意識、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同樣重要,教師也要注意培植。后者是學習的額外福利,雖然隱蔽,但更為重要。
[1]王榮生.當前閱讀教學的問題在哪里:廣西觀課印象及討論[J].語文學習,2012,(3):12-17.
[2]周流溪.互文與“互文性”[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137-141.
[3]轉引自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947.
[4]王榮生等.語文教學內容重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5]張文喜.自我的建構和解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4-115.
[6]張祥龍.現象學視野中的孔子[J].哲學研究.1999,(6):67-71.
[7][日]佐藤學著.課程與教師[J].鐘啟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123.
[8]陳鐘樑,余映潮.陳鐘樑老師<合歡樹>課堂教學實錄評點[J].語文教學通訊.2012,(2):15-19.
[9]和學新,焦燕靈.試論表達的教育學意義及其實現[J].教育研究.2006,(9):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