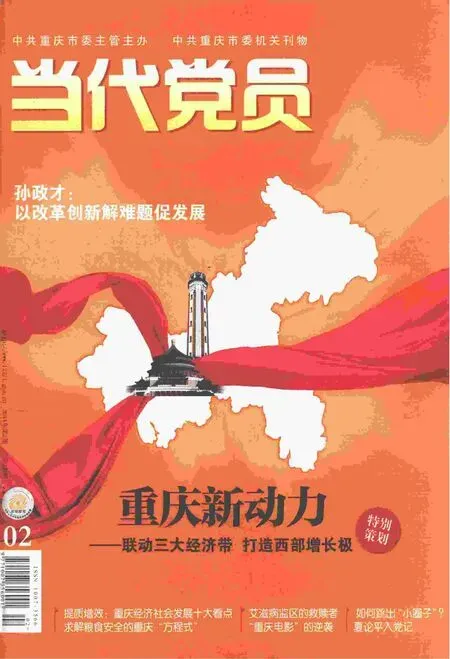渝西川東抱團(tuán)以后
黃海 左進(jìn)
2013年12月,每年的天然氣用氣高峰按期來(lái)臨。
以前這個(gè)時(shí)候,榮昌縣玻陶企業(yè)早就放假了——由于天然氣氣源受四川控制,榮昌企業(yè)不得不因“氣短”而停產(chǎn)。
然而2013年12月,榮昌縣工業(yè)園區(qū)內(nèi)玻陶企業(yè)的生產(chǎn)車間,卻爐火正旺。
“企業(yè)還能正常生產(chǎn),得益于渝西川東八區(qū)縣實(shí)現(xiàn)了結(jié)盟發(fā)展。”榮昌縣經(jīng)信委副主任蔣成龍說(shuō)。
行政壁壘
重慶直轄后,榮昌縣吳家鎮(zhèn)燕子壩村和四川省內(nèi)江市東興區(qū)石子鎮(zhèn)旱地壩村,雖近在咫尺,但公路卻一直未能貫通。
“川渝兄弟分家,造成渝西川東八區(qū)縣間留下大量‘?dāng)囝^路,僅榮昌到川東各區(qū)縣的‘?dāng)囝^路就有27條。”榮昌縣交委副主任翁壽剛說(shuō)。
區(qū)域壁壘,讓渝西川東八區(qū)縣飽嘗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之苦。
“通關(guān)難,難通關(guān),通關(guān)如闖鬼門(mén)關(guān)。”榮昌縣養(yǎng)豬大戶唐澤乾說(shuō),“這是前幾年流行在農(nóng)副產(chǎn)品販運(yùn)戶中的一句順口溜。”
以前,川渝之間生豬等鮮活農(nóng)副產(chǎn)品運(yùn)輸,經(jīng)過(guò)動(dòng)物檢疫站時(shí)手續(xù)十分繁雜。“如果手續(xù)稍有問(wèn)題,哪怕千里迢迢,販運(yùn)戶都得返回本縣補(bǔ)辦,太浪費(fèi)時(shí)間了。”唐澤乾說(shuō)。
榮昌每年有100萬(wàn)頭仔豬和其他鮮活農(nóng)副產(chǎn)品銷售到四川,而川東區(qū)縣每年也有100萬(wàn)頭肥豬以及其他農(nóng)副產(chǎn)品運(yùn)往重慶。
“榮昌的仔豬雖便宜,但拉不過(guò)來(lái),四川這邊肥豬價(jià)格雖低,又拉不過(guò)去。”四川省隆昌縣金鵝鎮(zhèn)方?jīng)_村村民劉定權(quán)說(shuō)。
政府間缺少協(xié)作,資源難以共享,優(yōu)勢(shì)不能互補(bǔ)——行政壁壘,讓渝西川東相鄰區(qū)縣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受到極大制約。
合作破冰
“區(qū)域之間既是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更是合作關(guān)系,合作必共贏,互斗則都虧。”榮昌縣決策層產(chǎn)生了“結(jié)盟”的想法。
于是,榮昌縣向周邊區(qū)縣發(fā)出倡議:“渝西川東八區(qū)縣山水相連、緊密相依,榮則共榮,損則共損,我們現(xiàn)在需要的是‘聚變,而不是‘裂變。”
出乎意料,榮昌縣決策層的想法與渝西川東其他區(qū)縣決策層的思路竟不謀而合。
有共識(shí)就好辦,剩下的工作就是“搭橋”。
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榮昌縣領(lǐng)導(dǎo)分赴渝西川東相鄰區(qū)縣,就合作事宜展開(kāi)磋商。
2007年12月7日,這一天,將寫(xiě)入川渝合作發(fā)展史——渝西川東八區(qū)縣經(jīng)濟(jì)協(xié)作研討會(huì)在榮昌舉行。
經(jīng)過(guò)熱烈討論,重慶的榮昌、雙橋、大足(2011年,市政府撤銷雙橋區(qū)和大足縣,設(shè)立大足區(qū)和雙橋經(jīng)開(kāi)區(qū))、潼南和四川的瀘縣、隆昌、安岳、內(nèi)江市東興區(qū)等八區(qū)縣,共同發(fā)表“榮昌共識(shí)”,簽訂“1+10”合作協(xié)議。
“協(xié)議包括1個(gè)框架協(xié)議和10個(gè)分類協(xié)議,涉及醫(yī)療衛(wèi)生、環(huán)境保護(hù)、警務(wù)聯(lián)勤、檢察工作、法院司法、旅游、林業(yè)、交通、畜牧等10個(gè)領(lǐng)域的合作。”翁壽剛說(shuō)。
這份協(xié)議,拉開(kāi)了川渝兩省市共同打造合作示范區(qū)的帷幕。
打破藩籬
“這條‘?dāng)囝^路都斷了20年了。”榮昌縣吳家鎮(zhèn)與四川安岳縣努力鄉(xiāng)近在咫尺,但因一段2.7公里長(zhǎng)的斷頭路沒(méi)通,村民只能隔村相望。
2008年11月,也就是在渝西川東八區(qū)縣展開(kāi)合作的第二年,情況終于有了變化。
“盼了20年不曾連通的路,現(xiàn)在終于連通了。”吳家鎮(zhèn)村民張成學(xué)感慨。
“吳努路是渝西川東八區(qū)縣打破行政區(qū)劃壁壘、結(jié)盟發(fā)展取得的第一個(gè)成果。”翁壽剛說(shuō)。
第一次會(huì)議之后,為讓協(xié)議從紙上走進(jìn)現(xiàn)實(shí),在隨后六年時(shí)間里,渝西川東八區(qū)縣又召開(kāi)了五次研討會(huì)。
建立聯(lián)席會(huì)議制度,討論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協(xié)作的重大事宜;建立秘書(shū)長(zhǎng)協(xié)調(diào)制度,編制協(xié)作規(guī)劃,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規(guī)劃的實(shí)施;建立部門(mén)銜接落實(shí)制度,落實(shí)框架協(xié)議、專題合作協(xié)議和項(xiàng)目合作協(xié)議約定的事宜……在一步步推進(jìn)中,“1+10”藍(lán)圖一步步變成現(xiàn)實(shí)。
2007年12月,渝西川東八區(qū)縣決策層在第一次研討會(huì)上承諾:五年內(nèi),打通所有“斷頭路”。
“現(xiàn)在,榮昌與周邊區(qū)縣的27條‘?dāng)囝^路已經(jīng)全部連通。”翁壽剛說(shuō)。
“兄弟”共贏
“大足臥佛,身在大足,腳在安岳。”這是2008年重慶大足與四川安岳共同推出的廣告宣傳語(yǔ)。
大足石刻人氣雖旺,但點(diǎn)少面小;安岳石刻雖然點(diǎn)多面廣,但缺乏人氣。“兩地石刻,具有極強(qiáng)的互通性和互補(bǔ)性,但2008年以前,兩地宣傳都是各自為陣,無(wú)法形成合力。”重慶市旅游局副局長(zhǎng)秦定波說(shuō)。
簽訂“1+10”合作協(xié)議后,大足與安岳便采取“客源共享、共同推介、共建線路”的合作方式,聯(lián)合推出了唐宋石刻國(guó)際精品旅游線路。
共建共推,使兩地互相成為游客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市場(chǎng)。“五年內(nèi),兩地互送客源就超過(guò)30萬(wàn)人次。”秦定波說(shuō)。
合作帶來(lái)的不僅僅是門(mén)票收入,還有酒店、餐飲、紀(jì)念品等消費(fèi)收入。
“與大足旅游合作,僅2008年,安岳一年多掙6000萬(wàn)元,大足掙得更多。”安岳縣委書(shū)記鐘毅說(shuō)。
自2007年結(jié)盟后,像旅游這樣的共贏正四面開(kāi)花。
從四川隆昌發(fā)往榮昌等重慶地區(qū)的蔬菜每天有30車左右,綠色通道一開(kāi)通,每天可節(jié)約過(guò)路費(fèi)近兩萬(wàn)元。
隆昌有全國(guó)獸藥業(yè)唯一中國(guó)馳名商標(biāo)“維爾康”,榮昌有西南大學(xué)畜牧獸醫(yī)學(xué)院,兩縣聯(lián)手共創(chuàng)區(qū)域品牌,打造出國(guó)內(nèi)最大的獸藥品牌集群……
八區(qū)縣“結(jié)盟”,打造出一塊區(qū)域合作發(fā)展的“樣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