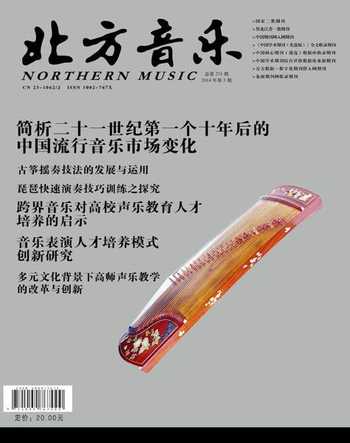論《火把節的歡樂》的藝術特征
魏俊曉
[摘要]《火把節的歡樂》是“中國花腔藝術的開拓者”——尚德義先生在聲樂創作領域的一次成功探索,他堅持走民族化的創作道路,同時大膽地借鑒國外花腔藝術之特色,將中西技法巧妙地融為一體,創作了大量優秀的花腔聲樂作品。文章從作品藝術特征方面進行深度的剖析,以期達到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作品的內涵。
[關鍵詞]火把節的歡樂;藝術特征;花腔藝術
一、作品的基本特征
“火把節的火把,像那鮮紅的山茶,開在彝家山寨里,開在月光下……”聽,這歡快明亮的音調、輕盈調皮的節奏,唱出了我們能歌善舞、熱情好客的彝家人民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歡樂心情。
從歌詞題材上看,歌曲感情真摯,具有濃厚的民族氣息。歌曲的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從我國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出發,深入領悟民族文化的精髓,以獨特的視角去挖掘我們民族的民俗的文化內涵,立足生活、謳歌生活,將貼近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揭示得淋漓盡致,充分體現出文學與音樂的高度統一。同時,他也很好地抓住彝族語言的本質,更加貼近生活的旋律,給人們帶來了美好而又高雅的藝術享受。
從歌曲的旋律上看,這是一首別具特色的花腔女高音歌曲。在過去,對于花腔這樣高雅的藝術,中國聽眾的欣賞能力有限,使得這種藝術手法不能很好地在中國流傳發展。但作曲家改變了這種現狀,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立足于我國的少數民族音樂,從我們民族的音樂元素出發,在此基礎上加入了西方的花腔技法,使歌曲具有西洋特色的同時又擁有民族音樂的旋律。這些都是《火把節的歡樂》這首作品最基本的一些特征特色,我想,一首作品的魅力絕不單單只有這些。作品在華麗外表下掩蓋真正的內涵美,還需要我們進行更深的剖析和挖掘,這才真正是這首歌曲之所以具有強大藝術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作品的審美價值
(一)題材美,歌詞美
在歌詞的創作上,詞作家盧云生所根植的是民族的民俗的音樂文化,“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繁榮昌盛,那歌曲賴以存在的根基就不會動搖,歌曲的生命力將長盛不衰。”他對我們民族的深厚情感也許在作品中是宣泄得最為淋漓盡致的。朗朗上口的歌詞,清晰明亮的旋律,使得這首歌曲具有很強的可聽性、可唱性;口頭化了的語言詞藻,源于生活的好題材,又使得作品與大眾關系更為密切,為大家所喜聞樂見。
歌曲仿佛是一幅彝族人民歡慶佳節的風情畫,一幅幅生動的民俗畫卷展現在我們眼前:姑娘在火把下跳舞,彩裙翩翩如鮮花;小伙在火把下彈琴,琴弦說出知心話;老人在火把下喝酒,豐收歲月添佳話;兒童在火把下游戲,手捧年糕騎竹馬……歌曲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形象生動地將彝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展現在我們面前。這首歌曲是創作者在與我們交流,是生活真實而生動的反映,流露出真摯的思想感情,“正如俄羅斯的作曲家格林卡先生說到的:‘創作音樂的是人民,而我們作曲家只不過是把它編成曲子而已。”一切美好來源于生活,這是歌曲的境界。
《火把節的歡樂》不僅是一部優秀的花腔女高音作品,同時也是一件極好地宣揚我們國家民族文化的佳作,“它將紅土地上一個民族的盛大節日——火把節,持久地烙進了人們的腦海深處,震撼人們的心靈。”就像我國著名女歌唱家王瑩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個人演唱會上,精彩地奉上《七月的草原》《火把節的歡樂》等經典的民族的花腔歌曲之后博得世界人們的熱烈喝彩。
(二)旋律美,內涵美
《火把節的歡樂》是一首色彩絢麗的花腔女高音作品,大量花腔技法的運用使得歌曲旋律更加豐滿,歌聲的表現更為靈動,為歌者提供了更大的發揮空間。“花腔本是美聲唱法中的一種裝飾性很強的演唱技巧,演唱的難度頗高,帶有器樂化的特點。”上世紀60年代以前花腔藝術在中國并不普及,之后,是尚德義的一首《千年鐵樹開了花》,使國人廣泛地領略到了花腔這種藝術獨特的魅力。尚先生從各種角度進行創作,大大地豐富了歌曲的題材,其中,以民族的作品最多,《火把節的歡樂》就是其中的一首經典之作。
有句話說得好:“再好的聲音素質,沒有好的作品也難以表現其魅力。”是啊,這些優秀的花腔歌曲,用上民、美相結合的唱法,為歌唱家發揮嗓音創造了條件,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的作品。在這些方面看來,尚先生的肩上擔負的不再僅僅是一名作曲家,而更多的是一種民族氣節,國家之重任。他也非常欣賞舒曼關于“歌是旋律的寶庫,民族性格的化身”這一論點,于是潛心研究,走出了一條“中國化”的花腔歌曲的發展道路,對我們后世影響也是非常大的。這樣,就又成就出了新的一批花腔歌曲的經典之作,成為我們后人繼承和發揚的典范。8(4+4)小節組成,在降E宮調式上展開,這兩個樂句描寫出了火把節的盛況。B樂段是對A樂段的進一步延續,是對前面盛況的歌唱和贊美,調性保持穩定,音樂情感發展要更為熱烈,呈上升態勢。整個首部有唱有和,比較完整。
歌曲在4小節連接句(23-26小節)之后進入作品的中部。
中部(27-50小節)為起、承、轉、合式的開放樂段結構,從連接開始轉調,由降E宮調式轉到B宮調式,同宮系統的B宮和升G羽調式的相互交替著使用,調性色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緊接著進入全曲的第一個小高潮,擴充句中華彩的花腔部分,之后,穩定地結束在升G羽調性上。”中部的旋律悠揚而舒展,與首部的歡快形成對比,這種抒情性的音樂特點能夠更好地勾畫出彝家山寨人們喜得豐收后的溫馨畫面。
接下來,歌曲又經過一個連接(51-56小節)進入再現部。
再現部(7-22小節)為首部的完全再現,從而首尾相呼應,使旋律的主題更加鮮明。
最后是結束部(57-68小節),這一部分12個小節構成的花腔華彩結束段對整首歌曲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塑造出一種輝煌宏大的氣勢。這些無詞部分并不是在炫耀技巧,而是在對原有詞義的拓寬和深化以及對歌詞未盡之意的補充。從作品的整體上看,結尾具有一氣呵成之感,揭示出了歌曲更深層次的審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