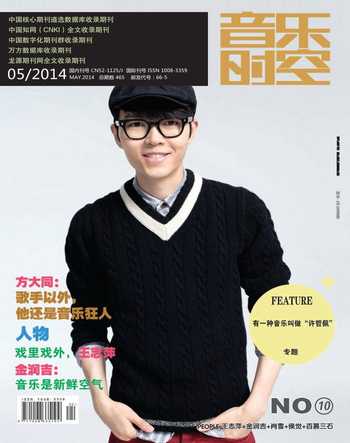論安徽民歌“慢趕牛”的區域性風格
陳璐
摘要:“慢趕牛”是安徽大別山地區的一種山歌曲目,原為大別山地區農民驅趕牛群時即興哼唱的曲調,也有稱為“慢趕羊”、“趕羊兒”等。因方言、習慣等因素的差異,安徽“慢趕牛”分為以淮南為中心的北路、以金寨縣為中心的中路和以安慶為中心的南路三個流行區。本文對比三路“慢趕牛”的音樂特征和風格,從分析“慢趕牛”曲調不同的性格色彩中領略中國民族音樂的風格和魅力。
關鍵詞:慢趕牛 區域性 風格 大別山
一、歌詞韻轍的區域性風格
漢字共有十三個韻轍,如發花韻、梭波韻、乜斜韻、一七韻、灰堆韻、懷來韻、姑蘇韻等。北路“慢趕牛”的歌詞以淮南為中心的北路“慢趕牛”常用懷來韻押韻,如阜陽潁上縣的“慢趕牛”《梔子花開六瓣子開》,其歌詞如下:
梔子小花(唻小)六瓣子開(吔),三瓣子正(唻呀小)三瓣子歪(呀),
你要歪(唻小)就歪倒(唻),你要正(唻呀)就正起來,
你哵正正又歪歪,你叫(那)情郎(呀)俺不敢來(呀)。
這首歌詞共六句,每句都以“唻”“小”“呀”等語氣詞作稱字擴充樂句結構。從歌詞本體的韻腳上看,除第三句轉到搖條韻,其余句末都落在懷來韻上,這種結構符合中國傳統曲體結構——起承轉合。加入稱字后,每句句末分別落在乜斜韻、發花韻、懷來韻、懷來韻、懷來韻和發花韻,稱字的加入結合語音語調的表現強化了歌曲的表現力,加強了這首歌曲情感的表達。
淮南有一首“慢趕牛”是以江陽韻為主韻腳押韻,稱字中的“來”“哎”體現了北方方言的特征。歌詞如下:
我送郎送至(在)五里崗,我送我的小郎子一對對(就)炮(來)仗,
你(哎)走的(哎)(小)一里你放上一個子(哎),你走的(就)二里你放一雙,
我看不著親人(喲)(我的哥子),能聽的炮仗響(來)。
這首歌詞本體的韻腳共有四個江陽韻、一個一七韻、一個人辰韻,雖說這首“慢趕牛”是以江陽韻為主韻轍,但其中懷來韻以稱字的方式銜接全曲,凸顯北方方言的韻味。淮南比潁上更偏北方,歌詞正文有四句押響亮的江陽韻,表現出了北方粗獷的性情,而懷來韻的使用又體現出北方粗中有細的性格。
中路慢趕牛以金寨縣的“慢趕牛”為代表,如《唱歌的可是凡間人》,其歌詞如下:
郎在(呀)高山(來)唱一聲(啰),順風(你就)刮倒(啊)紫(啊)禁(啰)城(唻),
萬歲爺聽見(了)下了位(呀),娘娘(啊)聽見(了)動了心(唻),
唱歌(你小)可(啊)是(啊)凡間(啰)人(唻)。
這首歌詞本體的句末落在江陽韻、中東韻、灰堆韻、人辰韻和人辰韻。這五句歌詞的押韻方式是首尾押中句轉,雖說首尾韻不同,但都有“n”音,相差并不是很大,稱字大多是以“呀”“來”“啰”為代表的發花韻、懷來韻和梭波韻。這些韻轍的結合運用使這首“慢趕牛”兼有北方和中部民歌的特征。
南路“慢趕牛”則是以安慶為傳播中心,具有南方細膩婉轉的風格,運用一七韻和灰堆韻等細膩柔和的韻轍較多。安慶市的“慢趕牛”有很多被稱為“喝羊兒”“慢趕羊”等,如“喝羊兒”《田寬路窄怎讓開》。這是一首多段體歌詞,每段歌詞并沒有統一的韻轍,其整體布局為:押同一韻→不押韻→首尾押韻→押同一韻的漸進式從穩定到不穩定的進行,從而表現出故事情節中男女主角內心曾掀起的波動。
二、音樂旋律的區域性風格
民歌的旋律大多是即興創作而成的,當曲調流傳到某一區域,逐漸形成了該地區特有的旋律結構。“慢趕牛”在其流傳中途徑不同的區域,也就產生了不同風格的“慢趕牛”。
(一)調式調性的區域性特征
安徽大別山區的“慢趕牛”多為徵調式和羽調式,但流傳區域的曲調風格不同,三路“慢趕牛”也有其相應的調性色彩。
淮南的一首《慢趕牛》(譜例1)是北路“慢趕牛”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歌曲。全曲以sol為尾音的E徵調式,其旋律的骨干音為sol、do、re、mi,其各句末尾音分別落于do、sol、sol、do、sol,這種五度的調性框架構建了調式的穩定性。這首《慢趕牛》并非運用了傳統的五聲民族調式,歌曲最后兩句出現了偏音變宮,變宮的出現意味著調性從E徵五聲調式轉入E徵加變宮的六聲民族調式。淮南的《慢趕牛》深受淮劇的影響,樂句中出現re-#do-re的半音輔助進行是西路淮劇典型的特征腔,而sol、do、re、mi的骨干音結構則是東路淮劇的骨干音。
金寨地區的“慢趕牛”曲調較為豐富,大多都是五聲民族羽調式,但也有加入了偏音,如《打一把苦菜當晚飯》(譜例2)。全曲旋律骨干的調式調性是C羽五聲民族調式,但其中三處增加了偏音變徵作為兩個徵音之間的輔助音,這種增加變徵的旋律調式被稱為加變徵的民族六聲羽調式。
安慶是戲曲之鄉,其“慢趕牛”的曲調更具南方的優雅、細膩和抒情。安慶有一首B羽民族五聲調式的“慢趕牛”頗具代表性。前兩大句都以do-la-sol在屬音落尾,調性明亮、寬廣,仿佛在向遠處呼喚,最后一句用稱字的方式將調式調性從徵調式轉到羽調式。最后一句的骨干音為la-do-sol-la, 尾聲僅用羽音收攏全曲,這首“慢趕牛”的風格大氣中蘊藏著柔情,將粗獷的山歌與細膩的小調結合地恰到好處。南路的“慢趕牛”不僅有小調的優美流暢,同時也有山歌蕩氣回腸的大氣之風。這與北路“慢趕牛”的干凈利落在調性色彩上具有很大的差別。
(二)旋律因素的區域性特征
旋律,是民歌獨具魅力的主題。各個地域語言環境的不同,相之對比而言,旋律的各個要素也大相徑庭。
1.音程與音列的區域性
以淮南為中心的北路“慢趕牛”一字一音的曲調較多,如淮南的《慢趕牛》:首句的骨干音為mi、re、do,尾音用低音la為倚音稍稍撥動旋律;第二句則以re-do-la-sol的音階落在徵音。第三句的骨干音為la、do、sol,色彩由明亮漸漸微弱,最后加入變宮在屬音落尾。這首“慢趕牛”的二度進行較多,如re-do-re、sol-la-sol等。而潁上縣的《梔子小花六瓣開》幾乎都是mi-sol-mi、la-do-la的小三度進行。因而,北路“慢趕牛”的旋律采用近腔音列、窄腔音列和小腔音列較多,曲風較細膩柔和。
以金寨為中心的中路“慢趕牛”較北路“慢趕牛”而言,稍添置了裝飾性的元素。la-do-mi的小腔音列是中路“慢趕牛”主要的音列構成,但其中也不缺乏如mi-la、do-sol等四、五度的大跳。在《打一把苦菜當晚飯》中出現了do-高音do的八度大跳,以及sol-↑fa-sol的近二度半音結構。因而,中路“慢趕牛”是以小腔音列為主,寬腔音列、中近腔音列等音列為輔,具有濃郁的山歌風格。
以安慶為中心的南路“慢趕牛”是“慢趕牛”曲調中裝飾最復雜的旋律。安慶的《慢趕牛》與石臺縣的《山歌本是古人留》的旋律差別不大,都是以sol-do-re的四二度結構將旋律揚起,隨后以do-la-sol將旋律緩緩平落,整首民歌的旋律骨干為sol-do-re-do-la-sol,旋律線條起伏有秩,具有抑揚頓挫的美感。南路的“慢趕牛”以寬腔音列和窄腔音列為主,大方婉約。安慶市另一首“喝羊兒”《田寬路窄怎讓開》則是將以大腔音列do-mi-sol和小腔音列la-do-mi并用,沒有多余的裝飾性音列,具有簡單、樸實的性格。
2.節奏節拍的區域性
“慢趕牛”的節拍幾乎都是2/4或4/4的方整性結構,各區域的“慢趕牛”在節奏節拍上又略有不同。
北路“慢趕牛”幾乎都是八分音符、四分音符等規整性節奏型較多,少有切分節奏型、反附點、復附點等節奏型的插入,結構規整,節奏型較單一。但也有一些節奏較為特色的“慢趕牛”,如潁上縣《梔子小花六瓣子開》(譜例4)。這首“慢趕牛”是3/4拍與2/4拍交替進行,節奏較為自由,起句前十六、大切分接后十六、大反附點的結構打破了規整統一的方整性結構。2/4拍的稱字滑音落尾,隨后2/4拍與3/4拍的交替進行,雖從節拍上打破了民歌節拍的統一性,但長音落尾的腔句在聽覺上給人以回味無窮的綿延之感。
中路的“慢趕牛”較于北路“慢趕牛”而言,節奏雖規整但富裕裝飾性,如金寨縣的《唱歌的可是凡人》。這首“慢趕牛”歌詞的本體部分幾乎是一字對一音,除了各腔句的尾字運用了連音線節奏型的拖腔,增添了歌詞的韻味。稱字的節奏較為自由,如三連音、附點音符等節奏型的運用為這首“慢趕牛”加入了旋律的多樣性。
南路“慢趕牛”最大的特點在于節奏寬廣、氣息悠長,但又不缺乏小調的流暢。石臺縣《山歌本是古人留》是4/4拍,起句旋律從八分音符、四分音符到二分音符的漸進性發展將旋律線條逐漸拉長,最后用全音符停留在主音。整首民歌
頻繁地運用倚音、滑音、附點音符、三連音等節奏型裝飾,節奏類型豐富不單一,頗具小調風格。
三、音樂結構的區域性風格
民歌的音樂結構與歌詞所表達的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在北路“慢趕牛”中,淮南的《慢趕牛》和潁上縣的《梔子小花六瓣子開》這兩首“慢趕牛”都是六句體的腔段。《慢趕牛》各個腔句的小節數分別是4、5、7、4、4、4,而相對應的歌詞本體的字數分別為8、12、11、9、6、6,從這兩組數據中可以看出,這首慢趕牛的腔句先擴大后縮減;從旋律上看,第三個腔句以小腔音列la-do-mi起音,這與其他腔句的mi-do大腔音列成對比,最后一句的so-la-sol正是將其它腔句的尾音so-la擴大化,因而這是中國傳統音樂結構中常用的啟承傳合的結構。這首《慢趕牛》應屬于重復引申式的六句體的腔段結構。
《梔子小花六瓣開》雖與《慢趕牛》同屬六句體的腔段,但從腔句的旋律材料上看,應屬于自由引申式的六句體,其各個腔句的小節數分別為2、3、2、2、2、3。這首“慢趕牛”的結構較短,但其結構與淮南的《慢趕牛》頗為相似,其通過節拍的交替統一腔句的整體結構。
金寨地區的“慢趕牛”是中路“慢趕牛”最具代表的曲種,音樂結構也多種多樣。金寨的《慢趕牛》是五句體結構,其各腔句的小節數分別為4、7、4、7、7。從旋律材料上看,起句起于re-do-la落于do-la,第二句則從la-do起又回落與do-la,第三句重復la音起,落于re-do-la,第四句從la-do起落于re-do-la,第五句則從la-do起,以re-do-la首尾。這首“慢趕牛”前三個腔句運用的是延展式的發展方式,前一句的尾音是后一句的起音,這種延展方式被稱為“魚咬尾”,最后一句則是通過變化重復第四句而來。總之,金寨的《慢趕牛》是屬于延展式的五句體的腔段結構
而金寨的另一首“慢趕牛”《眼望乖姐靠門庭》則一共有八個腔句,其各個腔句的小節數分別為4、7、6、4、4、2、4、7。這首“慢趕牛”結構上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中部“搶句子”的部分,從八分音符與四分音符到四個八分音符的節奏型,營造出一種緊張、活躍的氣氛,同時歌詞以“賽什么”為詞組的語言疊加,這種結構被稱為“加垛式”。
南路“慢趕牛”的歌詞字數并不多,多以旋律曲調或稱字拉長腔句的結構。安慶的《慢趕牛》是六句體的腔句結構,歌詞是兩段的多段體結構,其各個腔句的本體都為四個腔節,末句加入一小節的尾音。這首《慢趕牛》結構規整統一,最后兩句則是第三、四腔句的完全重復,各腔句的發展中也運用了接龍式的發展手法。安慶的另一首“慢趕牛”《山歌本是古人留》也是六句體,歌詞的字數以七字居多,但大量稱字、裝飾音的運用使旋律寬廣悠長,賦予流動性。從整體而言,南路“慢趕牛”的歌詞是以五言句或七言句為主,而稱字和裝飾音的運用則對于音樂結構的擴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結語
“慢趕牛”音域不寬,但音區較高,一般以五聲羽調式和五聲徵調式為主,中路金寨地區的“慢趕牛”常用加偏音的六聲民族調式。北路“慢趕牛”使用近腔音列、窄腔音列和小腔音列較多,中路地區偏中近腔和寬腔音列,而南路地區則將山歌與小調風格相結合,使旋律柔美又大氣。雖然各個地域的音樂風格略有差異,但仍能體現出中國傳統音樂體系的藝術魅力,而這種藝術風格也將隨著民間音樂的傳播開枝散葉,呈現出越來越多不同風格的民間音樂藝術。
參考文獻:
[1]崔林.安徽民歌200首[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2009.
[2]喬建中.經典民歌鑒賞指南(上)[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