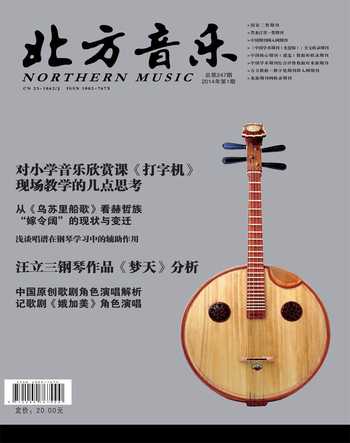民樂的繼承和發展
李明
摘要:什么是民族音樂的繼承發揚?怎樣創新發展?又如何在創新的同時,依舊能夠保持民族音樂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的特點?曹喜俠女士在采訪中對以上問題一一進行了解答。
關鍵詞:民族音樂;繼承;創新;發展
中國民族器樂的演變與發展至今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中西文化全面接觸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社會文化與個人價值觀的急劇變化。普通大眾當中已經很少有人肯靜下心來去仔細體味蘊含在傳統民樂、高雅音樂和嚴肅音樂中的意蘊了。近幾年,繼承和發揚民族音樂成為一個目標,時刻激勵著每一位“民樂人”前進的腳步。記者就民樂的繼承和發展問題采訪了著名青年琵琶演奏家曹喜俠。
記者:民族音樂的繼承和發揚創新發展一直是圈內討論的焦點——什么是繼承?
曹喜俠:20世紀中國民族器樂跨入了由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期。從19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工業文明傳到中國,受到沖擊的不僅是脆弱的經濟壁壘。當關閉已久的國門終于被打開時,人們忽然發現,我們對世界音樂幾乎一無所知。隨即而來的是對新潮音樂的盲目崇拜,是試圖跨越中國音樂與世界音樂的時間差,達到與其同步發展的夢想。幾乎與此同時,民族音樂卻走進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怎樣才能使民族音樂走出“低谷”,古老的傳統如何才能叩響現代之門,步入時代的門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音樂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它不僅可以連接歷史,更可以連接現在和未來。在歷史長河中,要求樂器制作者用一件器物去承載文化的精髓。每一件樂器不僅代表著單一的聲音,它必須代表著一種文化。有此概念,民族樂器的市場越大越好。每一件樂器就像是民族音樂文化的種子,通過樂器本身完成文化的傳承。無論是制作者、演奏者,亦或是評論者,都要具備這樣的歷史與文化責任感。
記者:那什么是創新呢?
曹喜俠:剛才說繼承,中國教育體系,或者音樂教育體系繼承上做的很好,拂曉就開始《十面埋伏》,小學埋伏,大學埋伏,到教授繼續埋伏,集成不難,包括二胡一路《賽馬》,從八歲賽到八十。但是創新特別當下民族音樂你拿下一個什么新的聲音影響當代青年人,這個難度特別大。而且實現起來也很不容易。中國傳統民樂具有悠久的歷史,它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傳承,致使其流派紛呈,品種繁多,風格各異,情感豐富,充滿了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獨特的個性魅力。20世紀80年代以后,傳統民樂的傳承和發展并不順利,這期間,古今的碰撞、中外的對峙、雅俗的抗衡都匯集到一起,一時間,民樂境況低迷,前景令人擔憂。2001年10月,“女子十二樂坊”在京隆重推出,時尚流行因素的大膽借鑒,使廣大聽眾的耳目為之一新,眾多媒體異口同聲地將其稱之為“新民樂”。“女子十二樂坊”的“新民樂”形式,給人們的視覺帶來了強烈的沖擊,融入了一份新奇和滿足,隨后與之相似的各種“樂坊”組合,迅速在各地接踵出現。十二樂坊拉開這個陣勢,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為她整個音樂感覺是當下青年人的,你拉下一個人自己在那兒埋伏,青年人肯定不看,所以要有一種新的視聽理念灌輸到當下媒體和受眾當中去。他們都很支持,也都很響應,用琵琶和小提琴,琵琶和鋼琴,琵琶和京胡,琵琶和打擊樂等等各種方式,但是凸顯琵琶,不是把琵琶淹沒掉,凸顯琵琶的魅力,要借助其他的手段,包括視聽,大家一起來。包括他們的合作,不是一個人單打,而是一個整體陣容,這種方式我們想一直試一下,就是集團作戰,不要一個人單打獨斗。
記者:您認為應該怎樣創新?又如何在創新的同時,依舊能夠保持民族音樂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的特點?
曹喜俠:民族音樂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成績斐然。香港中樂團從1979年至今,創作民樂作品總量已超過2000部,新加坡華樂團創作大型合奏音樂,以及二胡、琵琶獨奏藝術作品的總量預計達到3000部。從專業院校再到業余學習民族器樂的兒童們,民族樂器學習人群總量近1000萬。但我們不能為這樣的數字感到沾沾自喜,民族音樂發展近百年來,民族音樂最終會留下多少傳世之作,是所有民族音樂人值得思考的問題。從表演藝術層面講,民族音樂邁進步伐是最大的,涌現眾多優秀的民樂演奏家。但出現的問題是重技術,缺乏對文化深層的挖掘,如何去表現民族音樂的魂魄和風度,引人思考。
上世紀80年代后,音樂文化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社會也日漸容納各種各樣的思潮和藝術表現形式。當前,民族樂器演奏家在技巧和表演水平上,獲得大幅度的提高。民族樂器在民間普及面越來越廣泛,這是一個好的現象。當前,急于下定論為時尚早。關于民樂繼承與創新,繼承并不是讓演奏家在固有的框架下,因循守舊。根本問題在于,民樂從業能否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有新的東西出來。但此時的“新”非盲目的創新,不尊重任何規律的創新。如果創新是在嚴肅態度下對待藝術創作,進行音樂創作新的探索,都值得去鼓勵和扶持。而作曲家對傳統音樂文化理解不精不透,這反倒成為音樂創作的瓶頸。繼承不是做表面文章,并非簡單地拿一個元素進行所謂的創新。像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堅持30多年的民間藝術采風,記錄了3萬多手民歌,才創作出影響后世的作品,這才是繼承與創新最經典的案例。如果當代作曲家真有這種精神,那離我們聽到傳世之作的時間也就不遠了。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也預祝您一個月后的演奏會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