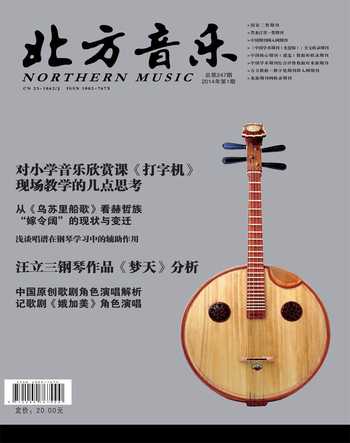史學(xué)研究中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
楊子
摘要:科學(xué)運(yùn)用“多重證據(jù)法”,應(yīng)該是在多學(xué)科知識(shí)鑒定史料的基礎(chǔ)上,靈活運(yùn)用各種材料,借鑒不同的學(xué)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進(jìn)行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對(duì)于中國(guó)音樂史的研究來說,因?yàn)槠湟魳繁倔w丟失的客觀現(xiàn)實(shí),所以不能只重視單一的文獻(xiàn)史料,而是要運(yùn)用多學(xué)科的知識(shí)對(duì)已掌握的資料進(jìn)行鑒別,更重要的是,在鑒別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多種資料相互考證,運(yùn)用多重證據(jù)法,作全面徹底的分析研究,以保證音樂史學(xué)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xué)性,更好地解釋音樂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提升音樂史研究的價(jià)值和意義,促進(jìn)音樂史學(xué)的發(fā)展。
關(guān)鍵詞:科學(xué);史學(xué)研究方法;音樂史;多重證據(jù)法
一、科學(xué)的史學(xué)研究方法之建立
“多重證據(jù)法”作為一種科學(xué)的史學(xué)研究方法,源于王國(guó)維先生在20世紀(jì)初,根據(jù)甲骨文字的釋讀成果而提出的進(jìn)行古史研究所運(yùn)用的“二重證據(jù)法”,即用文獻(xiàn)資料與考古文物相結(jié)合后的方法,來證實(shí)客觀的歷史實(shí)在。
一方面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xué)派“立義必憑證據(jù)”、“孤證不為定說”的考據(jù)學(xué)傳統(tǒng),一方面他積極采用西方近代史學(xué)的研究方法,結(jié)合一系列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對(duì)中國(guó)古代史進(jìn)行考證,開辟了20世紀(jì)歷史考證學(xué)的新道路。
證據(jù)法又分為內(nèi)證、外證、直接證據(jù)、間接證據(jù)。間接證據(jù)是指本身不能直接證明主要事實(shí),而需要同其他證據(jù)結(jié)合起來才能證明事實(shí)的證據(jù)。直接證據(jù),無需經(jīng)過復(fù)雜的推理過程,直接即可證明。“多重證據(jù)法”,顧名思義,就是結(jié)合不同材料、多種證據(jù)對(duì)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考證的方法,而且所搜集、整理的材料和證據(jù)必須是有科學(xué)依據(jù),是要經(jīng)得起驗(yàn)證的材料。
21世紀(jì)以后,隨著大量西方民俗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文化人類學(xué)等相關(guān)著作引入中國(guó),并紛紛建立相應(yīng)的學(xué)科后,一些人類學(xué)家在“二重證據(jù)法”的基礎(chǔ)上派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多重證據(jù)法”,即對(duì)“文獻(xiàn)典籍”、“文物考古”和“文化人類學(xué)”的資料與方法進(jìn)行綜合的運(yùn)用。
二、在音樂史研究中的科學(xué)運(yùn)用
1.材料的收集和運(yùn)用
在中國(guó)音樂史的研究中,“多重證據(jù)法”的應(yīng)用,可以狹義的理解為是用文獻(xiàn)史料、文物以及傳統(tǒng)音樂中“活”的材料,相互支持、印證。
文獻(xiàn)史料包括文本文獻(xiàn)和口述文獻(xiàn),是史學(xué)研究中的基礎(chǔ)和前提,尤其是中古音史學(xué)中雖然樂譜文本留存極少,但文獻(xiàn)史料卻極為豐富。文物,即“有形證據(jù)”,主要包括遺址、出土樂器、畫像、古代樂譜、出土竹簡(jiǎn)等,可以較為直觀、真實(shí)的了解古代音樂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傳統(tǒng)音樂中“活”的材料如西安鼓樂、山西八大套、福建南音等都較好的保存了古代音樂的本體材料,是古代遺留下來的最直觀最重要的資料。
因?yàn)橐魳匪囆g(shù),與美術(shù)不同,它是一門時(shí)間的藝術(shù),它本身具有很強(qiáng)的技術(shù)性,僅憑語言文字并不足以將它完全保存下來。而文物也是靜止的“有形證據(jù)”,它的年代需要借助其他學(xué)科進(jìn)行判斷,即使可以斷定年代,但它是如何奏響哪些美妙旋律,無從而知。對(duì)于現(xiàn)存的“活”材料而言,它蘊(yùn)含著一定的古樂因素,但是在歷史復(fù)雜的演變中,它受朝代的更替、民族遷徙、文化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等多方面影響,對(duì)于其源頭的確立,以及中間的變異程度,也是非常難以攻破的課題。
可以說三者各有優(yōu)勢(shì)也各有不足之處,所以在音樂史學(xué)研究中需要將各種材料相互印證,取長(zhǎng)補(bǔ)短,不能倚重倚輕,要根據(jù)具體情況來確定誰更可信。只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合情合理地、準(zhǔn)確地使用真實(shí)、正確的材料,才能使研究結(jié)論更加符合客觀事實(shí)和內(nèi)在規(guī)律。
2.多學(xué)科的相互依存
從另一個(gè)角度來說,廣義的“多重證據(jù)法”是指不同學(xué)科之間的相互借鑒和參證。音樂史研究應(yīng)當(dāng)打破舊有的單一模式(文獻(xiàn)史料),從多角度來思考研究音樂史的相關(guān)問題,將各種材料,甚至是不同學(xué)科相互融合。
如民族音樂學(xué)的建立,就大大促進(jìn)了音樂史學(xué)的相關(guān)民間音樂材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相關(guān)研究方法的借鑒和引入。民間音樂十大集成工作及各種民間音樂實(shí)地調(diào)查,為古代音樂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活”材料,搶救整理了大量民間傳統(tǒng)音樂資料和珍貴的曲譜文獻(xiàn)音響資料。在田野工作中,還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對(duì)少數(shù)民族音樂資料的收集、研究。70年代學(xué)術(shù)界在對(duì)裕固族民歌進(jìn)行搜集和調(diào)查時(shí),偶然發(fā)現(xiàn)它與匈牙利民歌的曲調(diào)完全相同,經(jīng)查閱裕固族的有關(guān)文獻(xiàn)記載,得知其祖先與匈奴有密切關(guān)系,通過與西方的歷史文獻(xiàn)相互考證,對(duì)匈奴族在公元9世紀(jì),東遷歐洲定居這一史實(shí)進(jìn)行確認(rèn)。進(jìn)而得知二者的曲調(diào)相同的歷史淵源。較好的運(yùn)用比較音樂學(xué)的方法,對(du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音樂文化發(fā)展歷程相互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的共性規(guī)律和個(gè)性特點(diǎn),是對(duì)中音史學(xué)研究的極大幫助。
除此之外,考古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音韻學(xué)、訓(xùn)詁學(xué)、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等學(xué)科,都可以與中音史研究相互融合、滲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3.主觀指導(dǎo)思想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xué)的首要任務(wù)就是了解“實(shí)事”,掌握史實(shí),從事實(shí)出發(fā),進(jìn)而揭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從事實(shí)出發(fā)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離開既有的歷史事實(shí),就不會(huì)有歷史科學(xué)。無論是文化史、哲學(xué)史等,都擺脫不了歷史史料和歷史史實(shí)的研究。
音樂史是一個(gè)綜合性的歷史問題,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不可能脫離其他因素,孤立的進(jìn)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應(yīng)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dǎo)的研究理念,從理性上、從證據(jù)上、從實(shí)踐上審視音樂,不僅重視民間音樂研究、樂律實(shí)驗(yàn)、音樂考古和古譜解疑的實(shí)踐,還要注意與文獻(xiàn)資料的相結(jié)合。要根據(jù)具體情況,靈活運(yùn)用,在慎重考證各種材料的基礎(chǔ)上,盡可能使用多種史料,聯(lián)系多種學(xué)科,進(jìn)行綜合研究,不能脫離實(shí)際的死板硬套。在這方面,音樂史學(xué)大家楊蔭瀏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好的范例,他撰寫《史稿》時(shí),就運(yùn)用唯物史觀,提出音樂是人民的音樂,音樂具有人民性。
三、音樂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
80年代以來,在各學(xué)科相互交融的發(fā)展趨勢(shì)下,音樂學(xué)界對(duì)音樂史的研究方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馮文慈先生最先借鑒歷史學(xué)中的“逆向考察法”,首次提出在音樂史研究中結(jié)合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實(shí)地調(diào)查的研究方法,開辟了傳統(tǒng)古史研究的新視角。隨后一批學(xué)者紛紛響應(yīng),并將這種方法付之于實(shí)踐。
然而,在此之前楊蔭瀏、黃翔鵬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多重證據(jù)法”的說法,但在實(shí)際的研究中,他們已經(jīng)自覺的運(yùn)用到這種科學(xué)的治學(xué)方法。
楊蔭瀏先生深深植根于中國(guó)民間的音樂實(shí)踐,在實(shí)踐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間音樂資料,并將這些資料運(yùn)用到中國(guó)音樂史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在他的影響下,4、50年代,剛成立不久的音研所篇開展了一些列收集、整理民間音樂的實(shí)地調(diào)查活動(dòng),如對(duì)全國(guó)琴譜琴人、民間藝術(shù)家阿炳和劉陽地區(qū)的祭孔音樂的錄音和記譜資料,以及對(duì)新疆、山西、福建等地區(qū)類似的收集整理工作,雖然當(dāng)時(shí)設(shè)備落后,但這一舉動(dòng),為樂律學(xué)、琴學(xué)、古譜學(xué)、民族音樂學(xué)等學(xué)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為“多重”在中國(guó)音樂史研究中的運(yùn)用,做好了準(zhǔn)備工作。此外,在楊生“里程碑式”的著作《史稿》中,努力突破過去音樂史偏重“文學(xué)史”的局限,在材料運(yùn)用上和研究方法上都盡量做到豐富、全面。書中廣泛吸收文獻(xiàn)學(xué)、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音響學(xué)、音韻學(xué)、民族學(xué)及民俗學(xué)各科知識(shí)和相關(guān)研究材料,已經(jīng)開始引用大量考古實(shí)物材料及圖片資料。楊生尤其注意現(xiàn)存?zhèn)鹘y(tǒng)音樂中“活”的音樂資料,對(duì)文獻(xiàn)資料的解讀和考證,如他借鑒西安鼓樂保存的一百余首用俗字譜記載的樂譜和山西五臺(tái)山《八大套》管子譜及北京智化寺音樂的宋代譜式,來解讀和翻譯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旁譜”,成為首位將17首詞調(diào)歌曲完全解譯的學(xué)者,打破了“啞巴音樂史”的詛咒,將絕響已久的宋音重現(xiàn)于世,可以說楊生在中音史的研究工作中已經(jīng)開始運(yùn)用“多重資料”“多重證據(jù)”的方法。
黃翔鵬先生在音樂考古學(xué)、音樂史學(xué)、傳統(tǒng)音樂研究領(lǐng)域均有深厚造詣,在《中國(guó)古代音樂史——分期研究及有關(guān)新材料、新問題》一書中憑借其多重學(xué)科知識(shí)的背景,已經(jīng)成功運(yùn)用了“多重”。他結(jié)合民族學(xué)、文化人類學(xué)角度,證實(shí)了現(xiàn)存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口弦”樂器即是“笙”。他把古代音樂史中“活”的材料作為研究對(duì)象,證明文獻(xiàn)中將“簧”注解為“笙”的不當(dāng)做法,正式“多重”運(yùn)動(dòng)的典范。80年代末,黃先生提出“曲調(diào)考證”法,是對(duì)逆向考察法的發(fā)展和延續(xù),對(duì)傳統(tǒng)樂曲作歷史形態(tài)的考證。他發(fā)現(xiàn)了今樂與古樂之間共同的規(guī)律性的要素——曲調(diào),古樂蘊(yùn)含在今樂之中,強(qiáng)調(diào)“無形文物”同“有形文物”同樣具有歷史文化價(jià)值,對(duì)研究樂律、古譜和音樂史相關(guān)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李純一先生作為一位音樂家,更是率先在遠(yuǎn)古時(shí)期的音樂研究中運(yùn)用考古資料,特別是其著作《中國(guó)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cè)》將先秦時(shí)期的文獻(xiàn)資料、測(cè)音資料、實(shí)物資料、圖片資料集于一體,綜合考古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人類學(xué)等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充分發(fā)揮了音樂考古學(xué)科得優(yōu)越性,并注意到與其它學(xué)科的借鑒融合。大膽采用古代傳說、詩歌和甲骨文的記載來研究夏商兩代的音樂史。并根據(jù)出土樂器的測(cè)音結(jié)果,來研究中國(guó)的音樂形態(tài)。如運(yùn)用民族音樂研究所對(duì)河南輝縣出土的陶塤以及故宮編磬測(cè)音的結(jié)果,對(duì)十二律的形成年代進(jìn)行考證。書中有不少猜測(cè)和想象,但仍不失為研究先秦音樂的重要著作。
近年隨著新史料、新學(xué)科的不斷涌現(xiàn),在史學(xué)研究中也出現(xiàn)了對(duì)這些材料不加鑒別考證,直接全面進(jìn)行運(yùn)用的情況,其結(jié)構(gòu)往往造成錯(cuò)誤性的結(jié)論。如牛龍菲對(duì)于“琵琶”,歷史的研究要講邏輯,證據(jù)與他所要論證的要有邏輯關(guān)系,要有聯(lián)系,必須承認(rèn)科學(xué)的法則。不然就會(huì)產(chǎn)生“多米諾效應(yīng)”,一個(gè)錯(cuò)誤的前提,引發(fā)出一系列的謬論。搜集再多的材料,也是枉費(fèi)工夫。
此外,在史學(xué)研究的過程中,還出現(xiàn)了一些輕視某種研究資料,或者盲目相信某一單一史料的現(xiàn)象。對(duì)于不同學(xué)科的材料,不能相互良性的結(jié)合、參證,更甚者出現(xiàn)相互排斥的現(xiàn)象。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應(yīng)當(dāng)仔細(xì)審視所收集的材料,擇取與所證問題有密切關(guān)系的材料。
科學(xué)運(yùn)用“多重證據(jù)法”,應(yīng)該是在多學(xué)科知識(shí)鑒定史料的基礎(chǔ)上,靈活運(yùn)用各種材料,借鑒不同的學(xué)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進(jìn)行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對(duì)于中國(guó)音樂史的研究來說,因?yàn)槠湟魳繁倔w丟失的客觀現(xiàn)實(shí),所以不能只重視單一的文獻(xiàn)史料,而是要運(yùn)用多學(xué)科的知識(shí)對(duì)已掌握的資料進(jìn)行鑒別,更重要的是,在鑒別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多種資料相互考證,運(yùn)用多重證據(jù)法,作全面徹底的分析研究,以保證音樂史學(xué)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xué)性,更好地解釋音樂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提升音樂史研究的價(jià)值和意義,促進(jìn)音樂史學(xué)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