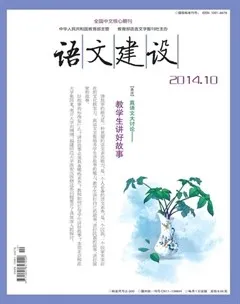以無序的自由聯想揭示思想的不自由
《墻上的斑點》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所寫的一篇小說,被選入人教版選修教材《外國小說欣賞》。要讀懂這樣的小說,關鍵是要抓住它的流派特點。
一
讀者閱讀的初感(直覺)的問題是:這樣的作品能算小說嗎?既沒有連貫的情節,很難說有什么人物性格,更沒有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心理錯位或者矛盾。只是一個不知姓名,沒有形貌,沒有行動,停留在原地的女性,在隨意地、即興地、斷斷續續地內審,毫無頭緒地聯想、回憶。引起這一切的,只是墻上的一個斑點,她一直以為是個釘子,想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六千多字),才發現并不是釘子留下的痕跡,而是一只蝸牛。
這樣隨機、漫長的感受,完全是個人內心無形的、無聲的自白,有些還是“幻影”,幾近于胡思亂想,和一般讀者預期的小說相去甚遠。是不是有點接近散文?似乎也不太像,其自言自語并不抒情,既不美化墻上的斑點,也沒有敘事,它僅僅是浮想聯翩,紛至沓來的感覺并不構成連貫的思緒,其間的聯系只是邊緣性的(近似切線的)相近性。這樣的自由隨想,也許有點像西方人所擅長的隨筆(如《瓦爾登湖》),可隨筆有一定的智性貫穿其間。《墻上的斑點》則談不上任何智性的一貫性。
那么,它為什么叫作小說,而且獲得舉世的共識呢?
這是因為,它具有小說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對于人物外部感知和內心情志的深度探索,表現作者對于人的內心感知和情志的獨特理解。這屬于特殊流派的小說——文學史上所謂意識流小說。
傳統的小說,不管是現實性的還是超現實的,或多或少都有或強或弱的情節,情節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軌,讓人物遭遇意想不到的災難或者幸運,進入非常環境,迫使人物在常軌情況下隱藏在人格面具下的、隱藏在深層的甚至連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情感思緒涌到表層。《項鏈》中那個追求虛榮的女人為了不被當作騙子,艱苦備嘗,付出十年的青春代價,表現出“英雄氣概”,堂堂正正地償還了那條項鏈。《最后一課》中,那個討厭法語的小學生變得無限熱愛法語。故托爾斯泰在《復活》中說:“人往往變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實,他仍舊是原來那個人。”[1]情節把人物打出常軌的另一功能是使相互之間本來親密的或者敵對的人物關系發生變幻、產生錯位、催生矛盾,推動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心理就得到更奇妙、更獨特的展示。《范進中舉》中胡屠戶本來對范進懷著極強的優越感,公然對之辱罵。一旦范進中了舉,就極其自卑,為了給范進治瘋病,打了他一耳光,居然認為得罪了天上的文曲星,遭到懲罰,手痛得彎過來了。這種情節性,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乃至部分超現實主義小說的不二法門,但是伍爾芙顯然對幾百年來的藝術成規發出挑戰:難道這是唯一的,別無選擇的嗎?在《墻上的斑點》中,作者讓人物停留在原本的環境中,沒有外來的干擾,甚至沒有親人、友人、情人,也沒有關系緊張的敵人,更沒有外來的幸運和災難,能不能表現人物感知的獨特,揭示人物深層的心理奧秘呢?
二
藝術的生命就是革新,就是突破,《墻上的斑點》表現了藝術家的大器,對一向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情節進行勇敢的顛覆。作品和打出常軌的情節小說相反,讓人物在常軌之中,沒有事變,甚至沒有動作,人物坐在那里,情思如萬花筒一樣,感知紛至沓來,迷離、紛紜、偶然、無序,如夢如幻。這就顯示了和傳統小說根本的不同,傳統小說以人物的情思的動態為脈絡,而這種小說則是表現人物的靜態。不但環境是寧靜的,而且心理也是寧靜的。這有什么東西可寫呢?她在追求什么呢?伍爾芙曾經這樣敘述自己的追求:“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它們來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計其數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這就是她追求的“真實的生活”。文學作品就應該“按照那些微塵紛紛墜落到人們頭腦中的順序,把它們記錄下來”,“追蹤它們的這種運動模式”。在《墻上的斑點》中伍爾芙這樣宣稱:
我希望能靜靜地、安穩地、從容不迫地思考,沒有誰來打擾,一點也用不著從椅子里站起來,可以輕松地從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覺敵意,也不覺得有阻礙。
這樣安穩地、從容不迫地思考有什么好處呢?這不僅因為,這是她所認為的真實,而且還有一種好處,他們叫作自由聯想:“可以輕松地從這件事想到那件事”,即事件之間是跳躍性的,和傳統小說事件的連貫性分道揚鑣。這樣的革新是大膽的,但是帶來一個嚴峻的問題,情節有時間上的連貫性,有情感邏輯上的因果性,有發展變化,有懸念,有轉折,才能吸引讀者不由自主地注意(在心理學上叫作“無意注意”),放棄時間上的連貫性,情感邏輯上的因果性,展示一片散漫的感知,憑什么讓讀者專注呢?這當然有風險,有難度,最大的難度應該在于感知的“自由聯想”是無序的。
此外,“自由聯想”雖然在時間空間上是自由跳躍了,可自由不是絕對的。第一,所有的感知、回憶、遐想、幻影,總是圍繞著一個焦點:墻上的斑點,斑點既是聯想的起點,也隱約沉浮于聯想的過程,最后結尾則是突然的、簡潔的對轉,那不是釘子的痕跡,而是一只蝸牛。從某種意義上說,斑點作為核心意象既是有序在無序中時隱時現,又在整體中首尾呼應。第二,墻上的斑點引起的紛紜的聯想是隨機的,但是微妙的聯系還是有跡可循的。從墻上的“斑點”,聯系到“爐子里的火”,“黃色的”,壁爐上有“菊花”,壁爐的炭塊是“火紅”的,聯想到了城堡上“鮮紅的旗幟”,從而又帶出了“紅色的騎士”。這完全是“幻覺”,甚至是“無意識”的,但又并不絕對是散漫的:“爐火”“黃色的菊花”“城堡上鮮紅的旗幟”“紅色的騎士”,不但同屬于色彩,而且大體為熱色調,就是這樣的熱色調把紛紜的感知、幻覺統一起來。作品后來從斑點猜想到在更高處可能有粉紅、藍色、“玫瑰花形狀的斑塊”,聯想到莎士比亞,這不是脫離斑點了嗎?但斑點是和爐火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伍爾芙讓莎士比亞坐在椅子上,“凝視著爐火”。絕對的自由聯想的可能本來是無限的,但是在伍爾芙這里,控制著它們只能向邊際相關的方向延伸過渡,即使在時空上有些大幅度的跳躍,馬上又回到核心意象(斑點/爐火)上來。
伍爾芙營造了這樣隱含著有序的背景,就讓人物的“思緒”“一哄而上,簇擁著一件新鮮事物”,傳統小說的情節功能就是讓人物在歷時性的動蕩中展示其內心的新異的動蕩。這里把人物放在共時性、瞬間的寧靜中,人物的情思也在運動,也有新異的變幻。只不過不是通過外部可感的動作、行為、語言,而是通過內心非邏輯的自白。這正是伍爾芙的追求:這才是人的內心的“真實”,在寧靜的狀態下,人的心靈,人的感知,人的回憶,是如此活躍、豐富,有一種“一哄而上”“簇擁新鮮”的感覺。這種既紛紜又新鮮的感覺正是小說對讀者的感染力來源之一。
伍爾芙顯然覺得,傳統小說把人物放在大變動的過程中,有條有理地按著清晰的邏輯去行動或者說話并不“真實”。這樣的想法,有一定的心理學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學原理》中指出,人類的思維活動是一種斬不斷的“流”,不是自覺地、有序地銜接,而是隨機變幻、錯綜交融,因此將之稱為“思想流”“意識流”。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則認為,“意識”存在于“不可分割的波動之中”。[2]這種心理學對于20世紀初的小說家影響甚大,以致在一些小說家中形成一種共識:只有把這樣的無序的意識之流,以內心自白的辦法描述出來,才是真實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文學流派,叫作意識流。很快產生了經典,如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英國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國小說家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
三
伍爾芙固然受到詹姆斯“思想流”“意識流”的影響,但是作為藝術家,她有自己的創造,她并不以為人的思緒僅僅是單線的、平面的、長期的自由聯想,在《墻上的斑點》中,她把意識和感知的流動集中到暫時的、瞬間的感知中來,從意識到潛意識,從現場感知到超越時空的回憶,展示為立體的隱顯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單線的,不是浮于表層的,而是從五官的感知、想象、意識和潛意識向智性的判斷深化的。在《墻上的斑點》中她這樣自白:
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離開表面,離開表面的生硬的個別事實。讓我穩住自己,抓住第一個一瞬即逝的念頭。
不寫事件,回避連貫性,乃是為了“離開表面的生硬的個別事實”。實際上,在她看來情節就是“生硬的”。“生硬”有什么壞處呢?那就是妨礙她“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這就是說,她認為描寫情節(事實)妨礙她深入人物內心深處去。用什么辦法突破事件的“生硬”外殼呢?那就是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說的“抓住第一個一瞬即逝的念頭”,從感知的紛紜中向智性深化,這樣,意識流就不僅僅是感知的流動,而是感知一方面向潛意識,一方面向智性深層流動。
小說向智性深化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從斑點不像是釘子的痕跡深化為觀念:“事件發生后”“沒有人能夠知道它是怎么發生的”,從而引導出偶然性這樣具有哲理意味的觀念:“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準確!人類是多么無知……和我們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帶有多少偶然性啊。”接著是把偶然性循著感性來擴展,從遺失的物品、人被射出地鐵,到紙袋被扔進郵包等,都是偶然的。
思緒深化的第二個層次:時間的流逝,在“綠色莖條”“杯盞形花”等,在此背景上,把偶然性從外延上拓展到人的生命:“為什么人要投生在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會行動、不會說話、無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腳下,在巨人的腳趾間摸索呢?至于什么是樹,什么是男人和女人,人們再五十年也是無法說清楚的。”這個層次時間和空間都有大幅度的跳躍,但還是有著意象的關聯性:“一朵花”的出現,顯然從開頭壁爐上的“三朵菊花”“夏天殘留下來的玫瑰花瓣”過渡來的“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塵土堆里開了一朵花”。因為“花”的意象關聯性,時空跳躍不是很突兀。
在“花”的意象(紫色的花穗)帶動下,思緒進入了第三個層次,從偶然性向真實性過渡。人們總是美化自我:“在頭腦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來”,本能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偷偷地,而不是公開地”美化自己,如果“鏡子”打碎了,浪漫的虛象消失了,“在這樣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意思是說,人總是不能面對“真實”,沒有浪漫的打扮,沒有自我欺騙,人就不能活。由于照鏡子(在公共汽車和地鐵里我們就是在照鏡子)的欺騙性,人們像小說家一樣,把“現實”“排除”,以“追逐”“幻影”為務,接著是把這種感性的“幻影”,拓展社會意識形態:“社論”“內閣大臣”等的套話,被人們認為是“正統”的“必須遵循”的標準,從希臘人、莎士比亞以來就是這樣想的,不然,“就得冒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危險”,但是事實上“毫無價值”。這就是對統一的思想規格進行直接的批判了,傳統套話束縛著人們本來可以自由的、多樣的想法。每一件事都只有一個規矩,連桌布的黃色小格子都一樣,換了一種花樣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
第四個層次,引申出作者女權主義的直截了當的宣告:究竟是什么掩蓋生活中“真實”,“也許是男人……男性的觀點支配著我們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標準”。所謂神圣的“尊卑序列表”,森嚴的固定社會等級:“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約克大主教。每一個人都必須排在某人的后面。”“最要緊的是知道誰該排在誰的后面。”但是,這是僵化的,不自由的,只有它遭到譏笑,被扔進垃圾桶,人們才可能得到“自由感”,盡管這種自由感是“非法的”,然而是作者向往的,認為是非常“奇妙”的。
這樣的思緒的深化,似乎離開斑點太遠了,于是第五個層次,回到斑點上來:以漫畫的筆法抨擊所謂“學者”,他們投身于古墓、白骨的研究,搜尋證據,除了蹲在洞穴里盤問老鼠,記載巫婆和隱士的后代,他們什么也不會。這是對經院哲學,對奉為神圣的“知識”的反諷。正統的“知識”事實上是迂腐的、不自由的、僵化的、迷信的,然而人們卻在崇拜他們。這就是說,一切神圣的學問,其實都迷信,都虛假,都可笑。歸根結底,是不自由的。
第六個層次則是作者正面的理想,那就是思想自由:現有的“知識”都是迷信,顛覆對這些知識的迷信,才能“想象出一個十分可愛的世界……這個世界里沒有教授、沒有專家、沒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這里人們可以像魚兒用鰭翅劃開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劃開世界”。在這里,“沒有尊卑序列表”。在看來紛紜無序的感知、回憶、幻覺、潛意識的流動中,居然升華出了對知識霸權如此尖銳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擺脫遮蔽,爭取思想自由的宣言。
這是多么勇敢,多么深邃,多么徹底。作者說這樣理想的、打破了迷信的世界是“可愛的”,但是,作者顯然意識到這又是多么不現實,只能在“兩百年后”才有可能。“大自然(按:現成的社會秩序)忠告你說,不要為此感到惱怒(按:不要懷疑現成的等級序列),而要從中得到安慰;假如你無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壞這一小時的平靜,那就去想想墻上的斑點吧。”這就是說,去看看墻上的斑點,去自由地聯想,是唯一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是虛幻的,在文章最后,回到墻上的“斑點”上來,發現那并不是想象中的釘子的痕跡,而是一只蝸牛。這最后一筆可謂真正的天才的一筆,既是現實的無奈,也是對自我的調侃,這里有深沉的黑色幽默。
四
伍爾芙對情節的批判:“表面的生硬的個別事實”,包含著兩個意思,第一,情節是“表面”“生硬”,被她用自由聯想瓦解,故能達到思想的深度。還有一點不可忽略,那就是“個別事實”。情節總是個別人的個別事情,而《墻上的斑點》達到的哲學的高度是普遍的,不是個別人的個別事件。把哲理的普遍性作為藝術的追求,不但是意識流小說家的追求,也是整個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追求。
作者在撲朔迷離的浮想之中,居然蘊含著這么深邃的哲學性意義上的自由追求,在意識流小說中堪稱一絕,但從小說藝術的精練性來說,作者的主題是不是太復雜了一點,起初關于“偶然性”的思考,和后來正統的霸權“知識”不自由的批判,是不是有機地統一,是很值得懷疑的。17世紀的斯賓諾莎(1632-1677)提出:自由乃是對于必然性的認識。[3]自由和必然處于對立和有機的統一之中,不管是啟蒙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肯定了這個命題。伍爾芙在這里把自由和偶然聯系在一起,顯然缺乏內在的統一性,也許正是因為這樣,耗費了多達六千余云霧漶漫的文字,對讀者也不無折磨。語言的拖沓和玄虛并不是伍爾芙一個人的缺陷,而是意識流小說家,包括經典小說家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等共同的癥候,因此意識流作為一個流派,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國也一度影響了白先勇、王蒙等作家,他們帶著意識流風格的小說,一度風靡一時,但是作為文學流派是曇花一現,至今只在為數不多的詩歌中顯示其生命力似乎還沒有完全消亡。
參考文獻
[1]列夫·托爾斯泰.復活[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262-263.(汝龍譯文略有不同)
[2]參閱鄭克魯.意識流[M].//袁可嘉等選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二冊(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1.
[3]這是長期以來,對斯氏思想的概括的說法。斯氏的原話是:“凡是僅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為僅僅由它自身決定的東西叫作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為均按一定的方式為他物所決定,便叫作必然或受制。”(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頁)嚴格說來,斯氏的思想更準確的表述是:自由和必然的關系首先不僅僅限于認識,而且還有行動,也就是在實踐的過程中才能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