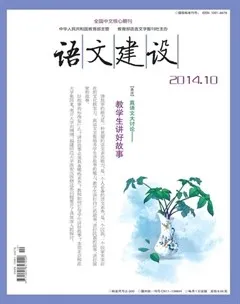問題意識主導下的語文測試探討
我和馮淵老師,因文字而結緣。
近年來,由于工作需要,我對中學語文教學有較多關注,也會看看語文類雜志上的文章,這其中,馮老師回憶他學生時代幾位語文老師的一篇隨筆,給我留下過很深印象。我在大學開設寫作基礎課,在開始“感覺和記憶”的訓練單元時,還把這篇文章作為例文推薦給學生。后來,我發現,他不但寫得一手充滿形象感的記敘類好文章,而且,在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探討語文教學的學理性問題時,也能提出一些益人心智、給人啟發的見解。再后來,我才發現,原來我投給《語文學習》“備課欄目”的文章,都是由他來初審,在我讀他隨筆、讀他教學論文的同時,他,也一直是我文章的讀者,而且讀得認真仔細,能給我提一些修改意見,還不時糾正我文字乃至標點上的一些謬誤。雖然幾年來,我和他的見面,只有寥寥數次,但我們以文字為媒介而展開的對話,卻一直沒有中斷過。古人說“文字緣深于骨肉情”,用于形容我和馮老師的關系,當然太夸張,但這樣的文字交往此刻想起來,還是讓人愉悅的,也是讓人期待的。雖然我的觀點,他未必全部認同,而他的一些分析結論,我有時候也要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這種切磋,不會讓彼此產生隔閡,只是增進了互相理解。我不敢說我的建議對他一定有用,但對我來說,他的每次意見,為我提供了反思自己文章的機會,更何況他主持《語文學習》“備課欄目”那么多年,閱文無數,“觀千劍而后識器”,所以他的意見,我總是特別重視。也許正因為他看得多、見識廣,再加上他當語文教師多年,晚近又擔任教研員,始終活躍在語文教學第一線,從實踐中積累的經驗也比較豐富,這樣,以學識與經驗結合為基礎,他探討起語文教學的諸多問題,就顯得特別游刃有余,寫出的文章,也特別實在。對于他的文章,雖然我時斷時續一直在看,但當他把關于探討語文教學命題的文章收集為一編寄給我并叮囑我寫序時,我始則驚訝,繼則慚愧,終則佩服了。
驚訝的是,想不到近年來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能夠寫出這么多高質量的專題研究文章;慚愧在于,雖然自己也參與過上海地區不同類別的語文考試命題工作,也確實收集過這方面的資料,做過初步的研究,似乎也有過一得之見發表于報刊,但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顯然不能與他相比。當我花了幾天時間讀完他結集的全部文章后,佩服之心,油然而生了。
文章聚焦于語文教學的各類測試,特別是對閱讀測試中命題工作涉及的各個方面,做了深入而細致的探討。雖然切入文章的角度比較多,但有一個總特點貫穿始末,那就是強烈的問題意識。無論是整體的學理闡釋(比如梳理國外布盧姆、安德森等教育目標分類學的知識點以構擬我們的測試層級目標);還是局部的對試卷題干用語或者所擬答案的解析,或者是對中外母語教學測試的比較研究,都是由當下語文教學實際問題、由命題工作遭遇的實際困難所引發的。這些問題既有操作層面的,更有觀念層面的。或者說,這兩個層面的問題有分更有合,使文章對問題的探討,常常由操作而深入到觀念,并由更新了的觀念推動對現實操作的反思。這種由問題意識主導下的深入探討,在他《拓寬文學類作品閱讀題的文本選擇路徑》一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其結論不但拓寬了命題者的視野,也對語文閱讀教學中的思維定式,有相當沖擊力。其他如對語文教學中閱讀理解和分析能力的界定不清,閱讀主觀題答案要求的非主觀性,探究性試題的設計缺乏探究的實質等問題,都做了深入分析,其結論也大多令人信服。
馮老師雖然是從語文命題角度提煉出他論文集的關鍵詞,但其意義又不局限于命題工作,更不僅僅是為語文教師出一套規范、合理的試卷作為指南(雖然這也很重要),它對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的教師、對語文界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語文教學的測量與評價對推進語文教學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當前應試教育屢遭社會詬病時,如何科學合理地開展測量評價工作,理性看待考試問題包括命題工作,就顯得尤為迫切。該論文集提出的觀點,有的能澄清時下的一些模糊看法,有的能糾正語文界趨同性的偏頗見解,即便對一些你未必認同的分析和結論,也能促使你更深入地思考相關問題。閱讀得來的這些顯而易見的收獲,大概是我讀后佩服他的主要原因吧。
是為序。
(馮淵著,《語文要怎么考——中學語文命題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