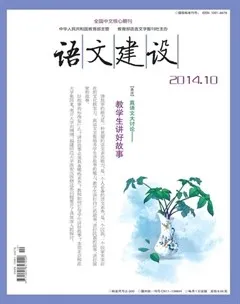《雷雨》臺詞品讀舉隅
《雷雨》第二幕周魯相認部分被選入不同版本的高中課文。一般的課堂上,教師免不了讓學生討論“周樸園對魯侍萍的感情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樣的問題。問題本身沒有錯,但筆者以為,課堂上無論圍繞怎樣的問題或話題進行學習與討論,都離不開對臺詞的細細品讀,絕不能“根據我的愛情觀”離開文本簡單揣想。對此經典中重要臺詞的品讀文章已很多,筆者就本文選擇周樸園向魯侍萍打聽當年的侍萍時的臺詞,以及其中容易被忽略的兩處運用比較的方法細加咀嚼。
為闡述方便,先把相關臺詞引述一下(本文對臺詞的引述都依據蘇教版高中教材):
一、“身份”強調里的復雜心理
在說到三十年前的侍萍時,周樸園和魯侍萍對其“身份”有不同的表述,且都有較大的強調。
周樸園把梅侍萍身份美化為“很賢慧”“很規矩”的“年輕”“小姐”,從中我們可以揣摩到三層意味:第一,這是周樸園在向一個陌生的無錫人打聽事情,這事又恰好是他這么多年來心頭不愿解開的結,打聽的時候似是而非可以多少掩蓋其與自己的關系;第二,周家少爺與女仆的女兒發生關系還把人家逼上絕路,多不體面,說“年輕的小姐”可以顯得體面些,作為現在“社會上的好人物”的周老爺更容易說出口些;第三,言辭上的美化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他潛意識里對當年與梅侍萍的感情的珍視,他現在的太太蘩漪恰恰就是“果敢陰鷙”,常常“不服從”,在他看來是與“賢慧”相去甚遠的,所以,在他的內心,在他最深的潛意識里,更愿意留存對侍萍的美好印象,以慰藉如今常感孤獨的心。
那么,魯侍萍為什么要“針鋒相對”地“作踐”自己當年的身份呢?“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賢慧,并且聽說是不大規矩的……聽人說她生前是不規矩的……她是個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聽說她跟那時周公館的少爺有點不清白……她不是小姐,她是無錫周公館梅媽的女兒,她叫侍萍。”其中同樣有豐富的意味。
首先,最直接的,這是她對周樸園說的情緒話。我們可以揣摩其潛臺詞:看你說得多好聽,我就是要揭穿你!“小姐”,真是“小姐”,你們周家會輕易地隨隨便便趕走嗎?你這是在美化你自己吧!
其次,她是在表現她的“悔”。后文魯侍萍在他們相認后有一句話:“我的眼淚早哭干了,我沒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我們可以從這里她對“不大規矩”“不守本分”的強調中讀出她的“悔”。這“不大規矩”“不守本分”可以看作是她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評價當年的自己——“單純”“幼稚”“無知”“自食其果”。我們可以想象,這么多年,她就是這樣為她的“苦”尋找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一切都是自找的,能怪誰呢,這也許就是一個自尊的人能夠受侵凌而依然堅強活下來的原因吧。
最后,她這也是在向周樸園憤然傾吐她的“苦”。如果我們再多想一想,這“不大規矩”“不守本分”也是當年出了這么“出名”的事情之后周圍人對她的評價。想想,她,還有她的母親——梅媽,當年必須在這樣的唾沫星子里生活。母親被氣死,很大原因就是出于這種輿論的壓力,而她自己投河未成被救起后也不得不到“外鄉”討生活。想想吧,在那個社會,出了這樣的事,周家、周家少爺偶或被少數幾個知情人譴責幾句,但下人梅媽、梅媽的女兒恐怕總是更被恥笑和鄙夷的吧!這就是梅侍萍當年的“苦”——精神上的“苦”!至于“一個單身人,無親無故,帶著一個孩子在外鄉,什么事都做:討飯,縫衣服,當老媽子,在學校里伺候人”,這些物質生活上的壓力還是其次的。
二、“忽然”背后的不同情味
說到當年的事情,周樸園和魯侍萍似乎不經意地都用了“忽然”,透過這個詞我們可以在比較中讀出不同的意味。
周樸園說的是侍萍“忽然”——“忽然投水死了”。表面上看,這是三十年后他向別人打聽這件事這個人時的“客觀”表達,實際上隱瞞了真相,也隱含了其逃避責任的心理。當然也有可能包含一定的“不理解”——好好的怎么就投水了?當年侍萍可能是被周家當家人趕出去的,周樸園有些無奈,但從“忽然”一詞還是可以看出他的冷漠、不關心以及對侍萍自尊心理的不理解。
魯侍萍說的是周樸園“忽然”——“忽然周少爺不要她了”。表面上看,魯侍萍這里說得并不“客觀”,因為當年趕她出周家的人最主要的似乎不是周樸園本人,因為后面有這樣的臺詞:
問題是,既然魯侍萍將“債”記在“老太太”頭上,那么,魯侍萍面對周樸園為什么說“忽然周少爺不要她了”而不是“忽然周家不要她了”?
這里其實涉及相認前魯侍萍的心理。在與周樸園對話前魯侍萍已經從這間房里家具的擺設和自己的相片知道了眼前所在就是周公館,認出周樸園后她并沒有走,內心里已經決定要相認。她為什么有這樣的決定?首先從后面她撕支票可看出她是自尊的,絕不屑于讓周樸園做經濟上的補償。那么,很有可能在感情上她對周樸園還是存有幻想的,當年與周少爺的初戀畢竟給她留下了些美好回憶。再從她把當年的“債”更多記在周家老太太頭上可以看出,很有可能當年被趕出周家門時周少爺也沒有太多機會跟她解釋,因此,她很想聽聽周樸園會怎么解釋當年的事,很想聽聽這么多年來周樸園良心上是怎么看待這件事的,如果真只是老太太的主意,周樸園這幾年一直心存愧疚,那么,她這么多年受的苦總算還有少許的安慰。有一句臺詞也可以證明相認前魯侍萍存有感情上的幻想:
樸你——侍萍?(不覺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魯媽。)
魯樸園,你找侍萍么?侍萍在這兒。
魯侍萍的這句話在人教版中是沒有的,注意這里魯侍萍對周樸園的稱呼——“樸園”,這個稱呼讓我們依稀仿佛回到當年梅侍萍與周少爺花前月下溫情脈脈的情景,如果只有恨,她完全可以稱“周樸園”,或者干脆嘲諷地稱呼“周大少爺”(像后文那樣)。
既然魯侍萍尚對周樸園存在幻想,想聽聽對于當年周老太太一手操辦的事周少爺的解釋是什么,這么多年來是怎么看待這件事的,那么她就沒有必要在這里提到“周家老太太”或者“周家”,而直接說“忽然周少爺不要她了”,把問題和疑惑直接拋向當年的周少爺、如今的周老爺。只有在相認后,周樸園的種種表現讓她徹底失望后,她才以控訴的口吻說“你們”“你們周家”,連續的“你們”“你們周家”能增強控訴的意味:你看看你們周家,現在社會上的名門望族,當年你們都干了些什么?!
更有意味的是,這兩個“忽然”離得那么近,像是魯侍萍敏銳捕捉到周樸園的“忽然”而有意套用的。我們不妨站在魯侍萍的角度揣摩一下她聽到這個詞的心理:明明是被你們周家、周少爺逼著去尋死,你周樸園卻說“忽然”,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詞,可以掩蓋多少難堪和良心上的不安!你們文明人用詞就是滑頭,我也用一個“忽然”,“生了第二個,才過了三天,忽然周少爺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館,剛生的孩子她抱在懷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既揭穿你掩蓋的跳河原因,也讓你體會一下這“忽然”里的絕情、人心的易變和對我的傷害!
同樣的事情,不一樣的述說,背后是何等豐富的意味,昭示著人物何等細膩而復雜的內心糾葛。高爾基說:“劇本要求每個劇中人物用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提示。劇中人物之被創造出來,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臺詞,即純粹的口語,而不是敘述的語言。”[2]《雷雨》臺詞之精彩從這兩個人物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述說中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夏竹.曹禺與語文老師談《雷雨》[J].語文戰線,1980(2).
[2]高爾基.論劇本[M].//文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24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