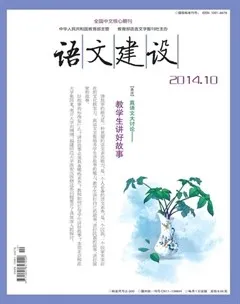胡懷琛的《中學國文教學問題》及其啟示
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有相當一部分博學的國學名家熱心關注語文教學問題,他們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見至今仍然有參考價值。本文談談胡懷琛和他的《中學國文教學問題》。
一、胡懷琛的著述
胡懷琛(1886-1938),原名有懷,字季仁,后改名寄塵。著名國學家胡樸安之弟。安徽涇縣人。少時聰穎,七歲即能詩。應童子試(秀才),不愿做經義試題,于紙上賦詩一首:“如此淪才亦可憐,高頭講章寫連篇。才如太白也遭謫,拂袖歸來抱膝眠。”交卷出場。20歲時再試,因為不避清帝之諱被黜。從此不作“制藝”(八股文)和試帖詩。后入南洋中學讀書,畢業以后即鬻文自給,終日筆耕不輟,勤奮好學。后與其兄胡樸安一起入南社,與柳亞子成金蘭之契。先后在《神州日報》《太平洋報》《中華民報》當編輯,在新聞界頗著名聲。民國九年起應聘在滬江大學國文系,旋辭職,應王云五之邀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參與編寫中小學教科書工作并兼任商務印書館的《小說世界》編輯。后又參與《萬有文庫》古籍部分編輯工作。此后先后在中國公學、滬江中學、持志大學、正風學院擔任教授,講授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等課程。民國二十一年受聘為上海通志館編纂,教書、編輯之余,勤于選編、著述。治學涉及范圍極廣,文史哲以外旁及佛學、考據、方志、評論等。門類眾多,學問博洽。所著存目有一百余種一千余萬字,主要著作有《國學概論》《墨子學辨》《老子學辨》《文學源流淺說》《中國文學史略》《修辭學發微》《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通評》《中國詩學通評》等百余種。這些書先后由商務、世界、廣益、崇文、新中國等書局出版。此外,胡懷琛編有多種教科書,編寫的《古文筆法百篇》一書流傳甚廣。胡氏一生好學,家境貧困無恒產卻酷愛藏書,藏書以詩文集和教科書為特色,蒙學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版本收羅殆盡。劉鶚稱其為“三、百、千、千”。惜其藏書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寇轟炸上海時損失大半。他本人也因國仇家恨郁積深重,于1938年卒于寓所“波羅奢館”。1940年,他的藏書由其哲嗣古籍版本專家胡道靜捐給震旦大學。
胡懷琛和黎錦熙一樣,在商務印書館編寫過中學國文教科書,又十分關注中學國文問題,在大學又教語言文字類課程,所以對中小學國文諸多問題看得明白透徹,所發議論切中肯綮。20世紀30年代他在上海的《時代公論》《教師指導》等雜志發表過《語文問題的總清算》《關于選讀中學國文的話》《中學國文作文問題平義》等長篇文章。有的還署名“上海高中教員胡懷琛”,可見他是做過中學國文教師的。胡懷琛關于中學國文研究的文章有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中學國文教學問題》。
二、關于《中學國文教學問題》
本書在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一本論文集。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作者在“凡例”中說:“為增加中學國文成績起見,將國文選讀及作文上各個問題拈出,逐個加以適當的解答。”全書共十六篇,每篇解答一個問題。依次排列,有一定的系統,但每篇又獨立,所以分和合,閱讀都很方便。確如作者自己說的:既可備中學國文教員參考之用,也可讓中學生做課外讀物。這十六篇依次是:(一)清理中國語文的方案(國文的性質和地位);(二)中學國文選讀問題;(三)從文法到文學;(四)文與題;(五)題目的性質和命題的方法;(六)文的分類;(七)文的內質和外形;(八)文的作者和讀者;(九)練習和模仿;(十)別字問題;(十一)改卷子問題;(十二)讀經問題;(十三)翻譯問題;(十四)譯名例;(十五)國文教員的地位;(十六)自己介紹幾本書。雖然作者自謙為“野人之曝”,這十六篇文章卻都是作者深入思考觀察的產物,可以說都是一些真知灼見。簡略地說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1.關于國文性質和地位的問題
自從1904年以后,關于中國語文問題的爭論就一直存在,各方各執一詞所以爭論永無休止。作者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出:為了增進中學生的國文程度,我們不必做無謂的爭論,而要做一點實際工作。這“實際工作”可以分為:第一步,把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分做兩件事,前者無論什么學科的學生都要學,后者則是學文科的人必須學的;第二步,要把中國語文做得“合理化、實用化、普遍化”,用字造句都要正確;第三步要定下三個好(文章、文字)的標準,在不隱晦的范圍以內愈簡單愈好,在不枯窘的范圍以內愈樸素愈好,在不浮泛的范圍以內愈淺近愈好;第四步,我們要整理原有的文法,取優汰劣,同時要適當吸收外來文法,拒絕不適用的部分。關于這四點,胡懷琛在文中分別用確當的例子加以說明。這聯系到當時的背景,更覺得胡懷琛的見解有道理,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是也。30年代初有關人士在上海發起了“大眾語運動”“漢語拼音化運動”“拉丁化中國字”“世界語運動”等。比較保守的堅持傳統文化的一些人和激進的左派人士爭論甚囂塵上,前者往往把語文和文學(其實是古文學)混為一談,陳義過高,要求中學生讀古書古文學,甚至讀經;后者往往罵倒一切傳統的東西,甚至連漢字也成了中國人民愚昧的替罪羊,魯迅、瞿秋白等人發表過許多批評“方塊字”的文章,他們提出要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1933年,蔡元培、孫科等人還發表了《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有許多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署名。很有意思的是,幾個國語運動頭面人物胡適、黎錦熙、周作人等未署名。[1]爭論的背后其實各階層有其不同的目的,這些因素要在幾十年以后才能搞清楚,但是當時關于中國母語教育的局面,真如胡懷琛所說的,“已到了極度混亂的時候”,這對在中小學教國文的人來說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名人們眾說紛紜,往往會讓底層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不知所從,這種情況今天也經常見到。因此,非常需要真正內行的專家發出理性的聲音,把問題解答得明白一點,而不是搞排山倒海般的宣傳。當時一批真正的語言文字方面專家呂思勉、林語堂、郭紹虞、陳寅恪、楊樹達、劉永濟、王力就曾對國文教學發表過中肯的意見,胡懷琛也是。例如,林語堂在他主編的雜志《論語》上發表過一篇《與徐君論白話文言書》,提出要吸收文言、外國語的長處,“要望中國將來演出又美麗又靈健的文字來”,“凡事只論是非,不論時宜”。陳寅恪在有名的《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徑斥那些熱衷套用外國拼音、語法一套的東西為:“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想想今天語文教學界的亂象,令人感嘆。
2.關于閱讀和作文教學的問題
在第二、三兩節里,胡懷琛討論了國文的選讀和文法、文學問題。由國文的性質決定了文章選讀的標準,他認為可以把選文分為四類:考據的、思想的、欣賞的、實用的。當然,由于選者立場不同,同一篇文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例如《孔雀東南飛》有人注意里面的典故,有人想到古代婚姻問題,有人只知道這是一首富有情感的民歌,而站在實用角度的立場認為可以不選。胡懷琛認為作為國文教材應當兼顧四種不同類型的文章,不能只站在一種立場上導致偏輕偏重。對于文法等問題,他說,中學國文要把文法、作文、修辭、文學四件事分一分清楚,然后教起來比較好教。實際情況是當時的教師和學生都分不清楚,結果是不容易獲得進步。他認為文法問題是一個“要緊”的事,但是“在中國人眼里以為文法比作文難,不講文法也會作文,應該把文法放到作文以后去講”。胡懷琛認為文法比作文簡單,因為作文包括許多內容。然后他舉例說明了為什么作文比文法難的原因,他提出首先要學一點簡單的文法,“把最基本的幾條大綱弄清楚了,在作文時可免掉一部分的錯誤”。強調文法教學這一點和胡適在《中學國文的教授》里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胡適是精通英語的新派人物,而胡懷琛則是一位國學家,從這一點看他完全是一位通達之士。章太炎曾說過“凡事當以是非為準,不當以新舊為準”。當然,究竟要不要在中學語文課上講語法,如何講語法,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不同看法。
從第四節到第九節,胡懷琛主要以作文為中心講解國文教學問題。關于作文命題,他認為主要有三類:一是作者自由作文然后起個題目,二是教師命題,三是考試時由專門人命題。對三類題目要區別對待:第一類要求學生根據文章重要內容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出來,而二三兩類題目必須顧及學生的知識經驗范圍,第二類有時還要提供“相當的材料”。關于作文,胡懷琛提出的多練習、重模仿的主張是最有價值的。他說,一般人認為練習是極麻煩之事,而模仿是“極鄙陋的事情”,這兩種說法對創作詩歌、小說來說是對的,但是對中學生習作,那是“誤會了”。他說小孩說話也是從模仿開始的,所以初學作文模仿是必不可少的。對于作文的分類他很重視,同樣寫一樣東西不同要求須用不同文體,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各有各的用途,不能混淆。他主張作文從形式看要掌握各種文體寫法,從內質看要養成各種情感思維習慣。總的說來,先要求準確,然后再一步步求巧妙優美。這與黎錦熙、王森然等人提倡學生作文“先求其通,次求其美”是完全一致的。
3.關于中學生“讀經”和翻譯的問題
關于中學生是否需要讀經,歷來有兩種不同意見,或提倡或排斥。1934年《教育雜志》發函給學界專家,咨詢對于學生讀經問題的看法,收集到蔡元培、唐文治、錢基博、陳立夫、胡樸安、顧實、陳望道等七十余人的意見書,翌年還編輯成專刊出版。有意思的是他們中大多數是國學名家,而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折中的:可以選一點有益修養的經典片段讀,不主張完全讀整體的經,也不主張完全排斥。胡懷琛也取這種意見。他認為對“經”要具體分析,儒家經典中有許多今日仍然適用的話為什么不可以讀?如:“天下為公”,“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他認為中學國文雖無“讀經”之名,但選文《論語》《孟子》《禮記》本身就是經。因此,對于讀經這件事,他的結論是:“無論如何,于讀者的人格修養方面,多少有點益處的,而且分出若干功夫讀這三十至五十句也很簡單易辦,不至妨礙其他功課。這豈不是一種很好的辦法。至于‘經’的全部,由其他專門學者去研究便是也,不必由國文教員自己再向‘經’中去覓取教材了。”關于青少年讀經問題近年來也常常被提及,臺灣地區有人大力提倡,以為可以拯救世道人心,內地也常常有呼應者。其實不妨讀讀七十多年前那些真正懂得經書的老先生的意見,或者讀一讀海外余英時先生的書,就不會盲目跟著時風走了。
關于翻譯問題也是當時國文教學中常見的,不少學校把它作為作文的一種,有外國譯為中國的,也有文言文和白話文互譯的。對此胡懷琛持反對態度,這一點和錢基博不同。他覺得兩個國家文字語言不同,翻譯外國文不是簡單地讀得通就可以了,而是要把“其中風俗習慣處徹底弄明白”才可以談翻譯,這對中學生來說太難了。他也明確表示,反對有些人把《詩經》《楚辭》譯成白話。
除了上述三點以外,胡懷琛還專門對國文教師的地位問題發表了意見,認為國文教師地位不高是造成學生成績不好的原因之一:“國文教員既然被人家看輕,那么學生在學校里的國文成績如何會好?”當然,他認為國文教師首先自己要看重國文,看重自己,明白國文的重要性:“既是中國人就應當通中國文。在國界還沒有消滅的時代,雖然也須兼習外國文,但終須以本國文為重,外國文為輕。”他說:“國文是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種工具。國文教員是應用這種工具的指導者。”這和王森然在《中學國文教學概要》序言里的話完全一致。最有意思的是本書的十六節“自己介紹幾本書”,他說這并不是為自己做廣告宣傳,而是要“增加讀者對于我的信任心起見,很誠懇地告訴讀者,我對于國文教學是有相當的研究的”。這些書包括《一般作文法》《作文研究》《標點符號使用法》《記敘文作法范例》《抒情文作法范例》《說明文作法范例》《議論文作法范例》,以及關于修辭、古書今讀法、中國文學史等方面的著作。可見作者確實是一個內行。
三、幾點啟示
老實說,胡懷琛提出的一些見解并沒有什么驚世駭俗的主張,他說的都是一些平實的話,和其他幾位名家差別并不大,但是作為一個真正懂行的專家,在那個喧囂的時代有他特殊的意義。國文教學雖是平常事卻是“茲事體大”,實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發一通議論的,即使是專家,如何表達自己的思想也是有講究的。以筆者愚見胡懷琛的論述給我們的啟示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討論問題應當有一種平和的態度,不要把討論搞成“宣傳”。王力先生早在《漢字改革》中提出,“凡是宣傳,就不免對于不利的事實有所掩飾,同時對于有利的事實有所夸張”。這幾年關于中學生學“國學”“讀經”等討論常常有此弊端,本來很好的討論變成無謂的爭論。
第二,專家要用通俗易懂的話表達思想,不要動輒搬來高頭講章甚至杜撰一些艱澀術語嚇唬中小學老師。這幾年語文研究局面看起來很“繁榮”,其實“人們只是由于濫用名詞,才自以為說了許多不同的東西,實際上他只是在說一些不同的詞或不同的聲音,并沒有給這些詞或者聲音任何真實的觀念或區別”,“事實上,所有別的注釋家們直到現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2]
第三,要多研究一些實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要熱衷于建構“體系”,講些不著邊際的“混話”——不中不西非驢非馬混搭的話。筆者審讀的研究生論文許多就是這種文風的產物。讀這些文章常常令我想起陳寅恪“認賊作父”“何其不通”那幾句憤激的話。老先生一定想到了孟子的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總之,要多從傳統語文教學那里多吸收思想資源。想一想,過去人們讀了四五年小學,國文就通了,這里總有它的道理。
參考文獻
[1]倪海曙編.中國語文的新生[M].上海:時代出版社,1949:120.
[2][法]拉·梅特里.人是機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