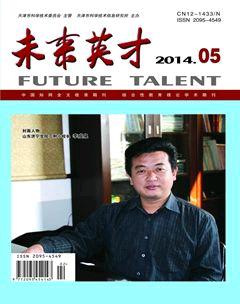“咬”出印記,“嚼”出味道
孫茜
語文是由語言文字組成的充滿生命活力的課程,絢麗多姿的語言是語文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而缺少了語言的課堂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語文課就應該在濃濃的語文味中,在滿懷詩意的情境中,在豐富的語言想像中,讓學生通過品讀語言文字,去享受文學的魅力。
錢理群教授說“語言文字要引導學生去感受、體味語言的氣韻,內在的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精神”。如何在閱讀課中引導學生品味語言,從而摸索語言形式規律,獲得語言表達智慧,使我們的語文課“無時不語文”呢?我認為“咬文嚼字”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教學策略。朱光潛先生說過: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但在實際上就是調整思想和情感。下面,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一、“細”枝末葉探真意。
咬文嚼字,換言之,就是細細品讀。王尚文先生說,文本細讀就是“傾聽文本發出的細微的聲音”,這種聲音首先來自文本的語言。細讀,常常要從尋找詞語推敲處的罅隙入手,從而“牽一發動全身”。
如:在學習《老王》這篇課文時,就“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 ”一句中的“鑲嵌”一詞,我請學生做理解分析。有學生認為“鑲嵌”一詞多用于形容美好的事物,而用在一個窮困艱難、疾病災難纏身的老王身上,實不合適。于是,我引導學生進行了一系列的推敲。
1.把詞語放到具體的語境中理解。“鑲嵌”一詞前有一個“直僵僵”,這一詞寫出了老王最后一次登門時身體虛弱,四肢也不能靈活地活動。“直僵僵”直接引起了楊絳先生用“鑲嵌”一詞來形容老王依靠在門框上的狀態。《現代漢語詞典》對“鑲嵌”的定義是“把物體嵌入另一個物體內或圍在另一物體的邊緣”。這就表現了老王像是門框上嵌入的一個器物一般,已完全失去了力量和活氣。顯然選用“鑲嵌”一詞,恰如其分。
2.從作者的情感傾向和文本主題來分析。楊絳先生一直被“為老王做得太少的愧怍折磨著”,因為此時面如死灰的老王讓她吃驚,讓她害怕。這份害怕甚至讓楊絳先生忘了道謝,忘了送老王下樓。從中可以看出楊絳先生對老王是有感情的,只是苦于無力回天,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對更弱勢者施以人性的關懷。
二、“讀”占鰲頭品語言。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張銳教授說得好:“我們面對的文本就好像一座島嶼,有水面之上部分,水面之下部分,還有河床部分。”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不能只遙望水上部分,繞島嶼走馬觀花地游一遭,而要設法挖掘這座“島嶼”。教師要引導學生深入文本,作深層次閱讀,不斷挖掘文本。
下面我以契訶夫《變色龍》中奧楚蔑洛夫穿大衣和脫大衣這個細節閱讀為例。
我在教授這一課,學生讀到這一細節的時候,僅僅是笑了幾聲。笑聲,說明學生并沒有深思作者為什么要這樣著墨一個尋常不過的細節,也沒有揭開詼諧夸張的外形下深刻的內涵。針對脫衣穿衣這一細節,我引導學生去反復讀。學生自己讀,表演讀,反復讀,在讀中思考省略號所起的作用。
通過讀,學生明白了:首先,脫衣這一細節揭示奧的誠惶誠恐。狗是將軍的,那條小狗在他眼中仿佛也成了“將軍”,想在將軍頭上動土,能不渾身發熱?其次,奧用這個動作來遮掩自己的出爾反爾。剛才還在慷慨陳詞,表示要秉公行事,突然又要改變口氣,中間總要做點什么過渡一下,不至于讓自己丑態畢露,這顯然符合人物當時的心理。再則,為下文的“穿衣”留下伏筆。奧的話后面還有反復,這個“脫衣”在這里還有提示讀者留意的作用。
領會了“脫衣”所蘊含的深意,“穿衣”這一細節的作用也就一目了然了。前者脫衣,后者穿衣,這一脫一穿,可謂相映成趣,其作用卻又異曲同工,這個小丑的一系列復雜、卑劣的心理,隨著這兩個極其簡單、不起眼的小動作暴露得淋漓盡致,展示了一個活脫脫投機應變、趨炎附勢的走狗形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三、填補“罅隙”出深意。
每一位作家在寫作作品時,總會留下些許空白,讓讀者去想象,去填充,去豐滿,去體味言外之意。這就需要學生在教師引導下,深入文本,揣摩作者意圖,構建多重對話,填補文本空白。
如魯迅先生的《孔乙己》。“孔乙己大約的確已經死了”。作者為什么要采取矛盾化的寫法,留下一個生死未卜的懸念,意圖何在?這一問題有必要引導學生進行探討。
首先讓學生續寫孔乙己離開咸亨酒后的情況。學生的想象力是豐富的,思維是天馬行空的。有的學生能依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寫出較為合理的結局,有的可能處于同情或想有創意,寫出較為荒誕的結局。那究竟哪種更合適,孔乙己究竟有沒有死,這就要細細揣摩。
“大約”、“的確”,一個表揣測,一個表確定,看似自相矛盾,不過仔細琢磨,反而覺得別有味道。從孔乙己這個悲劇人物的命運來看,他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別的結局:腿被打折,他的生計已很艱難,何況折腿以后,除了窮死,別無生路,“的確”一詞是孔乙己悲劇的必然歸結。顯然,“的確”一詞,是承前文而來的,這種對孔乙己結局的交代,是完全符合“我”當時的想法的。但又因為沒有確切的消息,終究只是一種懸想,所以還得用“大約”。再往深處想,大約一詞還表現了孔乙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在那樣冷漠的社會里,有誰會關心、會在乎他究竟是生還是死呢?“大約孔乙己的確是死了”,魯迅先生這么糾結的寫法已不僅僅在于批判和同情,而更多的是痛心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