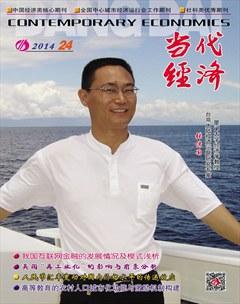明清浙江地域多商幫興起原因分析
冀春賢 王震宇
【摘要】 明清浙江地域多商幫興起有其必然。浙東文化“經世致用”、“工商皆本”思想的深刻影響,經商傳統的根深蒂固,人多地少倒逼經商,水陸交通的便利,農業由單一向多種經營的轉變,手工業的興盛與專業生產區的出現,城鎮的興起,商業與貿易的繁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商幫在浙江地域內相繼涌現。
【關鍵詞】 明清浙江 ?多商幫興起 ?影響因素
明清時期,浙江狹小地域內有多個商幫興起,龍游幫、湖州幫、寧波幫、紹興幫、杭州幫等,多商幫的興起和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浙江經濟發展、人文思想孕育的一個必然結果。
一、浙東學派經商思想的影響
明清之際由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是浙東地區發達的商品經濟和中華民族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思想成果。自成一體的浙東文化中的“經世致用”、“實功實用”、“工商皆本”思想,孕育了浙江人強烈的經商意識,因此,根深蒂固的重商思想和經商傳統是浙江地域多商幫興起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深厚的民間經商基礎和龐大的商人群體陣容。浙東學派的重要的思想取向是“經世致用”,對浙江地域經商思想的影響,主要體現再以下幾個方面。
1、經世致用思想
黃宗羲等一批具有經世精神的浙東知識分子依據市民社會的生活規則批判君主專制制度和程朱理學,竭力反映“士、農、工、商”的利益,要求經書研究要與當時社會的迫切問題聯系起來,并從中提出解決重大問題的方案,反對空談。明末清初,經世致用之學大興,形成了一股有影響的社會思潮,生活在浙江地域內的人們深受浙東學派思想的侵染,在渾然不自覺中深深刻上了“經世致用”,思想的烙印。“經世致用”思想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地方人文精神的實質,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成為他們的主導思想。
2、工商皆本思想
在經濟觀念上,浙東學派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重本(農業)抑末(工商業)”作為基本國策。明清時期,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國策,規定“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嚴禁棄農從商。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從反對“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倫理觀念著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從理論上說明了“工商皆本”經濟觀念的正確性,從而為人們經商,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思想武器。
3、民富先于國富的思想
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學說。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主張以農為本,以“強本”、“務本”的辦法富民;富民的目的是強國;富民的原則是“均富”。而浙東學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他們所重視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認定“商賈”與“力田”一樣都是致富的正途;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富民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們反對國家壓制、侵奪富民的財產,贊同追求財富,只要君子取之有道即可。認為只有民富,才能使官民和諧,使國家變的易于治理。這種富民觀念順應了百姓及時代發展的要求。
4、義利統一思想
在“義利”觀念上,儒家義利觀的基本觀點是重義輕利。浙東學派則主張義利統一。陳亮曾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將“理、德”和功利統一起來是浙東學派對商業精神發展的一大貢獻,使商業的發展具有了理論上的支撐,尤其是在道德上的支撐,確立了與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相一致的義利觀。
總之,浙東學派對商業比較贊同,主張提高商人和商業地位,其所倡導的公私觀、經濟觀、富民觀、義利觀,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他們的經世致用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對后世尤其是明清以來對浙江社會有深刻的影響,成為浙江人的文化自覺,而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也成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征。正是浙東學派為商品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思想道路,明清時期在浙江狹小的地域范圍內紛紛興起經商之潮,繼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商人群體。
二、自然地理條件對浙江地域商幫興起的影響
明清時期興起的浙江地域內以地緣為基礎,以血緣為紐帶的多個商人集團,與當時的自然地理條件也是密切相關的。
1、迫于生計去經商
縱觀明清時期各地商幫的形成,凡是興起商幫的地方,其客觀條件之一大都是地狹人稠,自然條件惡劣,人田矛盾突出,經商成為當地人無奈也是必然的選擇,屬于被逼經商。浙江雖相對富裕,地土肥沃,但地域狹小,并且產生商幫的地方恰恰人多地瘠,條件較差,單靠農業產出難以養家糊口,不少人是被逼經商。明后期,人田矛盾更為突出,興起商幫的龍游、寧波、紹興在浙江都是自然條件不夠好的地方,單純的務農已無法解決生存問題。龍游地處浙西山區,多山少田,生存困難;寧波“濱大海,居斥鹵之中,其土瘠而無灌溉之源,故耕者無終歲之給”,“人稠地狹,豐穰之歲猶缺民食十之三”。湖州雖地理位置優越,自然環境較好,但由于太平天國運動后,大批人口為躲避戰略聚集于此地,造成人地矛盾突出,單靠農田所入,已無法正常維持生計。在此情況下,經商成為這些區域內人們無奈也是必然的選擇,一批又一批地地道道的農民被迫走上了經商道路。
2、浙江境內便利的水陸交通
明清時期江南水運事業很發達,浙江境內盤踞著錢塘江、甌江、椒江、甬江、苕溪、運河、飛云江、鰲江八條長龍,密布著杭嘉湖、姚慈、紹虞、溫瑞、臺州五大平原河網。密布的河網、八大水系連接著大江南北,為商人的商品販運提供了便利,溝通了浙江與其它區域的經濟文化交流,為商幫的興起提供了客觀交通運輸條件。
三、浙江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
明清時期,浙江多種經營和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導致了市鎮經濟的繁榮,傳統的產業結構出現了深刻變化,一大批中小城鎮興起,為浙江地域內商人的聚集、商幫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1、農業種植的變化
明清浙江農業經濟的變化主要反映在由單一的水稻種植逐漸向麻、絲、茶種植轉變。
(1)蠶桑業興起。由隋唐以后至宋元時期,浙江是全國著名的糧食產地,農業經營方式是單一的水稻作種植。元末明初時期,這種單一的稻作經濟發生了變化,以蠶桑棉麻為主的經濟作物種植業與專業化的農業生產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入明以后,浙江北部地區逐漸成為當時全國絲織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杭嘉湖成為全國植桑飼蠶的著名地區。該地區的廣大農村,桑蠶種養業極為普遍,幾乎達到人皆植桑,戶戶養蠶的地步。養蠶收入的提高,推動了農業的轉型,到了清中期以后,桑蠶種植在浙江農業中占據主要地位,糧食種植降為次要地位,浙江單一的稻作經濟為主要的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為“以絲佐谷”的新的主從關系。
(2)棉麻業興起。浙江棉花的種植以寧波、紹興、溫黃平原為最普遍。當時紹興府的余姚縣所產“浙花”極為著名,至明清時,棉花種植普遍,推動了當地棉紡業的發展。除種植桑棉兩宗大的經濟作物外,浙江各地還大量種植麻、茶、豆、菱、煙草、柑桔等。
2、手工業的興盛與專業生產區的出現
浙江的手工業在明代初年還處于手藝人或手藝人作坊的階段,到成化年間,民間私營手工業在原來基礎上逐漸興盛起來,尤其是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更促進了城市手工業商品生產的蓬勃發展,并由此帶動了商業及整個城市及城市輻射區域內農村經濟的起飛。
浙江手工業以絲織、棉紡為主,杭嘉湖是當時全國絲織生產與交換的中心,那里桑麻遍野,全國繭絲棉大都出于此地,引來無數商人云集。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技術的不斷提高,杭州一些絲織手工作坊還擴大為手工工場。明末以后,在杭州還逐漸形成了專業生產區。嘉興、湖州二府的絲織業及其他手工業亦相當發達,絲織行業還有了相當細密的專業分工,形成了比較有名的絲織、棉紡專業市鎮、生產其他商品和進行農副產品加工的專業城市。遍布鄉村的大大小小市鎮,構成了密集的市場營銷網絡,到明代中后期,嘉興、湖州兩府就有各種市鎮近七十個,至清代又有增加。
3、商業與貿易的興盛
明清時期的浙江,各種農業區域之間的各種農產品的交換,使生產物轉化為商品,推動了整個區域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品種的增加,促進了商品流通的擴大,帶動了其他商業與服務性行業的繁榮。如杭州,就有“杭民半商賈”之稱,湖州的雙林、南潯經商者更是超過大半。
在貿易方面,浙江的寧波、溫州是對外貿易、海外交通的重要城市,浙江區域的商品如絲綢、瓷器、木材等得以通過這兩個港口城市輸送到國外市場,國內外貿易異常繁榮。由于海外貿易的需求,又刺激了浙江商品經濟的發展。如湖州的南潯鎮,既是當地絲、茶特色產品的專門性生產基地,又是國內生絲的集散中心,搭起了湖州絲、茶進入國際市場的通道。除了南潯外,寧波、溫州、杭州都曾是明清時期貿易的主要集散地。浙地各種農副產品大量運銷全國各地和海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對小農家庭的社會生活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為浙江商人走向海內外創造了條件。
隨著經濟、交通等因素的迅速發展,明朝以后浙江區域先后興起了大量嶄新的經濟型的城市,如嘉興一府,稱為市鎮的就有33個之多、湖州府有31個、溫州府在乾隆前已增至39個。城鎮的興起使大量農民離開了土地,到城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同時,大量人口的聚集與消費也成為商人經商的基礎。
總之,明清浙江商品經濟的發展,交通的便利,促進了貿易的繁榮,大量城鎮的形成,使農民逐漸擺脫土地,浙江地域內的商人隊伍不斷擴大,造就了一種世代相傳的商業智慧和商業技巧,腳步蹤跡遍及天下,形成了浙江地域內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商幫群體。
(注:本文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明清地域商幫興衰及借鑒研究——基于浙江三地商幫的比較》(批準號:11YJA770018)的資助。)
【參考文獻】
[1] 潘起造:明清浙東學派對經世致用傳統的傳承[N].光明日報,2004-11-16.
[2] 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的商品流通與水運業的發展[R].中國經濟史論壇,2005.
[3] 吳量愷:清代乾隆時期農業經濟關系的演變和發展[J].清史論叢,1979(1).
[4] 楊建華:明清浙江經濟結構變遷論[J].浙江師大學報,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