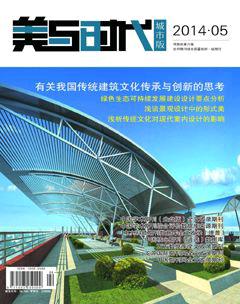城市公共藝術創作研究
高聰
摘要: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公共藝術建設之風愈發蓬勃。但從創作層面而言,多數公眾藝術作品卻如“無根之水”,更有甚者僅是簡單復制。通過從公共藝術的屬性研究出發,提出了公共藝術應具有傳播性、城市性、公眾性三層具象屬性,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兩個層面上的創作策略,以期為城市公共藝術創作貢獻出一份切實的實踐指導力量。
關鍵詞:城市;公共藝術;藝術創作
及公共藝術,想必無論是學界學者還是社會公眾都不陌生。公共藝術作為一個純正的“舶來品”,于20世紀70年代末引入中國,隨后迅速而適宜的在中國實現了本地化,即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時至今日,公共藝術已然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風景線,也多為政府及公眾所熟悉、所重視,真真切切地形成了一股建設風潮,風頭一時無二。
但遺憾的是,不管是從審美與傳播的角度,還是從城市化發展的角度,這股風潮呈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主要體現在公共藝術的創作層面,粗制濫造與審美乏味似已成為其代名詞。以雕塑為例,溫克爾曼曾對希臘雕塑有過經典評述,“高貴的單純與靜穆的偉大”。反觀如今作為城市公共藝術的部分雕塑作品,復制濫造暫且不論,更已淪為冰冷的金屬和無情的石材,毫無審美趣味可言。這也折射出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公共藝術的創作亂象便是其中之一,亟待解決。
事實上,任何藝術形式地創作,均需對此種藝術形式有深刻而又細膩的認知,公共藝術也不例外。我們認為,城市公共藝術的創作探索,便應從公共藝術的屬性研究出發。縱觀公共藝術研究史,對于公共藝術的屬性研究成果豐碩,觀點頻出。通過詳細地整理和系統地分析,我們將公共藝術的屬性總結為三個層面,即公共性、審美性與精神性。所謂公共性,從廣義上來講,是指藝術存在于公共空間與公共場所,是站在與私密性、個人藝術的對立面而言。如今以日常生活審美化和經濟審美化為主的審美泛化,與藝術公共化即公共藝術有著某種淵源。所謂審美性,顧名思義,任何藝術作品均有其審美價值,公共藝術亦不能免俗。相對傳統藝術觀念而言,公共藝術的審美性往往在于社會公眾,而不僅僅局限于特定的群體。而所謂精神性,亦一目了然,即公共藝術具備特定的精神內涵,這種精神內涵往往體現為城市、歷史、文化乃至社會公眾與生活。相對而言,這三個層面上的屬性之說,是側重于審美價值的。如果單純從公共藝術的實踐指導意義角度來講,就顯得略為空洞泛化,不能起到良好的理論指導實踐之功用。出于此種思慮,我們對公共藝術的屬性研究進行了更為具象和細致地區分,并據此提出了傳播性、城市性以及公眾性三個屬性,以更加深入的認識公共藝術并從實踐的角度提出更具指導意義的創作策略。
第一,傳播性;傳播是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從溝通的角度而言傳播亦是人類之天性。偉大先賢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而英文中的傳播與溝通確為同一詞匯,即“communication”。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如果說傳統的藝術形式傾向于“人際傳播”,那么公共藝術更傾向于一種“大眾傳播”,即與廣泛的社會公眾產生溝通和交流。事實上,所謂公共藝術的公共性,即帶有鮮明的傳播色彩。置身于于城市公共空間與公共場所之中的公共藝術,以社會公眾為審美群體的公共藝術,滿足傳播過程的每一個要素,即傳播者、信息、媒介、受眾,帶有不可剝落的傳播屬性。
第二,城市性;城市是一個沉重的詞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城市已不只意味著建筑群與人群,它的背后承載著多少歷史變遷與文化傳承。但遺憾的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當中,對城市歷史與文化的破壞也到了一個較為嚴重的地步。而公共藝術所具有的城市功能,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破壞,這也是為什么公關藝術的發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不僅僅是因其審美性。古老的城市,滄桑的歷史,精粹的文化,先民的智慧,皆能以公共藝術為主體并完美融入城市之中,所謂公共藝術之精神性,大抵如此。可以說,離開了城市,公共藝術不僅沒有了置身之所,也將會失去其靈魂歸宿。
第三,公眾性;作為公共藝術的基本屬性,公共性不容被忽略,即便上述所謂傳播性與城市性,仍帶有公共性之色彩。這所謂公眾性的內在涵義,更是一目了然。公共性使得公共藝術置身于公共空間與公共場所之中,也置放于“眾目睽睽之下”。傳播學角度所言之“受眾”,于公共藝術而言,便是這“眾目睽睽”的社會公眾。如果說城市意味著歷史與文化,公眾則述說著平凡的生活與散落的民俗。藝術傳播學曾詳盡闡述了藝術創作與受眾經驗之關聯,指出了藝術信息與受眾經驗之間的“契合”。走進公眾生活中的公共藝術,其社會學理論視角之下的公共性慢慢轉變為更接地氣“公眾性”,借以辨清公共藝術之本質。
基于上述所言之公共藝術的屬性分解,我們對公共藝術的本質與特點有了更為深入、更落到實處的認知。對于傳播性的提出與重視,將公共藝術納入到藝術傳播乃至大眾傳播的視角之下,為公共藝術的創作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深刻認識到了城市公共藝術創作與城市、公眾不可分割之關聯。基于此,特提出以下思路以作引玉之磚,以期指導城市公共藝術創作并引起相關研究學者之重視。
第一,以歷史為根,以文化為本,體現城市特色;歷史與文化是城市的根本,也是城市的特色。以城市為載體的公共藝術,更應以城市歷史為根,以城市文化為本,凸顯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傳承城市故事。事實上,不少城市已經認識到了公共藝術與城市文化傳承的緊密關聯,并涌現出了不少經典作品,比如蘊含上海歷史與文化的地鐵站浮雕、象征深圳精神的“拓荒牛”雕塑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當屬青島五四廣場的“五月的風”大型雕塑。五四廣場之名源于“五四運動”,爆發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便是青島主權問題,可見其建設與命名具有濃重的歷史傳承色彩。其標志性雕塑“五月的風”,高達30米,直徑27米,重達500余噸,是我國最大的鋼質城市雕塑。“五月的風”以螺旋上升的風為造型,以火紅的紅色為色調,形成騰空而起的“勁風”形象,極具視覺張力,動感十足,充分表現出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基調和蓬勃向上的民族力量,已然成為了新世紀青島的標志性景觀之一。
第二,重源于生活,應走進公眾,何須高于生活;民俗有言云:“藝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竊以為,公共藝術創作確應源于生活當中,從公眾自身與平凡生活中摘得具有代表性的只言片語加以藝術化。此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藝術作品,當屬位于深圳少兒圖書館附近園嶺社區公園內的一組群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叫做“深圳人的一天”。其創作故事亦頗具趣味,藝術家們在是在1999年11月29日這一天當中,在深圳隨機選擇了18位不同行業的普通人,并把他們作為模特進行翻模,繼而創作為雕塑。其中有打工妹、中學生、退休老人、兒童、醫生、工人、設計師等,雕像與真人幾乎完全一致。此外,每個雕像旁都有一個銘牌,記錄了該人物的真實資料。由此可見,這座群雕作品意在追求與公眾生活的貼近乃至完全真實,富含著深刻的意味。相信每一位看到它的人,都會為之駐足、沉思與驚嘆。然此處所謂之“何須高于生活”,意為不必刻意追求高于生活,并不是說不需要高于生活,乃是指拋卻“為賦新詞強說愁”之意。事實上,刻意地拔高層次,一味地追求審美,未必就適宜公共藝術之創作,也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其公共性。
綜上所述,城市公共藝術創作之亂象源于對公共藝術屬性的認識不清,更深一步講則是源于對城市與公眾的部分忽略。因此,在我國的城市化建設過程當中,應該充分重視公共藝術的精神內涵,應認識到它并不僅僅是用來美化城市的工具或者藝術作品,更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乃至民俗生活之內涵,記錄著這方土地上人們的智慧與勤勞。
【參考文獻】
[1]翁劍青.公共藝術的觀念與取向:當代公共藝術文化與價值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孫振華.公共藝術時代[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3
[3]周成璐.公共藝術的邏輯及其社會場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4]王中.公共藝術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