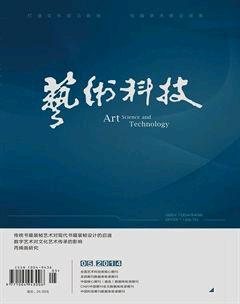舞者表演舞蹈作品的綜合能力
殷勤
摘 要:舞者是表演實踐的主體。舞者既受作品的制約,但又是編導構思的被動實現者,具有再創造的主觀能動性。舞者作為對舞蹈編排藝術構思的創造性舞臺體現,應具備綜合能力。
關鍵詞:舞者;舞蹈作品
舞蹈藝術是一種技術性極強的藝術門類,優秀的舞者,首先應具備較高的身體素質、較好的體形條件和舞蹈技術能力,這是舞蹈表演的基礎。舞蹈技術不是舞蹈的一切,舞者即使圓滿完成了技術技巧動作,也還不能完全達到舞蹈表演最終目的。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方面,即藝術表現力的問題。舞蹈是一種刻畫人物,表達事物的表演藝術,是由人物的思想通過肢體語言來表達情感的,舞者的一招一式都包含著人物細膩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鮮明的性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自身內部的矛盾沖突,都體現了人物的交流和情感。舞者表演一部作品所需要多項綜合的表演技巧和創造能力。它包括對外部形象設計與內部情感的體驗和創造;舞蹈風格與特色的把握;舞蹈節奏與韻律的感覺;舞蹈技術與造型的完成;舞蹈動作的表情與交流意識的表現等等。舞蹈是用人體表現人類心靈深處的感情和感受,舞蹈本身就是一種用“情”帶“動”,用“動”抒“情”的藝術表現形式。舞者的生活積累,思想文化素質是基礎,以及對音樂的感悟,它直接關系著舞者對角色理解、體驗的深淺。舞者觀察生活時要有效地捕捉形象,藝術實踐中就會更加有效地塑造形象。就會多一些主動性,少一些盲目性。在舞蹈作品的過程中,強調外部動作必須建立在準確的內心情感的基礎上,內心情感又要依靠外部技巧,內外相結合,準確的外部動作不單起到表達情感,塑造形象的作用,還起到誘發情感,孕育情感,穩定情感,推動情感發展的作用。舞蹈的表演性同樣有很復雜的技巧。舞蹈者的任務是以其掌握的舞蹈動作、造型和技巧能力,結合音樂等藝術手段,將作品的思想內容轉化為可視可感的舞蹈形象。舞者是表演實踐的主體。舞者既受作品的制約,但又是編導構思的被動實現者,具有再創造的主觀能動性。舞者作為對舞蹈編排藝術構思的創造性舞臺體現,應具備綜合能力。加上舞者身體技能的要求十分嚴格,不經長期艱苦的基本訓練,就無法進入創造實踐。舞蹈的技術技巧的訓練,與一般身體鍛煉不同,因為舞蹈動作必須負荷思想、傳達感情、塑造性格,為表現作品蘊含的主題服務。因此,在舞蹈作品中,作為手段的技術,只有在進行真正的藝術創造過程中才能顯示出它的價值。
舞者的表演,要經歷一個由外到內、再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的過程。舞者須先學習掌握某一角色的動作、姿態等外部技術后,再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體驗具體人物的心理活動并把握其個性特點,給身體動作(技巧)以內心依據,塑造有血有肉的豐滿的藝術形象。舞者“神”是通過“形”來體現的,完全脫離“形”的“神”,是空幻的;而單純的形似,則會使舞蹈形象蒼白無力。一個成熟的舞者在創作角色時,總是要求自己形神兼備。舞者表演的作品體現了情感世界,只有將情感融入每個動作中,才能賦予舞蹈以生命。舞者只有將真摯的感情融入每一個舞蹈動作之中,以心造舞、以舞傳情,作品才具有感染力。舞者通過內心、表情、眼神、動作、音樂、造型和各種技巧以及舞者的文化素養、生活閱歷等綜合這些才能完整展現人物的思想感情才能表演出真正的舞蹈作品。3 災異預兆的原因
《左傳》紀實,史家仍保留了巫卜文化中的天道神職職能,史官仍然擔負著占卜和祭祀等活動,“太史也,實掌其祭”;“祝史矯舉以祭祀”;“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晉侯筮之,史曰:‘吉”。“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春秋時期,對“德”和“禮”的維護,關系著國家的興衰和歷史人物的命運,違德和失禮都會遭到“天”的懲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侯”。在實錄原則和理性意識的影響下,史官記錄的預兆并非憑空想象,其憑借豐富的知識和對社會形勢的深刻了解做出符合社會現實的預測,抑或是記錄歷史事實的非同時性。據程水金先生推測《左傳》成書于伐齊、分晉前后,公元前370幾年,加之《左傳》是對春秋時期歷史事實的記載,預兆所顯示出來的在真實性也是可靠的。[4]
晚清社會自然災害頻發,《聊齋志異》中的自然災害多具有現實性,“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的地震是歷史上有名的“郯城大地震”;“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水災;“丁亥年七月初六日”的夏雪等。明末清初鬼神迷信思想盛行,文人多談鬼神, 蒲松齡又酷愛讀書,涉獵廣泛,尤其喜歡文字詼諧、內容奇詭荒誕的作品。作者通過描寫志怪、荒誕之事,表達個人的理想和愿望。[5]蒲松齡大半生在縉紳人家游學,坐館,孤獨落寞,其才華橫溢,但是終究不得志,抱負不得施展,其通過對志怪世界的刻畫,自由書寫,不受拘束,不能不說也是作者對自由的向往和對理想的渴望。[6]作者筆下的志怪亦有對黑暗社會下暗示的反映,反映了貪官污吏諂上媚下,強盜劣紳傾軋百姓,賄賂成行等社會丑惡現象,通過對鬼怪世界的刻畫懲惡揚善,伸張正義;作者作為讀書人一生不得志,其對科舉制度下的弊端也進行了嚴厲批判和揭露。
災異預兆源于早期巫卜文化,史官保留了巫的占卜祭祀職能,在史書實錄的原則和史官理性意識影響下,史傳文學《左傳》中的災異預兆是為史實敘事服務,其虛幻和荒誕性最終是服務于現實性。不同于史傳文學的實錄,志怪小說《聊齋志異》中的災異預兆多具有荒誕戲謔性,其表達了作者的個人思想感情和對黑暗現實社會的憤慨。
災異預兆是一種預敘的方式,作品中通過對災異預兆,暗示了后面的國家興衰、人物命運、世事變化;故事結構的展開以災異預兆為線索,使得故事的敘述脈絡更加清晰,結構更加完整;采用大量的災異預兆,使得故事的內容更加充實豐富;災異預兆亦豐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左傳》記載各種災異怪誕之事,使得史傳文學在理性視野下兼有怪誕離奇。史傳文學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通過對災異怪誕之事的記載,使得歷史人物的興衰成敗與際遇起伏充滿奇異色彩,增加了史傳文學的文學性。《聊齋志異》記載各種災異離奇事情,增強了作品的浪漫主義色彩。
參考文獻:
[1] 杜預注《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0:18081809.
[2] 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0.
[3] 杜預注.十三經注疏本《春秋左傳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19211922.
[4] 程水金.中國早期文化意識的嬗變[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342.
[5] 張進德,王景曉.論《聊齋志異》中的夢[J].河南周口: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8,25(3):23.
[6] 劉艷玲.《聊齋志異》夢創作類型及意蘊摭談[J].山東青島:東方論壇,2009(6):59.
作者簡介:趙慧玲,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魏晉文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