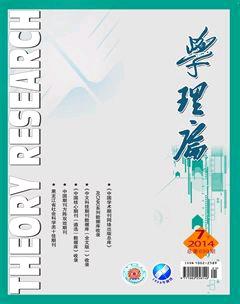《一九四二》改編得失談
羅閃
摘 要:電影與文學(xué)是兩種表達(dá)方式與接受形式截然不同的藝術(shù),但卻都在通過敘事反映人類的思想和情感。兩者獨(dú)立發(fā)展,卻又始終互動(dòng),電影改編文學(xué)的實(shí)踐突出地體現(xiàn)著文學(xué)與電影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一九四二》的改編成功地實(shí)現(xiàn)了紀(jì)實(shí)散文向電影劇本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并對(duì)原作的廣闊歷史保持了忠實(shí),但改編電影不是原作的影像復(fù)制品,電影改編更需要超越。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性;電影性;忠實(shí);超越
中圖分類號(hào):I247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4)21-0103-02
馮小剛的新片《一九四二》是2012年國(guó)內(nèi)文學(xué)改編電影作品中的一部佳作。這部電影改編自劉震云的短篇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是一部結(jié)構(gòu)散文化的紀(jì)實(shí)性質(zhì)的文學(xué),其本身是不合適改編電影的,但劉震云卻用自己對(duì)小說的深刻把握結(jié)合自己的編劇經(jīng)驗(yàn)成功地將這樣一部沒有任何劇情、人物,結(jié)構(gòu)松散的紀(jì)實(shí)文學(xué)改編成了一部非常忠實(shí)于原著精神的電影劇本。以下筆者通過對(duì)這部影片改編得失的分析,對(duì)電影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做出考察。
一、得:文學(xué)與電影的忠實(shí)轉(zhuǎn)化
《溫故一九四二》是作者通過對(duì)經(jīng)歷過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災(zāi)的許多人物的采訪以及翻閱大量相關(guān)的歷史資料后寫成的,主要內(nèi)容是對(duì)有關(guān)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災(zāi)的許多的歷史現(xiàn)象的陳述,以及對(duì)這一段歷史的反思。作者以一種紀(jì)實(shí)的風(fēng)格用平實(shí)的文字挖掘了那段關(guān)于“吃的問題”的,被埋沒的歷史,并站在民眾的角度反思了那段歷史,提出了“寧肯餓死當(dāng)中國(guó)鬼呢?還是不餓死當(dāng)亡國(guó)奴呢?”[1]3的問題。馮小剛被這部小說所打動(dòng)的地方就在于這部小說所挖掘出來的那段令人震驚卻被人埋沒、不愿提起,不為今人所知的歷史的真實(shí),以及作者審視那段歷史的獨(dú)特角度與反思。這部作品本身具有很好的歷史價(jià)值和歷史反思的深刻性,因而在文學(xué)改編電影的忠實(shí)性問題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從觀眾的接受心理角度來看,讀過小說的人看電影往往是出于一種還原想象的心理欲求,而不是想去看導(dǎo)演對(duì)原作解讀的一家之言;沒讀過小說的觀眾則多是想通過電影管窺原著的風(fēng)貌,而不想被導(dǎo)演和編劇的篡改所誤導(dǎo)。另一方面,這恰恰是采用文學(xué)來改編電影的原因和意義所在。文學(xué)可以反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而電影則更具有廣泛的社會(huì)影響力,電影與文學(xué)始終存在著媒介上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電影借助于文學(xué)改編,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題材和視角;而通過電影,文學(xué)的記錄和沉思也將得到更廣泛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因此,對(duì)于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電影與文學(xué)之間的這種媒介轉(zhuǎn)換更強(qiáng)調(diào)忠實(shí)性。
喬治·布魯斯東說:“小說家和電影導(dǎo)演的意圖是相同的,都是讓人們?nèi)タ匆姡≌f家讓讀者通過頭腦的想象來看,導(dǎo)演讓觀眾通過肉眼的視覺來看。而視覺形象所造成的視像與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兩者間的差異,就反映了小說和電影這兩者手段之間最根本的差異。”[2]8歷史總是復(fù)雜多變而又匆匆過去,相對(duì)于影像而言,文字更便于記錄歷史的復(fù)雜面貌;而電影作為造夢(mèng)工廠,能夠?qū)崿F(xiàn)許多我們?cè)诂F(xiàn)實(shí)中已經(jīng)不存在,或無法實(shí)現(xiàn)的景象,因而它更善于還原歷史。因此對(duì)于《溫故一九四二》的改編,有豐富編劇經(jīng)驗(yàn)的作者選擇了通過畫面還原歷史現(xiàn)場(chǎng),而沒有采用如小說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紀(jì)實(shí)回憶。小說可以以人物的行動(dòng)為主講故事,也可以以人物的思維為主談思想,而電影則主要依靠通過人物的行動(dòng)來講故事。因此在還原歷史的改編中,需要將原小說中平白簡(jiǎn)述的內(nèi)容加以虛構(gòu)擴(kuò)展,轉(zhuǎn)化為具體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們的行動(dòng)。小說中的深思則只能通過對(duì)人物的行動(dòng)和臺(tái)詞的具有表現(xiàn)力的設(shè)計(jì)來暗示性地傳遞給觀眾。因此在《一九四二》的改編過程中,作者虛構(gòu)了范財(cái)主一家、平民瞎鹿一家以及信基督的小安等在那一段歷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形象,然后將小說中平鋪直敘的歷史現(xiàn)象提煉擴(kuò)展為生動(dòng)的故事情節(jié),還原到了這些具體的人物身上。通過人物的行動(dòng)和對(duì)話,原小說中作者站在百姓角度審視這段歷史的感觀,通過畫面和故事的方式更直觀地傳遞給了觀眾。
電影劇本是電影創(chuàng)作的第一步,也是電影創(chuàng)作最關(guān)鍵的一部,電影劇本的故事框架不僅直接影響著拍攝的畫面內(nèi)容和效果,而且對(duì)后期影片剪輯的蒙太奇思維形成一定的制約,因此文學(xué)改編電影,最關(guān)鍵的步驟在于文學(xué)改編電影劇本的過程。劉震云以自己對(duì)自己作品的了解以及自己的編劇的經(jīng)驗(yàn),成功地將原不可能呈現(xiàn)為畫面的文學(xué)作品實(shí)現(xiàn)了創(chuàng)造性且忠實(shí)的轉(zhuǎn)化,這為這部電影的成功奠定了基礎(chǔ)。而在影片的拍攝階段,導(dǎo)演為了使電影畫面的敘事語(yǔ)句更為有力,更好地呈現(xiàn)歷史的真實(shí)感,電影中人物的衣著、道具都參考了那段歷史留下了的照片;演員每天挨餓以傳達(dá)更真切的感覺;龐大的群演群體調(diào)度形成了壯觀的歷史場(chǎng)面;飛機(jī)狂轟亂炸場(chǎng)面的則采用近距離現(xiàn)場(chǎng)拍攝,畫面效果非常真實(shí)震撼。如此,最終電影畫面的視覺沖擊力和音畫配合形成的震撼效果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小說中平淡描述的歷史現(xiàn)象以驚心動(dòng)魄的真實(shí)場(chǎng)面生動(dòng)地再現(xiàn)在了觀眾的眼前,使觀眾更加直觀真切地感受了那段歷史的悲慘與沉痛。在后期的剪輯創(chuàng)作中,電影敘事將兩條故事線索交替關(guān)聯(lián),營(yíng)造了小說原作中宏闊的歷史視野。敘事進(jìn)程中將第一條線作為主線,將范財(cái)主這個(gè)人物貫穿了整部影片,從而實(shí)現(xiàn)了作者在小說中所采用的站在平民的角度看歷史的獨(dú)特視角。馮小剛以冷靜、克制的鏡頭盡量的將原作中那些打動(dòng)了他、引人深思的東西客觀、完整地呈現(xiàn),最終作品達(dá)到了“看了原作需要去看電影,而看了電影則無需再去看原作”成功效果。這是將這樣一部并不適合電影表現(xiàn)的直陳而又瑣碎,思考多于故事的文學(xué)作品成功轉(zhuǎn)化為生動(dòng)的電影形象,并達(dá)到了對(duì)原作內(nèi)涵、風(fēng)格的忠實(shí)傳遞的一部成功之作。
二、失:文學(xué)改編電影的目標(biāo)——超越
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這部影片雖然以更加形象的方式忠實(shí)地再現(xiàn)了原文學(xué)作品中的內(nèi)容、風(fēng)貌,影像化的歷史再現(xiàn)非常具有沖擊力、渲染效果,讓觀眾的心靈通過電影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但在改編的過程中,由于導(dǎo)演沒有更主動(dòng)地去干預(yù)作品,保持了歷史的客觀性與復(fù)雜性,但使得影片的敘事無主題和敘事動(dòng)機(jī)可循。完全客觀地呈現(xiàn)一段不包含任何評(píng)價(jià)的歷史,這樣的客觀敘事中缺乏一種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樣能夠引發(fā)人的深思的力量。《一九四二》的劇本主要由劉震云本人依照他原本創(chuàng)作小說時(shí)的意圖和認(rèn)識(shí)而改編,作家有他自己站的高度,也有他視野的局限,導(dǎo)演拍攝文學(xué)改編電影作品,是站在作家的肩膀上看問題,其思考的起點(diǎn)和把握的高度應(yīng)該更高于作家,而不應(yīng)僅僅讓自己創(chuàng)作的電影完全忠實(shí)與作家的意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忠實(shí)了原作的哲學(xué)意蘊(yùn),但表現(xiàn)出來的卻是李安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間的更宏闊的視野。
《溫故一九四二》里面所能呈現(xiàn)的內(nèi)容,能夠引發(fā)人深入思考的東西很多:從一開篇時(shí)對(duì)歷史的談?wù)摻o人的啟發(fā):歷史本是由人民而組成的,但歷史卻不是人民的歷史的提出;到文章主體內(nèi)容對(duì)“吃的問題”的表現(xiàn),與我們現(xiàn)在這個(gè)豐衣足食卻糧食浪費(fèi)極度嚴(yán)重的社會(huì)的關(guān)聯(lián);再到文章中間部分論述的一種國(guó)家主義的觀念:“一塊陣地上死了一個(gè)逃亡的百姓,那這個(gè)陣地還是中國(guó)的,死了一個(gè)兵那這塊陣地就不是中國(guó)的了。”我們都知道,一塊土地先有了人民才有了國(guó)家,才有了軍隊(duì),軍隊(duì)抗戰(zhàn)不是為了保衛(wèi)國(guó)家的榮譽(yù)而是為了保護(hù)人民的安危。但這種打著保家衛(wèi)國(guó)旗號(hào)看似有理,而坑害百姓的觀念不光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在我們現(xiàn)在社會(huì)上仍可窺見;結(jié)尾對(duì)“寧肯餓死當(dāng)中國(guó)鬼呢?還是不餓死當(dāng)亡國(guó)奴呢?我們選擇后者”的問題的探討——當(dāng)人民不被認(rèn)可為人時(shí),他們就要開始行使人的本能。原小說可以進(jìn)行更深入拓展的思考很多,然而導(dǎo)演并沒有從自己的角度深入下去,影片的改編除了忠實(shí)地呈現(xiàn)了文學(xué)敘事中的歷史和作者雜陳的討論,沒有從導(dǎo)演角度上的更深入追尋。最終導(dǎo)致影片中除了客觀的歷史還原所呈現(xiàn)的悲慘情境和人情悲喜,沒有突出的能夠引起觀眾深入回思的點(diǎn)。影像的語(yǔ)言本身就是含混而復(fù)雜的,因而更需要導(dǎo)演的引導(dǎo)與掌控。如喬治?布魯斯東所說:“攝影機(jī)不能充當(dāng)托爾斯泰,也不能充當(dāng)喬伊斯,它并不能很好地處理主要人物的蕪雜狀態(tài),也不能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作全景式的關(guān)注。它也不能解剖思維在言語(yǔ)的復(fù)雜錯(cuò)綜之中的隱秘生命。”[2]69然而馮小剛卻放棄了介入鏡頭的機(jī)會(huì)。《一九四二》將極度慘烈的歷史以克制不煽情的方式表達(dá)出來,并且?guī)в辛艘唤z諷刺的幽默,本是表現(xiàn)這樣的災(zāi)難提出的一種獨(dú)特的方式,卻缺乏更深入的主題的引導(dǎo),使這部本可以闡發(fā)更多引人深思的歷史大片,僅僅呈現(xiàn)為了一部還原歷史的記錄文獻(xiàn)。
從這部作品改編的遺憾之處來看,電影與文學(xué)畢竟是各有優(yōu)勢(shì)的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文學(xué)為電影提供了豐富的視野和藝術(shù)借鑒,但電影不能成為文學(xué)的影像化附庸,電影是站在文學(xué)的肩膀上發(fā)展起來的,因此電影改編文學(xué)更需要的是超越。《一九四二》這部馮小剛醞釀了18年、籌備9個(gè)月、拍攝135天、制作8個(gè)月、耗資2.1億的電影,傾注了導(dǎo)演許多的心血,作為一部以與眾不同的角度,勇敢地回顧災(zāi)難歷史的嚴(yán)肅大片,這在國(guó)內(nèi)的商業(yè)電影中是少有的,這種勇氣和影片的歷史意義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但作為一部文學(xué)改編電影,我們還需思考,在表現(xiàn)人類精神世界的領(lǐng)域,電影要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超越文學(xué)。
參考文獻(xiàn):
[1]劉震云.溫故一九四二[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
[2][美]喬治·布魯斯東.從小說到電影[M].高駿千,譯.北京: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