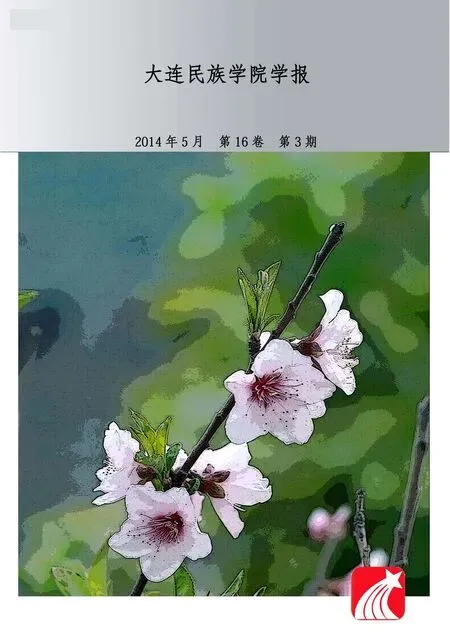不同放牧梯度上草原群落植物功能群的結構組成及其變化
道日娜,烏云娜,林 璐,3,霍光偉,張慶昕,賈子金
(1.內蒙古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21;2.大連民族學院
環境與資源學院,遼寧大連116605;3.遼寧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遼寧大連116029)
草原生態系統是中國陸地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類型之一,具有巨大的生態功能價值[1]。近年來,功能群概念的引入和功能群的劃分,為研究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功能和維持機制注入了新的活力[2-3]。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尺度來對植物功能群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結果有不同的針對方向和目的,使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更全面的理解復雜的陸地生態系統,這也大大拓寬了植物功能群的應用范圍。
目前,功能群多樣性、功能群豐富度及其類型已成為生態學和保護生物學新的熱點問題[4]。對不同載畜率水平下內蒙古荒漠草原功能群物種組成及功能多樣性變化特征的研究表明:灌木類和多年生禾草特性比較穩定,多年生雜類草隨著載畜率的增加,物種組成下降幅度較大,使得群落結構和組成隨載畜率的增加趨于簡單化。豐富度指數和多樣性指數在重牧區最低[5]。一年生、二年生和旱生植物功能群在不同退化階段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優勢地位,對群落生態功能的發揮和維持起著重要作用。草地退化過程中不同群落的組成變化是物種適應性和群落環境變化相互作用的結果,而物種、功能群組成的變化基本反映了草地生態系統退化、群落結構簡單化和環境基質穩定性減弱等一系列植被與生態環境變化的趨勢[6]。李里認為,物種豐富度和物種多樣性指數在中度退化草地最高,輕度退化草地次之,重度退化草地最低;群落生產力則在輕度退化草地最高,中度退化草地次之,重度退化草地最低,且與物種總數和多樣性指數無顯著相關性。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植物功能群的變化不盡相同,但功能群生物量與功能群內植物種數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7]。
功能群自提出以來,已經在功能群-干擾、功能群-全球變化及功能群-多樣性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8]。國內外相關研究更多的主要體現在自然或人為干擾背景下生態系統中單一功能群組成及動態變化,其研究結果尚難以說明植物功能群及其組成對生態系統過程的相對重要性,而且對功能群間的相互作用及其群落功能和穩定性的維持機制尚不太清楚,特別是對于自然生態系統運作機制的解釋還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9]。干擾與植被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干擾對物種的進化意義和干擾對植被過程的調整作用,植物種對干擾的適應表現在繁殖、物候、形態、生理等方面。
本研究通過探討放牧梯度上生活型和水分生態型植物功能群的變化,闡釋草原退化的生態演替過程及其機制,為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與重建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域概況
以蒙古高原東部呼倫貝爾草原的克魯倫河流域草原為研究對象。研究區位于東經115°31'~117°43',北緯 47°36'~49°50',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半干旱氣候,年均降水量200~300 mm,年平均氣溫為-5~2℃,≥10℃的年積溫2 320℃,持續日數125 d左右。地帶性土壤類型主要為栗鈣土。群落優勢種為克氏針茅(Stipa krylovii)、羊草(Leymus chinensis)、糙隱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等。
2 研究方法
2.1 樣地設置
在研究區采用空間演替系列代替時間演替系列的方法,利用GPS定位,以具代表性的克氏針茅草原群落的建群種變化為依據選取輕度放牧、中度放牧、重度放牧三個實驗樣地(見表1)。參考王明玖和馬長升[10]、鄭陽[11]等對內蒙古典型草原載畜量的研究方法,結合實地調查結果,估算出三個樣地的載畜量分別為0.62,1.55,2.79羊·hm-2。輕度放牧樣地為圍欄區,封育時間為2001年,季節性放牧,在生長季不受人為干擾;中度放牧樣地為輪牧活動區,植物得以恢復生長;重度放牧樣地為自由放牧區,常年受到放牧壓力影響。

表1 研究樣地基本特征
2012年7月,在各個樣地選擇典型地段設置一條50 m樣線,間隔5 m做1 m×1 m的樣方,記錄10個樣方內的植物種類組成、株叢數、種群的蓋度(Penfound法)、平均高度和最高高度,采用刈割法獲取種群的地上部現存量,80℃下烘干24 h,獲得干物質量。
2.2 植物功能群的類型和劃分
依據物種的生態生物學特性,將群落物種劃分為生活型和水分生態型兩種不同類別的功能群。生活型功能群包括:(1)一、二年生草本(Annual or biennial herb);(2)多年生雜類草(Perennial forbs);(3)多年生禾草(Perennial grasses);(4)灌木、半灌木類(Shrub,subshrub)。水分生態型功能群包括:(1)旱生植物(Xerophyte);(2)中旱生植物(Meso-xerophyte);(3)旱中生植物(Xero-mesophyte);(4)中生植物(Mesophyte)。
2.3 數據分析
(1)綜合優勢比
采用(SDR4)計算樣方中各物種的綜合數量指標:

式中,C'為相對蓋度,H'為相對高度,D'為相對密度,W'為相對生物量(干重)。
(2)物種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分析采用Patrick豐富度指數(Pa)和香農-韋納(Shannon-Weaver)指數(H'):

式中,S為物種數,Pi為各種植物的相對生物量,i代表第i個物種(其中i物種在整個樣帶內的平均優勢度為i物種在該樣帶所有樣方內的優勢度之算術平均值)。
(3)物種均勻度指數
均勻度采用Pielou均勻度指數(E):

式中,H'為Shannon-Wiener指數,S為物種數。
3 結果與討論
3.1 不同放牧梯度上群落物種組成的變化
不同放牧梯度上的種類組成與出現頻率見表2。

表2 不同放牧梯度上的種類組成與出現頻率

續表
表2表明,在克魯倫河流域物種組成有32種,且不同放牧壓力對物種組成結構影響較大,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物種組成呈遞減趨勢,輕牧、中牧、重牧下物種數分別為23,18,10種。輕牧狀態下出現頻度較高的植物有羊草和阿氏旋花,其次為克氏針茅、星狀刺果黎、尖頭葉藜,出現頻度較少的是乳白花黃芪、披針葉黃華、豬毛菜、燥原薺;中牧出現頻度較高的植物有糙隱子草、尖頭葉藜,其次是蒙古蔥、黃囊苔草,出現頻度較少的是狹葉錦雞兒;重牧出現頻度較高的植物有黃囊苔草、多根蔥。不同物種在不同放牧梯度上的變化規律亦不同,呈遞減趨勢的物種有克氏針茅、羊草、黃蒿、星狀刺果藜,呈增加后降低的物種有冰草、糙隱子草、細葉蔥、蒙古蔥、冷蒿、豬毛菜、尖頭葉藜等,呈增加特征的物種則有狗尾草、多根蔥、絲葉蒿、黃囊苔草。
同一科物種在不同放牧梯度下出現的頻度差異較大,禾本科在輕度、中度、重度放牧下呈現頻度最高,依次為克氏針茅、羊草,其次為糙隱子草、冰草,頻度最低的是狗尾草;藜科植物的變化特征為星狀刺果藜頻度最高,其次是豬毛菜、星狀刺果藜,頻度最低的是豬毛菜;百合科植物均在中度放牧下出現頻度較高,其中頻度最高的為細葉蔥;菊科物種則以絲葉蒿在重度放牧下出現頻度最高;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莎草科的黃囊苔草遞增明顯,旋花科的阿氏旋花遞減明顯;莧科的尖頭葉藜則表現明顯的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趨勢。
3.2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的結構組成
不同放牧梯度上各個功能群的物種數及其百分比見表3。

表3 不同放牧梯度上各個功能群的物種數及其百分比
從各生活型功能群的種類組成看,多年生禾草在輕牧、中牧和重牧中物種數分別為4,3,2,其中糙隱子草為共有種;多年生雜類草共20種,輕牧階段有14種,中牧下10種,重牧中3種,其中黃囊苔草為共有種;一、二年生草本共4種,其中共有種為尖頭葉藜和豬毛菜。種數最多的是多年生雜類草,在各放牧梯度上均表現出最大值,其次是多年生禾草,且多年生雜類草和多年生禾草在重牧區迅速降低;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在各放牧梯度上分布均勻;而灌木、半灌木功能群種數最少且基本保持不變。
從水分生態功能群的物種結構看,中生植物共2種,中旱生植物共11種,旱中生植物共2種,旱生植物共17種。物種數最多的是旱生植物,其次是中旱生植物,第三是旱中生植物,最小的是中生植物。旱生、中旱生、旱中生植物的種數由輕牧到重牧均逐漸降低,而中生植物隨放牧梯度的增加呈上升趨勢。
3.3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綜合優勢比的變化
3.3.1 不同放牧梯度上生活型功能群綜合優勢比的變化
在不同放牧梯度上,一、二年生草本、多年生雜類草、多年生禾草及灌木、半灌木各功能群的綜合優勢比存在較大差異(如圖1)。

圖1 生活型功能群綜合優勢比的變化
由圖1可知,從輕牧到重牧,灌木、半灌木的綜合優勢比逐漸升高,依次為0.033 3,0.027 6及0.067 5,灌木、半灌木在輕牧和中牧間差異不顯著(p>0.05),但兩者與重牧差異顯著(p<0.05);多年生禾草的綜合優勢比呈相反趨勢,其優勢比依次為:輕牧0.6675、中牧0.593 5、重牧0.139 8,重牧與輕牧、中牧差異性顯著;多年生雜類草的優勢比在重牧下達到最高,數值為0.697 8,與中牧(0.2531)、輕牧(0.2632)差異顯著;一、二年生草本的優勢比在中牧階段最高,為0.125 8,與輕牧區(0.0383)差異顯著,與重牧區(0.0948)差異不顯著。
3.3.2 不同放牧梯度上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綜合優勢比的變化(如圖2)

圖2 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綜合優勢比的變化
由圖2可知,旱生植物在中牧階段的優勢比最高,為0.754 4,輕牧為0.600 4,重牧為0.485 7;而中旱生植物在中牧階段的優勢比最低,為0.143 4,在重度最高,為0.468 9;旱中生植物隨著放牧梯度的增強,優勢比呈現逐漸降低的趨勢,在輕牧階段最高,為0.037 8;中生植物在不同放牧梯度上優勢比的變化與旱生植物相同,在中牧階段最高,為0.072 8。
3.4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組成的變化
3.4.1 不同放牧梯度上生活型功能群組成的變化
生活型的差別反映了群落的生境,特別是小生境、小氣候的變化[12]。不同放牧梯度上組成群落的各生活型種數百分比的變化如圖3。

圖3 群落生活型功能群組成的變化
由圖3可知,不同放牧強度下,植物生活型功能群組成基本一致,均含有四個功能群。灌木、半灌木所占百分比在重牧區中最高,為17.8%,在中牧區為9.1%,輕牧下為7.3%。中牧與輕牧、中牧與重牧差異性不顯著(p>0.05),輕牧、重牧差異性顯著(p<0.05);多年生禾草所占百分比在輕牧、中牧、重牧區分別為22.4%,20.2%,21.5%,三者差異性均不顯著。多年生雜類草在輕牧區所占比例最高,為59.1%,其次是中牧區,為52.9%,最次是重牧區,為32.2%。輕牧、中牧差異性不顯著,重牧與中牧、重牧與輕牧差異性顯著。一、二年生草本所占百分比呈遞增趨勢,在輕牧、中牧區分別為11.2%,17.8%,輕牧、中牧差異性不顯著,在重牧區占28.5%,中牧、重牧差異性顯著。
3.4.2 不同放牧梯度上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組成的變化
植物的水分生態類型是依據植物對生態環境中水分狀況的適應性而劃分的。不同放牧梯度直接影響著草原群落的蓋度,進而影響水分生態環境。群落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組成的變化如圖4。

圖4 群落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組成的變化
由圖4可知,隨著放牧梯度的逐漸增強,旱生植物功能群種數的百分比基本保持不變,中旱生植物在中度放牧中所占比例最高,而旱中生植物種數百分比隨放牧強度的增加呈現先增強后消失的特征,中生植物種數的百分比隨放牧強度的增強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旱生植物在輕牧、中牧及重牧區所占比例分別為49.10%,43.33%及50.00%,各放牧梯度間差異不顯著(p>0.05)。中旱生植物在輕牧、中牧及重牧區分別為31.60%,37.78%及32.22%,并且各放牧梯度間差異不顯著。旱中生植物在中牧區占11.66%,與重度區(占0.00%)差異顯著(p<0.05),而與輕牧區(占8.85%)差異不顯著。中生植物在輕牧下占10.44%,它與中牧、重牧所占百分比均差異不顯著,中牧(占7.22%)與重牧(占17.78%)差異顯著。
3.5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生物量的變化
3.5.1 不同放牧梯度上生活型功能群生物量的變化(如圖5)

圖5 生活型功能群生物量的變化
放牧梯度對于草地生產力具有決定性作用。由圖5可知,在生活型功能群組成中,多年生禾草占有絕對優勢,在輕牧區的生物量最大,為53.45%,并隨放牧梯度的加大而減少;多年生雜草在輕牧區所占比例最大,為40.78%;灌木、半灌木在各放牧區的生物量相近;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在輕牧區較少,中牧區和重牧區占明顯優勢。
3.5.2 不同放牧梯度上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生物量的變化(如圖6)

圖6 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生物量的變化
由圖6可知,旱生植物在輕牧區和中牧區占絕對優勢,在輕牧區生物量最大,為46.35%;隨放牧強度的加大,相對生物量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在中牧區和重牧區生物量依次為37.20%和16.45%;中旱生植物相對生物量在輕牧區最大,為47.46%,在中牧區和重牧區所占比例接近,分別為26.49%和26.03%;旱中生植物在重牧區未被統計,可能與選取樣地的局限性有關;旱中生植物和中生植物在各個放牧區的相對生物量均較少,所占比例分別為3.35%和3.80%。
3.6 不同放牧梯度上功能群和群落多樣性的變化
3.6.1 不同放牧梯度上功能群多樣性的變化
從輕牧到重牧,不同生活型功能群和水分生態型功能群的多樣性變化見表4。可以看出,生活型功能群中,多年生雜類草的豐富度指數隨放牧梯度加強而明顯減小,在輕牧區最高,為14;多年生禾草的均勻度指數在各放牧梯度上均較高,在中牧區最高,為0.77;多年生雜類草的多樣性指數隨放牧梯度的增加呈現減小趨勢,重牧區多樣性指數與輕牧區和中牧區有顯著性差異;多年生禾草的多樣性指數在重牧區最低,Shannon-Weaver指數為0.417 6,中牧區多樣性指數與輕牧區和中牧區有顯著性差異;而一、二年生草本與灌木、半灌木相同,隨放牧強度的加大而呈現遞增規律,并且輕牧區多樣性指數與重牧區有顯著差異。
水分生態型功能群中,旱生植物和中旱生植物的豐富度指數隨放牧梯度的增加呈現遞減趨勢,且在重牧區均勻度指數較高;中旱生植物多樣性指數在輕牧區最高,重牧區多樣性指數與輕牧區和中牧區有顯著性差異;旱生植物的多樣性指數在中牧區最高,輕牧區多樣性指數與重牧區有顯著性差異;中生植物多樣性指數隨放牧梯度的增強而增加。

表4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多樣性的變化
3.6.2 不同放牧梯度上群落多樣性的變化
群落的物種豐富度及多樣性是群落的重要特征。不同放牧梯度上群落多樣性及其相關關系見表5。可以看出,中牧下多樣性指數最高,為2.25,其次為輕牧區,為2.20,但二者不存在差異(p>0.05),重牧下多樣性指數最低,為1.95。重牧區多樣性與中牧、輕牧區有顯著性差異(p<0.05)。多樣性指數在中牧下最大,隨著放牧強度的加大,呈單峰式曲線變化特征,符合“中度干擾”假說,這與不同植物功能群在放牧退化演替過程中的消長變化密切相關。由于牧草在營養價值和采食難易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家畜具有擇食性,可顯著改變植物種間競爭格局、物種侵入或遷出以及群落組成。

表5 不同放牧梯度上群落多樣性及其相關關系
從輕牧到重牧,豐富度指數呈遞減趨勢,輕牧區豐富度指數最高,為18.00,三個放牧階段間均呈現顯著差異;均勻度指數呈遞增趨勢,在重牧區最高,為0.87,重牧與中牧條件下二者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輕度區為0.76,與中牧、重牧有顯著性差異。
4 結論
(1)不同功能群對草原退化的響應程度不同。植物生活型功能群中,多年生雜類草在輕牧、中牧區都占有明顯優勢,多年生雜類草的生物量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顯著減少,說明在群落植物功能群組成中,多年生雜類草的作用逐漸減弱,一、二年生草本在重牧區占有絕對優勢,使群落結構趨于簡單,生態系統穩定性變低;植物水分生態型功能群中,旱生植物在輕牧區、中牧區和重牧區均占有絕對的優勢。
(2)從植物功能群的地上生物量來看,生活型功能群組成中,多年生禾草占有絕對優勢,在輕牧區的分布量最大;多年生雜類草在輕牧區占有優勢,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在中牧區和重牧區較有優勢。水分生態型功能群中,旱生植物在輕牧區和中牧區占絕對優勢,隨放牧強度的加大,相對生物量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
(3)從物種多樣性的變化來看,多年生雜類草和多年生草本功能群多樣性指數隨放牧梯度的增加呈現減小趨勢,一、二年生草本與灌木、半灌木以及中生植物功能群多樣性,隨放牧強度的加大而呈現遞增規律。由輕牧到重牧,物種豐富度指數逐漸降低,而均勻度指數逐漸增加,Shannon-Weaver指數在中牧區最大,符合“中度干擾”假說。適度放牧是保護草原生物多樣性、維護放牧生態系統功能與健康的有效途徑。
[1]尹劍慧,盧欣石.中國草原生態功能評價指標體系[J].生態學報,2009,29(5):2622-2630.
[2]KOBRNER C H.Scaling from species to vegetation:the usefulness of functional groups[M]∥SCHULZE E D,MOONEY H A.eds.Ecosystem function of biodiversity.Berlin:Springer,1994,99:117-140.
[3] WILSON J B.Guilds,functional types and ecological groups[J].Oikos,1999,86:507-522.
[4]林麗.石羊河上游退化草地植物功能群特征研究[D].蘭州:甘肅農業大學,2007.
[5]焦樹英,韓國棟,趙萌莉,等.荒漠草原地區不同載畜率對功能群特征及其多樣性的影響[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6,20,161-165.
[6]馬建軍,姚紅.內蒙古典型草原區3種不同草地利用模式下植物功能群及其多樣性的變化[J].植物生態學報,2012,36(1):1-9.
[7]李里,劉偉.退化草地植物功能群和物種豐富度與群落生產力關系的研究[J].草地學報,2011,19(6):917-921.
[8]李榮平,劉志民,蔣德明,等.植物功能型及其研究方法[J].生態學雜志,2004,23(1):102-106.
[9]MC CANN K S.The diversity stability debate[J].Nature,2000,405:228-233.
[10]王明玖,馬長升.兩種方法估算草地載畜量的研究[J].中國草地,1994(5):19-22.
[11]鄭陽.內蒙古克氏針茅典型草原生態系統放牧管理優化模式研究[D].蘭州:甘肅農業大學,2010.
[12]王正文,邢福,祝延成,等.松嫩平原羊草草地植物功能群組成及多樣性特征對水淹干擾的響應[J].植物生態學報,2002,26(6):708-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