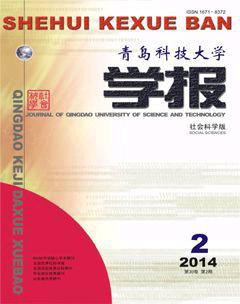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研究
任燕
[摘要]山東省正處于城鎮化水平迅速提高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階段,采用1978—2012 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探討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及產業結構演變的關系。通過建立協整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從實證角度研究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的相關性及因果關系。結果顯示,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和單項因果關系。
[關鍵詞]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372(2014)02-0018-0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andong province
REN Y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Shandong province is in the key stage on which its urbanization is improving quickly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12. We build the cointegration model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o study the dependency and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 changes of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singl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urban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ointegration analysis;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城鎮化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結果,反過來,其對產業結構優化也有重要影響。國內外學者從理論層面研究了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優化的互動關系。國外學者庫茲涅茨指出,產業的不同屬性是產業結構變動對城鎮化形成影響的原因[1]。錢納里在考察工業化發展進程時,發現城鎮化率與工業和服務業中的勞動力份額在變動上相似,指出工業化過程會帶來城鎮化現象[2]。之后,Krugman[3]、Porter[4]、Raco[5]、Kondo[6]分別從交易費用、空間經濟、要素流動、不完全競爭等角度進行研究,認為規模經濟決定經濟主體必然選擇在某一區位進行大規模生產,從而使經濟呈現出聚集格局。Lucas、Black強調人力資本在城市中聚集形成[7-8]。Murata認為城市中的工業和服務業加速了城鎮化的發展[9]。國內學者陳頤認為,工業發展需要集中,工業集中形成城市,因此工業化必然導致城鎮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研究”課題組認為產業結構變動首先作用于就業結構,然后影響到城鎮化水平[10]。曾芬飪指出城鎮化會優化第一產業,提升第二產業,帶動第三產業,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同樣會對城鎮化的發展起積極作用。李培樣和王利明認為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是城鎮化的動因,城鎮化則通過投資形成、投資導向和產業整合作用于產業結構。魏娟、李敏通過對江蘇省的實證研究認為,產業結構升級與城鎮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和單項因果關系,就業結構對城鎮化進程的促進作用更大[11]。李卉群認為,城鎮化進程與服務產業高度正相關,短期內城鎮化能推動服務產業的發展[12]。山東省正處于城鎮化水平迅速提高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階段,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的現狀
本文對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測度方法是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圖1顯示了山東省目前的城鎮化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山東省城鎮化率權威數據判斷,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基本與中國城鎮化水平持平,遠高于山東省所統計的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山東省雖然地處經濟發達的東部,但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率為52.43%,列全國第14名;人均GDP為51768元,列全國第10名。
圖11978—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及與中國和東部地區的對比
注: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等10個省市。
數據來源:圖1—圖4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及山東省1978—2012年統計年鑒
圖2顯示了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及產業結構現狀。山東省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2.46%上升到2012年的52.43%,同時,第一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33.3%下降到2012年的8.6%,產業結構逐步由以第一產業為主轉變為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
圖21978—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及三次產業產值比重(%)
第二和第三產業代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因此再對山東省和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如圖3所示,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明顯高于中國平均水平,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則滯后于中國平均水平。
圖31978—2012年山東省第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
及與中國的對比(%)
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就業結構發生互動關系的。如圖4所示,1978—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率、非農產業(第二與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三者保持了較為平穩的上升趨勢,但城鎮化率更接近于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而距離非農產業的產值比重則有一定的差距。山東省非農產業產值比重較高,呈上升趨勢,2000年后比重超過90%,但就業吸納能力不強,最高也剛剛超過60%。說明非農產業對人口向城鎮集中的消化能力不夠,導致產業結構對城鎮化帶動作用不大。
圖41978—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率和非農產業比重的對照圖
二、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實證分析
1.模型變量選擇
本文采用1978年以來的山東省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記為IND1、IND2和IND3)來體現山東省的產業結構。山東省的城鎮化率(記為UR)從數據的可得性和統一性出發。2000年之前統計數據不可得,可使用中國城鎮化率代替(因為由已知數據可知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中國城鎮化率基本相等),以保證能在更長的時間序列基礎上計量分析。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影響和數據的劇烈波動,所選擇的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分別記為 lnUR、lnIND1、lnIND2、lnIND3,相應的一階差分記為ΔlnUR、ΔlnIND1、ΔlnIND2、ΔlnIND3。為了定量研究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的關系,采用協整分析的方法,首先對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然后對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函數檢驗,最后對變量作 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13]。
2.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現象,模型首先對時間序列變量—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結構產值比重進行單位根的穩定性檢驗。采用 ADF 檢驗方法,使用 Eviews5.0 軟件對各變量的原序列與一階差分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結果見表1。
表1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單位根的ADF檢驗結果(1978—2012年)
變量 ADF值 檢驗形式
(C,T,L) 顯著水平下的檢驗結果
1% 5% 10%
LnIND1 -3.328956 (C,T,1) 不平穩(-4.262735) 不平穩(-3.552973) 平穩
(-3.209642)
△LnIND1 -3.938311 (C,0,1) 平穩
(-3.653730) 平穩(-2.957110) 平穩
(-2.617434)
LnIND2 -2.650695 (C,T,1) 不平穩(-4.284580) 不平穩(-3.562882) 不平穩(-3.215267)
△LnIND2 -3.770246 (0,0,2) 平穩
(-2.639210) 平穩(-1.951687) 平穩
(-1.610579)
LnIND3 ?1.963150 (0,0,1) 不平穩(-2.636901) 不平穩(-1.951332) 不平穩(-1.610747)
△LnIND3 -4.706844 (C,T,0) 平穩(-4.262735) 平穩(-3.552973) 平穩
(-3.209642)
LnUR -3.479993 (C,T,4) 不平穩(-4.296729) 不平穩(-3.568379) 平穩
(-3.218382)
△LnUR -3.685629 (C,0,0) 平穩
(-3.646342) 平穩(-2.954021) 平穩
(-2.615817)
說明:檢驗形式中的C、T和L分別表示截距、趨勢項和滯后階數。最優滯后期根據SIC準則確定
表1的檢驗結果表明,當置信水平為5%時,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是不平穩的,故不能簡單做回歸。但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均為一階單整,根據協整理論,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
3.協整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現象,對相關變量進行Johansen檢驗,判斷其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并進一步確定相關變量之間的符號關系,結果見表2。根據AIC最小準則,最優滯后期為滯后2期。Johansen協整檢驗的原假設是變量間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一行概率為0.0000,表明拒絕兩個變量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第二行概率為0.0042,表明拒絕兩個變量最多存在一個協積變量的原假設;第三行概率為0.1777,表明接受兩個變量之間最多存在兩個協積變量的原假設。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模型不存在謬誤回歸,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4.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協整理論,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時,各變量間的長期均衡及短期波動關系可以用誤差修正模型描述。協整關系反映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短期動態模型則反映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修正機制。建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三次產業產值比重之間的誤差修正模型,系數估計和檢驗結果見表3。根據AIC最小準則,最優滯后期為滯后2期。由于存在2個協積變量,對誤差修正模型系數的經濟意義的解釋較為復雜,因此直接用脈沖響應函數來說明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
表2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1978—2012年)
協整關系假設 跡檢驗特征值 臨界值(0.05顯著性水平) 概率值** 協整關系假設
None * ?0.696283 ?76.40003 ?47.85613 ?0.0000
At most 1 * ?0.565541 ?38.26696 ?29.79707 ?0.0042
At most 2 ?0.303359 ?11.59001 ?15.49471 ?0.1777
At most 3 ?0.000703 ?0.022495 ?3.841466 ?0.8807
說明:*表明在0.05的顯著水平上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MacKinnon-Haug-Michelis(1999)概率值
表3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VECM模型
(1978—2012年)
協整方程 協整方程1 協整方程2
LnUR(-1) ?1.000000 ?0.000000
LnIND1(-1) ?0.000000 ?1.000000
LnIND2(-1) -3.89462[-9.0018] ?5.60925
[11.8143]
LnIND3(-1) -0.83141[-4.1681] ?1.45308
[6.63834]
C ?14.42323 -29.58743
Error
Correction: D
(LnUR) D(LnIND1)
D(LnIND2) D
(LnIND3)
CointEq1 -0.03217[-0.5412] -0.51868
[-3.5653] ?0.47701
[3.9752] -0.51661
[-3.7654]
CointEq2 -0.04169[-0.8331] -0.36627
[-2.9910] ?0.314109
[.10983] -0.42242
[-3.6579]
D(LnUR(-1)) ?0.54266[2.5975] -0.15675
[-0.3066] -0.28011
[-0.6642] ?0.59313
[1.2301]
D(LnUR(-2)) ?0.08772[0.43645] ?0.48406
[0.98411] -0.31350
[-0.7727] -0.07605
[-0.1639]
D(LnIND1(-1)) -0.15734[-1.0658] ?0.215445
[0.5963] -0.32712
[-1.0977] ?0.583656
[1.7131]
D(LnIND1(-2)) ?0.000942[0.0057] -0.29104
[-0.7305] -0.36523
[-1.1114] ?0.482043
[1.2829]
D(LnIND2(-1)) -0.39957[-1.6115] ?0.242361
[0.3994] -0.30049
[-0.6004] ?0.717584
[1.2540]
D(LnIND2(-2)) -0.00214[-0.0082] ?0.044563
[0.0702] -0.85607
[-1.6364] ?0.787420
[1.3165]
D(LnIND3(-1)) -0.15534[-0.9660] ?0.445979
[1.1333] -0.35012
[-1.0786] ?0.262726
[0.7079]
D(LnIND3(-2)) -0.11062[-0.7790] ?0.295554
[0.8505] -0.49208
[-1.7169] ?0.144410
[0.4406]
C ?0.013733[1.4514] -0.08226
[-3.5526] ?0.018221
[0.9540] ?0.048210
[2.2077]
?R-squared ?0.444856 ?0.625737 ?0.671662 ?0.683095
?F-statistic ?1.682805 ?3.511034 ?4.295856 ?4.526591
?Log likelihood ?95.17683 ?66.53788 ?72.70017 ?68.41353
?Akaike AIC -5.261052 -3.471118 -3.856261 -3.588346
?Schwarz SC -4.757205 -2.967271 -3.352414 -3.084499
?Log likelihood ?350.4219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18.65137
?Schwarz criterion -16.26954
5.脈沖響應函數
由于誤差修正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因此在分析誤差修正模型時,往往難以直接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其他變量的影響,更常見的是利用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建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對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沖擊響應模型,使用漸進解析法計算響應函數的標準差。分別給 lnUR、lnIND1、lnIND2、lnIND3當期一個標準差的新息后,lnUR、lnIND1、lnIND2、lnIND3的脈沖響應曲線見圖5。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為年),縱軸表示脈沖響應函數值。
圖5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圖5中的A1-A4說明的是城鎮化自身及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對城鎮化水平的影響。圖A1說明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為正向反應,反應較為迅速且強烈,3期時到達最高點,之后對新息的反應呈平穩趨勢。圖A2說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對城鎮化水平影響較小,1-5期為正向影響,5期后為負向影響。說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變化會在滯后5期對城鎮化產生影響,同時如果第一產業產值降低,則會促進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來到城市,從而提高城鎮化水平。圖A3說明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對山東省城鎮化水平是負向影響,即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的提高,反而會降低城鎮化水平。究其原因,是由于山東省第二產業基礎雄厚,在全國極具競爭優勢,已經進入高度發達階段。根據第二產業與城鎮化互動關系的階段性理論,山東省已經度過依靠第二產業擴張從而帶動城鎮化迅速發展的時期,第二產業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已經減緩。第二產業的發展特點更多體現在原有產業基礎上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因此難以再吸納大規模進城農民,對城鎮化率的提高也沒有太大的帶動作用。第二產業的發展,反而使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并對城市就業人員的技術、文化要求更高,不利于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并使城鎮化率下降。圖A4說明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對山東省城鎮化水平也是負向影響,山東省第三產業的發展未能吸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根據產業結構與城鎮化互動關系的階段性理論,在第二產業無法有效推動城鎮化后,第三產業應該取而代之,成為推動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但從山東省第三產業的現狀來看,技術密集型的高級服務業發展較快,這種類型的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低,需要高素質的從業人員,難以形成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拉力;而勞動密集型的初級服務業則較為滯后,就業吸納力低,反而使城鎮化水平下降。
圖B1、C1及D1說明的是城鎮化水平對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影響。圖B1說明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影響沒有時滯,從第1期開始就是負向影響,且隨著時間推移呈放大趨勢。這說明山東省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呈反向作用,這是因為城鎮化進程使一部分勞動力離開第一產業進入到第二、三產業,如果一個地區的第一產業屬于粗放增長模式,投入要素的減少勢必會降低其產值;但若第一產業呈現集約增長的特點,即使農業勞動力下降了,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和效率提高反而會增加其產值。從這個角度判斷,山東省城鎮化并未帶來第一產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圖C1說明城鎮化對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的影響沒有時滯,滯后1期后開始產生影響,且從開始的正向影響到保持平穩的放大趨勢,表明隨著山東省城鎮化的推進,城市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對第二產業發生正向影響并逐漸歸于平穩。圖D1說明城鎮化對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的影響從開始就是負向影響,之后一直呈放大趨勢。山東省城鎮化的推進不利于第三產業發展,主要原因仍是山東省現代化第三產業更加依賴于生產方式的升級、技術進步等,城鎮化的推進對這些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并無推動作用,城鎮化反而會增加土地使用、環境、交通等額外成本,對第三產業帶來一定的負向影響。
6.Granger因果檢驗
根據Granger因果關系,建立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檢驗模型,檢驗結果見表4。表4的檢驗結果說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1-3期是第一產業產值比重變化的原因,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產值比重變化的推動作用較為明顯;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在1-5期不是城鎮化的原因。即山東省的城鎮化水平與第一產業具有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城鎮化有利于第一產業的發展,但第一產業的發展卻無益于城鎮化。
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在1-5期是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變化的原因,說明城鎮化對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變化的推動作用較為明顯,但是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的變化一直不是山東省城鎮化變化的原因。這與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一致,說明山東省第二產業的優化升級主要依賴于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從而無法大規模吸收山東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并將之真正轉化為城鎮人口。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也是單向因果關系,山東省第二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利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山東省城鎮化率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在滯后第4期時分別互為Granger原因,說明山東省的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具有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需要說明的是,結合脈沖響應函數,這種雙向的因果關系都是負向影響。
表4山東省城鎮化率和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1978—2012年)
滯后1期 滯后2期 滯后3期 滯后4期 滯后5期
LnUR 不是LnIND1的 Granger 原因 ?19.6576(0.0001)
拒絕H0 ?4.84238(0.0156)
拒絕H0 3.94247(0.0197)
拒絕H0 1.28085(0.3077)
接受H0 ?1.61974(0.2029)
接受H0
LnIND1不是LnUR的 Granger 原因 ?0.65292(0.4252)
接受H0 ??0.22984(0.7961)
接受H0 1.52531(0.2324)
接受H0 1.93050(0.1410)
接受H0 1.36797(0.2801)
接受H0
LnUR 不是LnIND2的 Granger 原因 9.85165(0.0037)
拒絕H0 ??4.93161(0.0146)
拒絕H0 ?6.30762(0.0025)
拒絕H0 2.78772(0.0517)
拒絕H0 ?3.03892(0.0351)
拒絕H0
LnIND2不是LnUR的 Granger 原因 ?0.00615(0.9380)
接受H0 ?1.64526(0.2111)
接受H0 1.16716(0.3420)
接受H0 1.02921(0.4143)
接受H0 1.04784(0.4190)
接受H0
LnUR 不是LnIND3的 Granger 原因 ?0.13270(0.7181)
接受H0 ?0.85947(0.4343)
接受H0 1.24611(0.3141)
接受H0 3.23766(0.0312)
拒絕H0 3.69664(0.0166)
拒絕H0
LnIND3不是LnUR的 Granger 原因 0.28737(0.5957)
接受H0 ??2.23677(0.1255)
接受H0 1.10434
(0.3659)接受H0 ?2.62077
(0.0626)拒絕H0 ?1.91835(0.1385)
接受H0
三、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1.研究結論
山東省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的變動整體趨勢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方向,但略顯滯后。從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看,山東省的產值結構表現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 ”,同期城鎮化發展也呈現速度緩慢及反復狀態。山東省的這一特點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產值比重一般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順序不一致。
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和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城鎮化對第二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但對第一、第三產業具有負向影響。同時,山東省產業結構升級難以對城鎮化形成帶動作用,三次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產業結構的升級整體上不利于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具體到各個產業,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一產業的發展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一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一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山東省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為負向影響,即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第一產業產值的降低,山東省第一產業仍呈現粗放增長的特點。山東省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下降并未影響城鎮化水平,雖然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下降,但由此而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并未遷移到城市,這將導致農業生產的集中化和大規模經營仍難以實現。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發展也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二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二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從經濟實踐的角度而言,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通過城市經濟的聚集效應、規模效應、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的下降等促進第二產業的發展。目前,盡管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占絕對優勢,但由于山東省第二產業的發展更多依靠自身的技術革命、生產方式轉變、資本積累等,其就業彈性較低,無法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真正帶動力,因此對山東省城鎮化的拉動作用不是很大。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存在一定滯后期。結合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這種雙向影響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第三產業對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從而無法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未能有效增加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及市場對服務的需求,因此無法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14]。
2.政策建議
第一,改革戶籍制度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調動農民進城的積極性。目前的戶籍制度已嚴重抑制了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即便已經進城的農民在社會保障各方面受到種種限制,因此無法充分享受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能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群體,阻礙了城市的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從而嚴重阻礙了山東省城鎮化的發展。
第二,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強化第一產業的發展。由于自然資源豐富,土地質量及氣候條件都較好,山東省農業基礎較好。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山東省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向多元化的現代農業轉換。在農業生產中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使第一產業在發展壯大的同時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有利于山東省城鎮化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第三,推進新型工業化,注重工業的集約式增長。在城鎮化的初期階段,工業化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但由實證分析可知,山東省工業化在城鎮化進程中沒有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山東省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因而不能有效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城鎮化進程中,不應對工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寄予過多的期望,給予更大的壓力,工業對城鎮化的帶動應讓位于第三產業。因此,山東省工業的發展方向在于推進新型工業化及集約式增長,著力提升工業化發展的質量,增加對交通、電信、金融等生產服務業的需求,增強工業化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帶動,進而間接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發展進程。
第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證分析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更為明顯。同時,山東省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偏低,表明山東省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仍十分巨大,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尤其是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進入后期階段時,第三產業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道路,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及城鎮化的后續動力。因此,山東省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高度重視第三產業提供就業的能力,使其成為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參考文獻]
[1]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
[2]錢納里.發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75.
[3]Krugman. 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 1991(99):83-99.
[4]Porter 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M]. NewYork:FreePress,1998.
[5]Rac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40):3-37.
[6]Kondo, Hiroki. Multiple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spatial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2004(1):167-199.
[7]Lucas R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42.
[8]Black V. Henderson.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7):252-284.
[9]Murata. Manufacturingstructureand regionalurbanization[J].Journalof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56):44-95.
[10] 周維富.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論[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
[11] 魏娟,李敏.產業結構演變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實證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中國科技論壇,2009(11):83-87.
[12] 李卉群.中國城鎮化進程與服務經濟發展動態關系的實證研究[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87-92.
[13] 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14] 吳先華.城鎮化、市民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山東省時間序列數據及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地理科學,2011(1):68-73.
[責任編輯王艷芳]
接受H0 1.16716(0.3420)
接受H0 1.02921(0.4143)
接受H0 1.04784(0.4190)
接受H0
LnUR 不是LnIND3的 Granger 原因 ?0.13270(0.7181)
接受H0 ?0.85947(0.4343)
接受H0 1.24611(0.3141)
接受H0 3.23766(0.0312)
拒絕H0 3.69664(0.0166)
拒絕H0
LnIND3不是LnUR的 Granger 原因 0.28737(0.5957)
接受H0 ??2.23677(0.1255)
接受H0 1.10434
(0.3659)接受H0 ?2.62077
(0.0626)拒絕H0 ?1.91835(0.1385)
接受H0
三、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1.研究結論
山東省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的變動整體趨勢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方向,但略顯滯后。從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看,山東省的產值結構表現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 ”,同期城鎮化發展也呈現速度緩慢及反復狀態。山東省的這一特點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產值比重一般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順序不一致。
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和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城鎮化對第二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但對第一、第三產業具有負向影響。同時,山東省產業結構升級難以對城鎮化形成帶動作用,三次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產業結構的升級整體上不利于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具體到各個產業,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一產業的發展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一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一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山東省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為負向影響,即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第一產業產值的降低,山東省第一產業仍呈現粗放增長的特點。山東省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下降并未影響城鎮化水平,雖然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下降,但由此而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并未遷移到城市,這將導致農業生產的集中化和大規模經營仍難以實現。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發展也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二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二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從經濟實踐的角度而言,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通過城市經濟的聚集效應、規模效應、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的下降等促進第二產業的發展。目前,盡管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占絕對優勢,但由于山東省第二產業的發展更多依靠自身的技術革命、生產方式轉變、資本積累等,其就業彈性較低,無法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真正帶動力,因此對山東省城鎮化的拉動作用不是很大。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存在一定滯后期。結合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這種雙向影響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第三產業對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從而無法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未能有效增加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及市場對服務的需求,因此無法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14]。
2.政策建議
第一,改革戶籍制度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調動農民進城的積極性。目前的戶籍制度已嚴重抑制了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即便已經進城的農民在社會保障各方面受到種種限制,因此無法充分享受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能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群體,阻礙了城市的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從而嚴重阻礙了山東省城鎮化的發展。
第二,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強化第一產業的發展。由于自然資源豐富,土地質量及氣候條件都較好,山東省農業基礎較好。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山東省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向多元化的現代農業轉換。在農業生產中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使第一產業在發展壯大的同時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有利于山東省城鎮化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第三,推進新型工業化,注重工業的集約式增長。在城鎮化的初期階段,工業化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但由實證分析可知,山東省工業化在城鎮化進程中沒有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山東省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因而不能有效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城鎮化進程中,不應對工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寄予過多的期望,給予更大的壓力,工業對城鎮化的帶動應讓位于第三產業。因此,山東省工業的發展方向在于推進新型工業化及集約式增長,著力提升工業化發展的質量,增加對交通、電信、金融等生產服務業的需求,增強工業化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帶動,進而間接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發展進程。
第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證分析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更為明顯。同時,山東省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偏低,表明山東省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仍十分巨大,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尤其是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進入后期階段時,第三產業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道路,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及城鎮化的后續動力。因此,山東省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高度重視第三產業提供就業的能力,使其成為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參考文獻]
[1]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
[2]錢納里.發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75.
[3]Krugman. 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 1991(99):83-99.
[4]Porter 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M]. NewYork:FreePress,1998.
[5]Rac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40):3-37.
[6]Kondo, Hiroki. Multiple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spatial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2004(1):167-199.
[7]Lucas R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42.
[8]Black V. Henderson.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7):252-284.
[9]Murata. Manufacturingstructureand regionalurbanization[J].Journalof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56):44-95.
[10] 周維富.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論[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
[11] 魏娟,李敏.產業結構演變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實證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中國科技論壇,2009(11):83-87.
[12] 李卉群.中國城鎮化進程與服務經濟發展動態關系的實證研究[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87-92.
[13] 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14] 吳先華.城鎮化、市民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山東省時間序列數據及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地理科學,2011(1):68-73.
[責任編輯王艷芳]
接受H0 1.16716(0.3420)
接受H0 1.02921(0.4143)
接受H0 1.04784(0.4190)
接受H0
LnUR 不是LnIND3的 Granger 原因 ?0.13270(0.7181)
接受H0 ?0.85947(0.4343)
接受H0 1.24611(0.3141)
接受H0 3.23766(0.0312)
拒絕H0 3.69664(0.0166)
拒絕H0
LnIND3不是LnUR的 Granger 原因 0.28737(0.5957)
接受H0 ??2.23677(0.1255)
接受H0 1.10434
(0.3659)接受H0 ?2.62077
(0.0626)拒絕H0 ?1.91835(0.1385)
接受H0
三、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1.研究結論
山東省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的變動整體趨勢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方向,但略顯滯后。從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看,山東省的產值結構表現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 ”,同期城鎮化發展也呈現速度緩慢及反復狀態。山東省的這一特點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產值比重一般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順序不一致。
山東省城鎮化水平和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城鎮化對第二產業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但對第一、第三產業具有負向影響。同時,山東省產業結構升級難以對城鎮化形成帶動作用,三次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產業結構的升級整體上不利于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具體到各個產業,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一產業的發展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一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一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山東省城鎮化對第一產業為負向影響,即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第一產業產值的降低,山東省第一產業仍呈現粗放增長的特點。山東省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下降并未影響城鎮化水平,雖然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下降,但由此而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并未遷移到城市,這將導致農業生產的集中化和大規模經營仍難以實現。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二產業發展也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是第二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而第二產業發展卻不是城鎮化推進的Granger原因。從經濟實踐的角度而言,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通過城市經濟的聚集效應、規模效應、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的下降等促進第二產業的發展。目前,盡管山東省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占絕對優勢,但由于山東省第二產業的發展更多依靠自身的技術革命、生產方式轉變、資本積累等,其就業彈性較低,無法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真正帶動力,因此對山東省城鎮化的拉動作用不是很大。
從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關系來看,山東省城鎮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存在一定滯后期。結合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這種雙向影響均為負向影響。說明山東省第三產業對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從而無法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山東省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未能有效增加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及市場對服務的需求,因此無法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14]。
2.政策建議
第一,改革戶籍制度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調動農民進城的積極性。目前的戶籍制度已嚴重抑制了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即便已經進城的農民在社會保障各方面受到種種限制,因此無法充分享受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能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群體,阻礙了城市的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從而嚴重阻礙了山東省城鎮化的發展。
第二,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強化第一產業的發展。由于自然資源豐富,土地質量及氣候條件都較好,山東省農業基礎較好。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山東省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向多元化的現代農業轉換。在農業生產中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使第一產業在發展壯大的同時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有利于山東省城鎮化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第三,推進新型工業化,注重工業的集約式增長。在城鎮化的初期階段,工業化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但由實證分析可知,山東省工業化在城鎮化進程中沒有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山東省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因而不能有效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城鎮化進程中,不應對工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寄予過多的期望,給予更大的壓力,工業對城鎮化的帶動應讓位于第三產業。因此,山東省工業的發展方向在于推進新型工業化及集約式增長,著力提升工業化發展的質量,增加對交通、電信、金融等生產服務業的需求,增強工業化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帶動,進而間接推動山東省的城鎮化發展進程。
第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證分析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山東省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更為明顯。同時,山東省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偏低,表明山東省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仍十分巨大,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第三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尤其是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進入后期階段時,第三產業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走上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道路,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及城鎮化的后續動力。因此,山東省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高度重視第三產業提供就業的能力,使其成為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參考文獻]
[1]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
[2]錢納里.發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75.
[3]Krugman. 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 1991(99):83-99.
[4]Porter 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M]. NewYork:FreePress,1998.
[5]Raco.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geography[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40):3-37.
[6]Kondo, Hiroki. Multiple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spatial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2004(1):167-199.
[7]Lucas R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42.
[8]Black V. Henderson.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7):252-284.
[9]Murata. Manufacturingstructureand regionalurbanization[J].Journalof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56):44-95.
[10] 周維富.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論[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
[11] 魏娟,李敏.產業結構演變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實證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中國科技論壇,2009(11):83-87.
[12] 李卉群.中國城鎮化進程與服務經濟發展動態關系的實證研究[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87-92.
[13] 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14] 吳先華.城鎮化、市民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山東省時間序列數據及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地理科學,2011(1):68-73.
[責任編輯王艷芳]